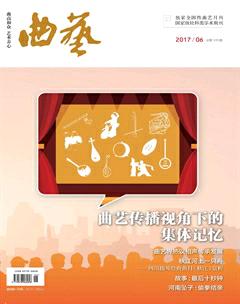我和《曲藝》的緣分
崔立君
緣分天注定,我和《曲藝》就是這樣。
《曲藝》于1957年問世,而我也在那一年出生,我們同庚。
今年,對我和她來說,都是第一個甲子,不同的是,我的一生只能有這一個甲子,而她,可能會有N個甲子。
六十年的歷程,伴隨著她的生而生,伴隨著她的長而長,伴隨著她的困惑而困惑,伴隨著她的快樂而快樂,是緣分,更是一種幸運。
第一次看見她,還是在懵懂的年齡。記得是父親把她帶回家來的,那時,我還認不了幾個字。喜歡藝術的父親把她捧在手里看,時不時地發出笑聲,這笑聲吸引了我,于是也湊了過去。父親指著封面上的兩個大字,告訴我,是“曲藝”。我問什么是曲藝,父親告訴我,曲藝就是讓人開心的藝術。讓人開心誰不喜歡啊?就這樣,我開始對曲藝產生了興趣。可是,那時畢竟年齡小,還沒有閱讀《曲藝》的能力,于是就聽收音機。凡是播送曲藝節目時,我都老老實實地坐在那里聽,坐在那里笑。在父親的啟蒙下,我知道了侯寶林、高元鈞、李潤杰、關學曾、王毓寶、馬季,知道了相聲、山東快書、快板書、北京琴書、天津時調。就這樣,我早早便愛上了曲藝。
不幸的是,當我有了閱讀能力的時候,《曲藝》卻見不到了,那時我十歲,《曲藝》停刊了。但我心中對曲藝的愛之火已經被點燃,是無法熄滅的。上中學時,我開始寫相聲、寫快板,和同學排練演出,活躍在校園的舞臺上。此后,無論是插隊下鄉還是抽工回城,我的創作和表演都沒有停止過。
1979年,《曲藝》復刊。那時,我已經是一個大學生了,不僅在校園的舞臺上大顯身手,而且還擔任了校學生會的文藝部部長。在我極力主張下,部里給大家訂了三本雜志:《曲藝》《遼寧群眾文藝》和《天津演唱》。
大學期間,我在曲藝創作上發展勢頭很不錯,陸續往《遼寧群眾文藝》和《天津演唱》上投了幾篇稿子,都變成了鉛字,并且有了稿費的收入。那時的稿費標準相當可觀,發表一篇稿子竟然可以解決一個大學生半學期的伙食費。但我卻一直沒敢往《曲藝》上投稿,因為那是曲藝界最高級別的刊物,在我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我知道我的功力還達不到,不敢輕舉妄動。那時的我已把有朝一日在《曲藝》上發表作品設定為自己人生的一個大目標,并為之時刻準備著。
1990年,湖南益陽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相聲比賽,我前往觀摩學習,第一次見到了《曲藝》雜志的編輯朱疆源老師。那時我還很年輕,見到大刊物的編輯有點誠惶誠恐,激動之余難掩緊張之情。轉過年來,我的一篇作品在一次全國性的曲藝征文活動上獲了個小獎,我萌生了給《曲藝》雜志投稿的想法。將稿件郵走后過了些日子,我收到了《曲藝》雜志的回復。朱疆源老師親筆寫信告訴我那次征文活動收到的稿子很多,限于版面,雜志只能選發獲獎名次靠前的稿子。但她還在信中熱情地鼓勵我堅持創作,相信我會寫出更高質量的作品。雖然稿子退回來了,但我的創作熱情卻被這封信進一步激發出來了。1992年,我寫出了相聲《8字迷》,沒想到這篇作品瞬間火了起來,甚至讓我感到猝不及防。這段相聲不僅入選了當年的丹東市、遼寧省和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而且拿了從地方到國家一系列的大獎。《8字迷》是我的成名作,一下子改變了我的命運。我把稿子寄到《曲藝》雜志,作品發表了。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曲藝》雜志,用今天的話來說,好的開端奠定了我從事曲藝創作的基調,我和《曲藝》的關系更加親密起來。隨后,我和雜志社不少編輯成為了朋友。如今,我已從一個普通作者成長起來,以為新生代作者作點評、撰寫“卷首語”等方式為《曲藝》雜志貢獻智慧。
時至今日,我寫的曲藝作品已經有三百多段了,出版有三本作品集。《曲藝》這個平臺一直是鼓勵我筆耕不輟的加油站。
六十年來,我和《曲藝》同呼吸、共命運,用東北話來說,感情杠杠的。雖然我的人生已步入老年,但《曲藝》的生命依然強壯。我相信,只要人類存在,只要藝術存在,《曲藝》就會存在。
我感謝曲藝,也感謝《曲藝》,是她們讓我的人生如此精彩。我愿意在曲藝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直到人生的盡頭。
六十年轉瞬即逝,我老了,她不老。我不能永遠陪她,但我要深深地祝福她——她將生命常在,她將青春永駐。
愿對《曲藝》的愛,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