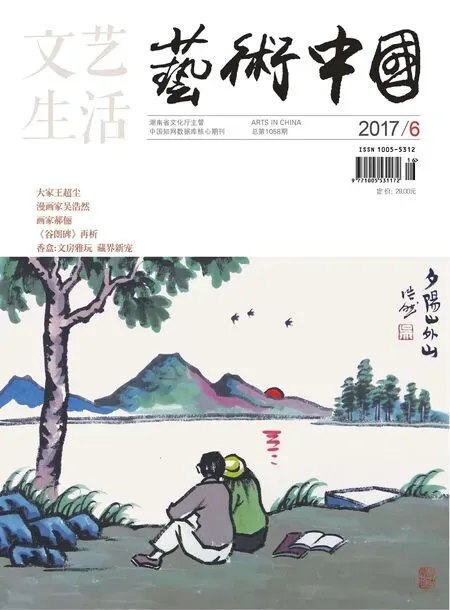元氣淋漓真境生
◆ 譚金平(陽光學院)
元氣淋漓真境生
◆ 譚金平(陽光學院)
初識曾進教授,我記得已是2005年的事了。見其人之前,已久聞其名。美院一位資深教授曾告訴我,曾進教授是一位非常認真負責、平易近人的老師。其畫、其人儒雅而不柔弱,豪邁而不張揚。見其人便可窺其畫境之真,觀其畫亦可識其人格之誠,此正所謂畫如其人,人如其畫也。
毋庸置疑,在當今美術界,“真情、真景、真筆墨”的山水畫“觀道”方式帶來的不僅僅是賞心悅目的藝術美,同時也批判、揭露了藝術的虛假、柔弱、怪誕之風。立足于中華文化傳統,以開拓的精神,發展真、善、美的山水畫藝術才是中國山水畫藝術發展的正道。而真誠應該是藝術的首要根本。我們從曾進教授率性求真的藝術道路,亦可以一窺其人之誠、其境之真。
曾進教授1962年出生在一個典型的書畫世家,其父曾曉滸先生是譽滿全國的山水、花鳥畫大家。他自幼耳濡目染,受書香畫韻熏陶頗深。按常情,深厚的家庭背景會讓他在傳統的培養模式下按部就班地學習,但現實總是不按常理出牌。十年的動亂給正值少年的他帶來了空前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沉醉于圖畫之中;亦可自由地游玩于山野之間。喜山愛水的天性讓他見到色彩斑斕的水彩畫、油畫風景便開始有意模仿、玩轉。可以斷定,人在少年時的色彩是燦爛的,正如這時他似乎更喜歡西畫的色彩風景,鐘情于那絢爛的、直接的色彩。1978年,十六歲的他就考入了湖南師范大學美術系,滿懷熱情地選擇了色彩豐富的油畫專業,系統地學習了西畫,為日后打下了堅實的造型基礎。在這個時代,一個繪畫者是不可能完全擺脫西畫影響的。西畫的傳入是利大于弊的,是有利于中國畫發展的。排外的文化既不健康,也不能長久。歷史證明,中國文化處于世界巔峰之時都是開放的和兼容并蓄的。如對西畫認真研究,使其為我所用,這對我們民族藝術的發展也有莫大好處的,這也是他少年時代感性而自由的選擇。而不是像不了解內情的人猜測的那樣,是其父的有意安排。這是率性自然的選擇和真性情的表達貫穿于他的藝術與生活之中的體現。
大學畢業之后參加工作,雖然在教學上從事西畫,但隨著思想的日趨成熟,文化藝術中自我意識的發現、成長,使他始終無法找到文化藝術的歸宿感。而藝術應該是對自我的肯定,是表現自我、抒發情感、“澄懷觀道”的活動過程。藝術追求上一顆徘徊、游離的心,讓他意識到是對自我的疏遠,也許最終會失去自我。1983年,在當時全國最先進的長沙火車站,其父曾曉滸先生帶領了包括他在內的5名學生共同繪制了巨幅山水畫《醴蘭沅芷 岳色湘聲》。這一年,為創作這一幅畫,他隨父親到北京、南京、蘇州等地參觀名家大作,赴湘南、湘西采訪寫生,飽覽武陵秀色、三湘美景。最終歷時半年之久,一幅高9米,寬18米,當時號稱全國最大的紙本國畫得以完成。此畫集三湘秀色,納四水靈氣,把這塊人杰地靈的熱土描繪得神奇而秀美,深受社會好評。這次經歷給他個人帶來的藝術震撼也是無法估量的。眼界的開闊、技法的純熟、認識的提高、理解的深入使他逐漸地清晰了適合自身個性特點的藝術追求。由于中國山水畫特有的“澄懷觀道”藝術表達方式非常適合他的個性表達,加上自我意識的覺醒,從此他便一發不可收拾地鐘情于國畫的山山水水。這是藝術自由的回歸、傳統文化的感召、率性自然的選擇和真情真景的融合。
他率性真誠地投入到真山真水的山水畫創作,以真情入畫、以真景達情是他的藝術特點之一。
繼承父輩的事業猶如站在巨人肩上,憑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加上自身的勤奮努力,曾進教授很好地掌握了傳統精髓和高難技藝。身處湘楚之地、學堂圣殿,以傳統為依托,以地域為特色,將自己對時代氣息的把握和對現實生活的體驗熔于山水藝術之爐,養成了他文雅、質樸、真性情的人格與畫格一致的品質,鑄就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他走遍三湘四水,用心感受,用心提煉,完全用自己的感覺方式畫他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情感和手段努力發展他所堅持的符合他性格特征的山水畫藝術樣式。其遒勁的筆力、豐富的色彩、富有韻味的墨色變化,每每讓我感動,讓我興奮。其“真情、真景、真筆墨”所營造的豪邁之情,恰到好處地傳達了湖湘人文、地貌的精髓。“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曾進教授一直提倡的創作理念。不論是畫畫還是教學,他都把寫生和繼承傳統看得同等重要。跟隨他出去寫生的學生,更能體會到他是如何以真情融入真景、如何以真景表達真情,更能理解何謂“天人合一”、如何“澄懷觀道”,而不是一味地、長期地閉門造車式地復制帶有自己那點功利性風格的作品。

岳麓勝概 國畫 曾進
雖是秉承其父“真情、真景、真筆墨”的真山真水風格,然其人至誠,始終堅持“真筆墨”的寫心性,畫風也更似為其量身定做。其用筆用墨在勾勒真景的過程中,講究書法用筆,把書法的用筆功力貫注進去,把對象的內在氣質同筆劃的力度、節奏結合起來,使其有骨氣的意味。這樣主體的涵養和性情隨筆墨在物象的書寫過程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使描寫對象成為一種心靈的化身,成為能讓觀者識心見性的載體。這就是“真筆墨”的“寫心”功能。真正的藝術家善于運用最適合自己的藝術形式把內心的感受和情緒表達出來。他根據虛谷與龔賢畫樹的筆法,有意識地探索出一種“散筆”枝葉法,使他的畫樹法成為畫風的重要構成因素。枝干部分用筆遒勁、氣勢連貫,而細枝大部分是用的“散亂”勾筆,樹形更顯生機與靈動。點葉將傳統筆法中的“個”字、“米”、字“介”字點都概括為圓點、豎點、橫點和折扇形點,使樹葉疏密而有秩序感,發揮了中國畫表現自然的主觀能動性。而遠山上的樹有時就只有交替出現的橫點和豎點,既獲得“面”的感覺又能將樹和巖石的簡約用筆區別開來。“真情、真景、真筆墨”的筆墨風格特點,是他數十年真誠尋找培養出來的。就如孟子所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曾進教授的“養”是有繼承基礎的,它不是短時間的一蹴而就,而是漸變的過程。雖略看有似其父之處,但這是學的痕跡,其中更有新的發展、新的氣象。從畫作中可以看出他受西畫的影響比父親更明顯強烈一些,山川更真實,自然氣息更濃厚,色彩也更濃郁豐富。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其面貌應該是與他的身體、精神狀態和文化學養相符才是真誠的、真正的藝術品。和諧社會提倡的是健康的審美的藝術。我想沒人愿意看一個20多歲的健康青年畫那老態龍鐘的畫作,即使真有這樣的,那也必定是不真誠、病態的,那不是審美的。“真情、真景、真筆墨”的繼承和發展,更符合他正值壯年的精神狀態和天性,它流露出來的是一種真誠而健康的審美。
中國畫作為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藝術門類之一,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自古以來畫家極其講究“畫外功”,他們的學識修養、精神氣度、人格品質,一直是被作為品評畫作優劣的重要依據。既有家學淵源,又由于大學畢業就一直在大學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教學相長,使曾進教授的為人處事總是那么的有條不紊、不急不躁、認真負責、細致入微。作為教師,他向來以“學高為師,德高為范”的標準自勵,提倡終身學習。經歷數十年,除畫事、教學外他一直筆耕不輟,先后在《美術研究》《美術》《中國美術》《中國書畫報》《美術家》《湖南書畫》《湖南師大學報》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文章。
身處美術學院——湖南美術教育的最高殿堂,曾進教授將“真情、真景、真筆墨”的繪畫理念從做學問延伸到做人處事的方方面面,以求言、行、畫、學的真誠一致。相識日久,聽其言,觀其行,更覺古人所言“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之語非妄言。他一心執著于藝術創作和教育,心境灑脫,不受名利場的誘惑而保持了人格的率真。體現了他對“畫外功”的學養、性情品格的修煉深度和意義,這也是中國文人畫家的價值核心所在。這一點一直為我所佩服,為熟悉之人所敬仰。他倡導的以真性情入畫,以真景、真筆墨示人,不正是符合國人那“人如其畫,畫如其人”的審美理想嗎?
情景合則為境,筆墨真則“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