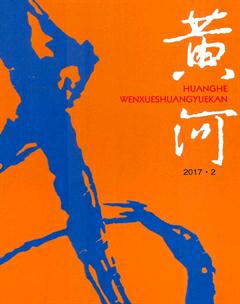貼地飛翔
賈晟
閆文盛,1978年生于山西介休,從事文學創作二十年,現為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農家子弟踏實勤奮的樸素信條,和與生俱來的敏感性情構成他文字生涯中的首位老師。1996年,閆文盛的第一首詩在《中國校園文學》發表,此后六七年里,詩歌成為他宣泄積郁、抒發感悟的寄托。在此期間,他經歷了四年苦悶而乏味的小縣城生活,半年奔波轉徙的異地打拼,青春的激情逐漸凝為冷峻的思慮,創作重心隨之轉向更能直接表達這種體悟的文體——散文。
2010年,閆文盛的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入選由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主持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使他在山西青年作家中嶄露頭角。此書以娓娓道來的筆調講述了作者親歷的人生故事及所思所感——故鄉難忘的童年回憶、孤身漂泊在外的異鄉經歷以及人到中年的負重與虛無。當多數人以反映宏大事件為創作方向時,閆文盛這種面向自我心靈的孤獨求索無疑是獨特無二的。他以當下的處境為切入點,以擇心自食的勇氣反復觸摸常人習慣性回避的生存痛感,展開對“人的存在”這一終極性問題的哲理性思考。
從2002年初涉太原的媒體行業,歷任報紙編輯、周刊執行主編、雜志編輯總監、執行主編,到2014年調入山西文學院任專業作家,閆文盛結束了在省城變動不居的12個年頭,迎來了文學創作的沉潛期。固定的居所、穩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庭為閆文盛提供了回顧人生過往,反思創作局限的良好契機,他的寫作技能愈加精煉純熟。這一時期的創作成果是兩部散文集《你往哪里去》和《主觀書》。《你往哪里去》已于2015年正式出版,《主觀書》中的部分篇章選入其中。最為作者珍視也最具研究價值的是系列散文《主觀書》,該書突破了之前的自敘模式,開辟了全新的寫作路向,在文體實驗以及自我心靈世界的挖掘上均向縱深處發展。
十多年的散文創作中,閆文盛始終秉承的是自我豐富而又復雜的心靈因子,即他自述的“內心中的善、誠摯、恐懼和惡念”。他以自我心靈為觀察對象,記錄自己在現實種種遭際中的所思所感,展現由困頓現實飛躍到自由精神之境的艱難歷程。一方是紛擾不斷的現實,一方是難以企及的夢想,他始終是在貼著地面作奮力的飛翔。
一、面向現實的自我審視
《失蹤者的旅行》和《你往哪里去》先后出版于2011年和2015年,展現了閆文盛散文創作從發軔到成熟的過程。二者均記錄了一個漂泊多年,身心都無處歸依的異鄉者的心路歷程,處處滲透著清晰而深徹的生存痛感。
《幼年的冰雪》解密了作者最初的兒時記憶:飽受傷害的母親,會時不時向年幼的“我”哭訴不幸的遭遇,她的苦痛與淚水像冰雪一般覆蓋了“我”幼小的心靈。這一兒時的創傷性記憶塑造了作者敏感的性情,深遠地影響了他此后的寫作路向。《水利學校》點明了作者邂逅文學的契機:少年時代無處排遣的憂傷與孤獨在與文字的對話中得到釋放,他的寫作生涯由此開始。《南方的寒冷》《應聘記》《購房記》回溯了作者作為一個農家子弟為獲得城市的接納所經歷的辛酸往事,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城鄉碰撞帶給個體生命的痛楚”,坦言這些文字記錄了他遭遇現實重創后的種種思慮。然而對生存痛感的反復書寫并非他的興趣所在,他是希圖通過“直面慘淡的人生”,達到對現實以及對自我的和解。由此,他展開了面向現實的自我審視,這一由外而內的視角不僅賦予了其散文創作寫實性與哲理性兼具的藝術特質,而且影響了其散文的結構安排。
(一)基于寫實的情感傳達
寫實性是閆文盛初期散文創作的突出特點,一件小事、一點情緒、一處景致、一縷思緒都能被納入到細密的敘述中。于是,為我們所忽視的生活常貌被活色生香地呈現出來:“家家戶戶的廚房里都傳出鍋碗瓢盆互相碰撞的聲音,油煙味也隨之在空氣中蒸騰”(《寄居者》);“唯那街邊的樹木都瘦削骨立,那挑檐的建筑都是仿古的新構架,唯有那走動于街市上的少女帶了生動的顏色,把整個畫面帶出了一絲絲青春氣”(《集市》);“那滴雨,另外的那一滴,又一滴雨,它們在破空而下時發出一片沙沙沙的聲音,仿佛刺穿了空氣中的所有物質。它們尖利的部位首先鉆入水里,然后整個身體歸于無形。”(《寧靜的加速度》)
但閆文盛并不止于對生活表象鏡像般的描摹,而是將強烈的主觀感受注入對客觀事物的描寫中,使得一切所見所聞化為作者心理感覺的投影,從而間接折射出作者微妙難言的心緒。例如作者在回憶南方寒冷之時,并不止于描寫這種物理現象帶給人的生理反應,而是在此背景下,講述異地漂泊的“我”屢遭公司拖欠薪水的經歷。身體上的寒冷經由艱難處境的逼迫一步步侵入“我”的內心,“我”感到“一種貫通心扉的冷意”。南方寒冷的冬天透露出人在異鄉的孤獨無力之感,而故鄉悠長的夏天則勾起了無限鄉愁。“我”想象父親“扛著鋤頭到了田里,他看到了這個夏季正如一只久久不歸的鳥,它飛得那么高,那么遠,卻好似沒有力量”。年老的父母思念著久久不歸的兒女們,漫長的夏日化為遙遙無期的等待。這一想象隱含著故土對漂泊的游子的深情呼喚與堅定守望,這何嘗不是游子對鄉愁的另一重委婉表達?在寫實的背后,作家顯然調動了豐富的人生閱歷,從而寫出了深沉的人生況味。
(二)寫實之上的哲思涌動
除了深沉的情感之流的涌動,閆文盛的散文中還處處閃現著睿智的哲思之光。他時時被圍困在由時空巨大變遷所引發的陌生感與迷失感之中,執著于對人將何去何從這一終極命題的追問。他習慣于在觀察中沉思,從當下的心態出發,蔓延出歷經風雨的人生感懷,將此刻、昨日與未來融為一體,賦予原本普通的描寫對象以深刻雋永的內涵。
這一特點在《火車站》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該文講述了“我”圍繞“火車站”這一極具開放性的流動空間展開的回憶與思考,置身空曠的車站廣場,“我”回憶起人生中多次意義重大的遠行。年少時,由于對家鄉心生厭倦,“我”決定去外面的世界闖蕩。可當“我”背上行囊,即將踏上列車之時,對未知的恐懼和對故鄉的無限留戀攫住了“我”的內心。“我”就在這樣矛盾的情緒中邁出了走向獨立的第一步。從此,“我”以流浪者的身份過著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火車站”賜予了“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可同時也給予了“我”獨在異鄉的深切痛楚。后來,“我”終于結束了漂泊生涯,在省城安家落戶。
火車站記載了作者的心理變化,保留了漂泊歲月中的生存痛感,它成為現代人面臨重大抉擇時的一種象征。是固守一成不變卻又安逸舒適的封閉狀態,還是走向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開放空間,這是每個人尤其是初涉社會的青年人都會遭遇的選擇難題。與習慣的生活環境告別無疑是痛苦的,可正是在一次次告別過去,走向陌生的旅途中,年輕的一代革新了自我,成就了自我,伴隨著割裂的苦痛,逐步抵達人生的成熟之境。在文章結尾,作者凝神注視著站牌,領悟到那上面“兩個相背而行的指向導致了我們的人生”,我們正是在一次次離去與歸來中構建漫漫人生道路,“它們循環往復,永無盡時”。
(三)無規則敘述
閆文盛的初期作品是圍繞觸動作家的某一事件或事物展開敘述,有著清晰可循的敘事線索,而在其后來的創作中敘述的連貫性與完整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敘述的無規則化。這一變化最初顯露于《失蹤者的旅行》中的部分篇目,如《思維練習冊》和《寧靜的加速度》,成熟于長篇散文系列《你往哪里去》。
隨著人生閱歷的積累與沉淀,作家舍棄了著眼于局部的視角,嘗試對人世的看法作出整體性的描述。如此一來,無規則敘述實則是作家為重組記憶碎片,提煉個體經驗所刻意采取的敘述策略。若想追尋其中的敘事線索,往往始于有形,歸于無蹤,毫無規則可循。主體意識的自由伸縮跳躍取代傳統的敘述邏輯,成為其散文的結構方式。在這看似隨意拉雜的表象下,貫穿著作者強大而持久的精神氣流,這股氣流將碎片式的敘述凝結成穩定統一的抒情形態。
長篇散文《寧靜的加速度》是無規則敘述的典范之作。該文分為三章,分別是“出生地”、“微弱的轉折”和“本命年”,每一章又劃分為幾個不同小節,對應不同的敘述對象,如第一章中的“家鄉”、“居所”、“樹蔭”以及“清水”。全文籠罩在對“生命的隱痛和時間的蒼茫”的感懷之中。“歲月的滄桑”顯示出一種“流逝的力量”,作者因身心的加速衰老而“手足無措”、“耳暈目眩”。他選擇回歸出生之地,以尋找緩解惶惑感的精神力量。“故鄉”給人以深切的歸依之感;“居所”如同港灣一般庇護著人的身體和靈魂;“樹蔭”給人一種容納“風云滄桑”的從容之感;“清水”則滋養著如夢般絢爛的童年時光。故鄉的“時光如永恒一般漫長和古老”,可“我”終究要去遠方謀生。第二章將公司搬遷的經歷、走在雨中的感悟以及對漫長夏日的遙想等彼此并無關聯的事物依次呈現出來,匯聚出異鄉人的“滄桑和勞頓”。第三章訴說著“我”為逃脫荒蕪之感所作的精神修行——在夜晚傾聽萬物的獨語,在閱讀中“穿行于文字的叢林”,歷經曲折,最終坦然接受“歲月的結局”——“一切尚未開始,但一切卻又結束了”。多重不同層次的人生經驗統攝于作家的主觀意緒之下,創造出醇美而豐富的審美想象空間。
在這類散文中,作者有意減少敘事因素,突出內在思緒的起伏變化,由對外部現實的關注轉向內心世界,開啟“向內的旅行”。這一傾向在下一時期的創作中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
二、返歸內心的艱難開掘
隨著探索的不斷深化,閆文盛的散文創作朝著更加個性化的方向邁進,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是《主觀書》。《主觀書》是閆文盛于2012年至2016年陸續寫成的長篇系列散文。在此書中,作者從思想深度與文本形態兩方面同時進行突進。就思想深度而言,他延續前一時期對自我心靈的探索,但他不再從日常瑣事中提煉感悟,而是返歸內心,直接與自我進行對話,將充滿悖謬與矛盾的心理處境一一挖掘,展現自我的破碎、分裂以及重建的種種可能性。這使得《主觀書》排除了敘事因素,呈現出純粹的抒情性。從文本形態而言,作者將詩的手法與思維引入散文創作,句式上也由復雜的長句變為精悍的短句,并使用重復的詞、短語和句式來凸顯情感的表現力度與變化程度;抽象意念與具體形象的結合,加深了作品的思辨性與蘊藉性,大大擴充了散文的思想容量。在本章中,筆者將以收錄于已出版的散文集《你往哪里去》中的《主觀書》部分為研究對象,嘗試分析其思想內涵與藝術特色。
(一)思想內涵
《主觀書》是一部孤獨之書,而對于孤獨,薩特曾作出以下定義:“孤獨是人類屬性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特征,它是被一種存在于人們‘找到生命意義的需要和‘對人世本質的虛無的覺察之間的矛盾所激發的。”用這句話來解釋閆文盛的寫作動機再恰切不過。閆文盛生來就是一個專注于心靈涉險的孤獨者,他對人生意義的追尋有著不可遏制的熱情與沖動,可是多年的人世浮沉讓他意識到人生本是“一個巨大的虛空”。這二者的矛盾時時刻刻糾結于他的內心,而寫作給予了他“人生的教益和疏放的通道”,但與此同時,寫作也“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教會了他“感知痛苦的能力”,潛伏著墮入另一重虛無的危機。以虛無對抗虛無遂成為了閆文盛寫作的動機。以此為前提,本節將以《主觀書》為核心,著力探討閆文盛散文的思想內涵。
“無力的追尋”與“強勁的夢想”。“無力的追尋和強勁的夢想”是出自《主觀書》中的一個詞組,可用來表征閆文盛散文創作的一大常見主題類型。
閆文盛從青年時代起,就全力追逐人生的意義,經歷過最為動蕩卻又無比新鮮的九年后,他終于結束了漂泊的生活,落戶在省城太原,為疲憊的身心找到了一個棲居之所,并且足不出戶也“足以養活一家老小”。可他卻無法從中獲得身心統一的寧靜之感,日復一日的壓迫感依然如陰云般籠罩著他的心靈。顯然,他在減輕物質需求的壓迫后,又為繁冗的世俗雜務所捆綁,在機械的重復中耗費著寶貴的光陰。他迫切地渴望擺脫世俗的困擾,去尋求理想的精神家園,可歲月的侵蝕打磨使他變得疑慮重重,諸多隱憂使他不敢脫離既定的生活秩序,投入新的生活。他感受到無情的歲月正將他鮮活的生命力一點點扼殺,“直到整個身心、軀干成為一個巨大的虛空。”
在追求精神理想的同時,作家亦不可避免地追求物質理想,而這一種理想是與親情密切相關的。他年少時就離開故土,輾轉異地,“想到母親華發早生,想到母親此生吃過的苦,我就深感悲戚。”由于父母對高樓的巨大恐懼,想要團聚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城里購買別墅。已為精神思慮所苦的作家,又被物質需求這另一種重壓困擾,這何嘗不是人類的普遍生存困惑。
自我的分裂與重建。閆文盛散文第二個經常出現的主題類型,是表現“自我的分裂與重建”。對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謬性的艱苦開掘,使其散文中的自我形象呈現出高度緊張的特征。閆文盛這樣寫道:“我看到深藏在自己身體內部的敵人。我把他們一一殺死,但他們復活的速度過快了,只要我還睜著眼,罪惡遂召之即來。”他將自我視作最大的敵人,這樣的“自我”是分裂的,是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現代人無法確定自我生命價值、存在意義的困境由此被表達了出來。
《盲目》表明了時間對自我確認的影響。“我”的生命曾擁有一個核心,即那些本真的,異于他人的特質。而時間的流逝使“我”與這個核心漸行漸遠。記憶似乎是“我”過去時光的見證,但當“我”試圖說出曾經深刻影響我命運的抉擇時,“這種記憶卻不存在了”——過去之我已與現在之我分離。“我”汲取教訓,小心翼翼地寫下心中的每一絲起伏,可當記憶“被復寫在紙上”,“就開始一次次地重復,失真”——就連寫作也無法彌合“我”在時間中的破裂。后來,我從迷失中走出,“那些被分離的舊我與新我重新合歸一處”,我又重新建立起了核心。作家這看似指向自我心靈的探秘背后,蘊藏著人類的大我——人類正是在一次次的迷失中尋找自我,這場與時間的曠日之戰構成了我們“偉大而盲目的生活”。
除了舊我與新我之間的分裂,當下之我的不同側面也存在著緊張的對峙。《自我否定》中,“我”一面雄心勃勃,認為自己前途無量,一面又憂心忡忡,覺得自己終將一事無成,無限的狂妄與極端的自卑撕扯著“我”的靈魂。“我”的內心如同帝王與乞丐同住,二者之間的沖突不斷上演,難以調和。兩種力量已然壓迫著“我”,而“我”卻開始懷疑這種自我折磨的空虛性。“我”知道最真實的生活是放下苦苦的思慮,“寄居于一種平靜的忙碌”。“我”因此“羨慕黃昏獨飲的爺爺”,他完成了成家立業,繁衍子孫的壯舉,“目光淡定,毫無憂愁”。每當“神經質和事無巨細的敏感”將我逼向虛無,“我”總會走到人群中去,他們身上透露出的瑣碎平凡的生活氣息,有效地減輕了我的思慮之苦。如同《在酒樓上》“我”與呂緯甫所象征著的不同精神指向,一方是飛翔于天空的漂泊者,一方是落腳于大地的堅守者,究竟哪一種生存形態更為貼近生命本質,作者同魯迅一樣并未給出確切的答案,而是勇敢面對這一人類的生存困惑,將自我逼向審察的絕境。
(二)藝術探索
純“抒情性”。《主觀書》是作者對自我心靈的全方位書寫,它將客觀世界排除在外,構筑起隱秘而駁雜的主觀世界。這一向內切入的視角導致了本書的純“抒情性”。作者有意排除充溢于前期創作中的敘事因素,將主觀抒情推向極致。
從當下的情緒狀態出發,追蹤微妙而曲折的心理變化,經歷情感上的苦悶、灼痛、釋放,再到自我平復,是《主觀書》最常見的抒情模式。情感的發端,常出自偶然,有時是做完工作后的悵然若失,等待寫作靈感時的漫長難熬,有時是乘坐公交時聯想到人生的往返不斷,偶爾早起后的別樣感觸……這些看似無關的觸發點,往往將作者引向相似的情感氛圍——困頓和焦灼。這種存在的焦慮感奠定了全書的感情基調,使得創作于不同情境,彼此并無關聯的各個短篇具有了相同的情感指向。
這一結構組織方式無疑借鑒了小說的寫作技法。美國作家馬里奧·普佐的名作《教父》中許多的支線“各有自己的源頭、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匯攏到主線上來。整個故事的主線與支線的發展脈絡,很像一條大河的主流與支流的關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瀉千里”。作者長期浸潤于小說的閱讀與訓練,無形中將小說的結構意識滲透入了散文的整體構思之中。
相似的抒情模式往往會導致作品的單調與雷同,楊朔的散文因此為人所詬病。而閆文盛的散文之所以保持魅力,原因之一就在于抒情過程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在文章的開端,“我”往往徘徊于無邊的困境,當“我”嘗試做出一項定論或行動時,另一種聲音就會提出反對,在二者此消彼長的辯詰之中,我的情感呈現出線團式的復雜變化,如同飛向天空的渴望遭遇重力的撕扯,“我”在掙脫與沉淪之間一步步將自我逼向審察的絕境。比如在《自我否定》中,“我”彷徨于煩悶的情緒中,心中充滿對自我的否定,而同時,“我”對這種看法又提出另一種否定——“我依然覺得自己像個帝王”,自信可以窮盡人世探究的每一個角落。“我”希望通過回憶來解除揮之不去的壓迫感,但“我搜索枯腸,仍然難以從此刻逃脫而去”。“我”感受到沉浸于想象世界的美好與置身現實的煩憂。“我”依靠內心力量與故鄉接近,希望以此尋回本真的自我,卻一無所獲。可在同時,“我深知這個虛無的話題之毒性”。為了找到抵擋其侵蝕的替代品,“我”返身投入人群,讓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沒沉重的虛無之感。最后,“我”重申,“自我否定并非我的興趣所在”,這是“我”難以擺脫的一重心理狀態,“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我們一次次地逼近了自己”。
抒情之純粹是《主觀書》最為突出的特色之一,它使作者豐富而駁雜的內心世界得到了清晰的呈現。作者并不追求物我合一的融洽狀態,而是變傳統的抒情為戲劇性的處境,這與現代人日益復雜的思考密切相關,有其深厚的社會成因。由此可見,《主觀書》在大幅度背離古典抒情傳統之時,實則契合了三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理念,可以說,《主觀書》的思維是閆文盛詩歌創作思維的延續。
詩性的語言。《主觀書》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氣息。“特別是其語言兼具詩歌的凝練與整飭,可謂當代漢語駢文,這種融其他體裁之長于散文的寫作不僅增強了散文的表現力,也凸現了散文的詩意效果。”充滿詩性的語言是《主觀書》的又一大藝術特色。
這一特色首先體現在語詞之間的跳躍性上,比如《空腹》中的一段描寫:“請規律地生活……得找個好大夫。請看他的雙眼,注意他的措辭,請看飛鳥。注意陽光的厚薄。請自視,遠離塵灰和土色。請構筑空中樓閣……請學習辯證法。請戒酒。請繪制旋轉木馬。”開頭即以“請規律地生活”這一訓導性語言奠定全文基調,接著各類具體的請求依次鋪陳開來,“請”字短句貫穿全文,造成強大的抒情力度,讀來一氣呵成。短促而跳躍的語詞,形成了緊促的節奏感,恰切地傳達出作者峻切的精神湍流。
其次,體現在排比句式和相似語詞的反復使用上。這一方法的運用不僅促成了散文結構上的起承轉合,而且成為情感起伏變化的依托,使得原本松散的篇章具備了詩一般的凝練性。《短暫》描述的是“我”尋找寫作靈感的艱難過程。首句“我始終傾心的一刻如此難求”作為中心句反復出現,帶動全文的起承轉合。首次出現,引出“我”為尋求寫作靈感所做的各種嘗試。再次出現時,傳達出“我”想要改造自身局面的迫切渴望。由此開始,中心句的三次復現反復渲染了“我”這種急切的心態,與此相適應,句式由長變短,焦灼感“追擊我,打壓我,迫害我”,將“我”惶惑不安的心情推向頂點。接著中心句的出現,成為“我”由絕望到振奮的轉折,“我”深知尋求之難,卻篤信“它自有秘徑”。在經歷過情緒的暗夜后,“天色大亮”,“我”堅定地走向探尋之路。寫詩手法的引入,使得散文原本松散的結構變得嚴謹,同時也強化了情感變化的戲劇性,大大凸顯了散文的表現力。
類似語詞的重復在《主觀書》中隨處可見,最常見的是“不要”和“請”字短語的重復。這類訓導性的語言表明了作者強烈的傾訴愿望,而傾訴造成了作品強大的語氣流,“讀《主觀書》讀者只有嘆服而無暇反駁”。
獨特的意象。《主觀書》中意象的大量使用亦可看作作家詩歌創作的延續。閆文盛不再似前期創作中將內心想法不加掩飾地說出,而是將觀念和情感外化為一個個新奇的意象或具體的生理感知,調動聽覺、視覺、觸覺和嗅覺等感知覺來傳達復雜經驗。例如對身處困頓的描寫:“有時我正從外面回來,屋子里電話響了,夜風吹滅了燭燈,開門的一瞬,我覺得饑餓像一個小神,它捆綁了我,訓斥著我,指導著我。”作者為心靈的焦灼狀態營造了一重客觀化的處境,漆黑的夜與空蕩的鈴聲渲染出無邊的孤寂,這一情境觸發了“我”的“饑餓之感”。作者用“饑餓”這一生理感覺喻指精神上的迷惘狀態,并將之擬人化為“一個小神”,“我”被動地接受它對“我”的統治。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將抽象的情思具體直觀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讓原本深奧隱秘的內心世界變得親切可感。
除了喻指抽象情感的這類意象,文中還存在更為蘊藉深廣的意象。作家善于從生活現象中發掘生活的底蘊,從客觀對象的具體形態中發現內在深刻的人生內涵,創造出包含著個體經驗又超越個體經驗的、更強烈地反映了人生內容的意象。例如《瞬間記》中,“我”走在離開家鄉的路上時,回想起自己曲折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人跡渺茫,大雪困村,日暮獨步,我看著南山,憂戚頓起。”“我”從現實離別的“路”中看到了孤獨艱難的人生之“路”,又進一步從不變的“路”中發覺時空的變遷,引發世事如煙的感慨。“我”曾在自己的路途里開天辟地,創造輝煌,可有限的人生終究無法與無限的時空相抗衡。“路”的意象在此涵括了“我”個人的體驗,也指向人類“以有涯追無涯”的終極困惑。
《主觀書》中的意象往往單獨散布于各個篇章,而有時也會以密集的形態構成一篇完整的散文。此類散文可謂之“獨語”,它擺脫了傳統的寫實摹寫,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者的藝術想象力,借助象征、變形……創造出由意象群體構成的主觀世界。于是在這類散文里,“我”可以化身“天地洪荒”時的“一粒草籽”,也可以變為“坐擁江山”的一個“自由神”,或是“萬物黯淡之處”的“一只甲蟲”,一個“被植入無用之用的魔瓶”的“試驗品”……意義模糊的奇特意象傳遞著作者最為個性化的存在體驗,直逼靈魂最深處。
《理想的黃金》就是一篇由意象組成的散文,核心意象“黃金”象征作者全力追求的理想。出身農家,我從未見過“黃金”,由于環境的困囿,“我”并不知理想為何。“世界之大,我遍訪宗匠,他們指我明路”,“我”通過閱讀滋養了精神世界,逐步在平凡的生活中樹立不凡的理想。可面對殘酷的現實,“黃金哪里有用”?“我陷身絕壁”,與如同“野狼”般的強大現實苦苦搏斗。多少年過去,“靈魂的墓穴”依然遍尋不得。我漸漸懂得,有時“學點醫學”——治愈精神之傷,就是“黃金”;“日常生活的流水”——瑣碎平凡的幸福,“更勝過黃金”。“我”不再“孑然獨行”,而是希望“找到引路人的后裔”,在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協助下,修正自己對于“黃金”的定義。現實是“奔騰的洪水”,應當“動員全軍抗洪”。“我”努力把自己從絕境中拯救出來,“到熱帶雨林”找尋“生命的源頭”。這一系列豐富意象的使用,擴充了散文的思想容量,使散文可在短小強悍的篇幅中展現更為復雜細膩的情思變化。
三、從狹小向博大突圍
縱觀閆文盛的散文創作,不難發現,這些作品皆是以自我為對象,寫盡一己之悲歡。他深刻意識到了自己的寫作格局相對狹小,并努力追求更高層次的散文理想,即實現“從狹小向博大的突圍”。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從不諱言我的生活之‘小。我也從不諱言在巨大的社會格局之中,這些隱語般的‘小很難上升。若是長久以來,我無法遭遇更深刻的精神契機,那濁浪滔滔卻無法洞徹的龐大‘現實必會將我湮沒其中。”他深知“自己的心靈遠遠沒有達到博大的境界”,“它局促、狹小、飄忽不定,就像我的生存一般”。因此作家希望心靈博大,希望能夠寫下這個時代的一些大元素。他采取的策略并不是轉向對時代的正面切入,而是進一步深入自我的探究,希圖通過“無限之我”揭示“大世界和大宇宙”。《主觀書》的部分篇章已顯示出這種轉變趨勢。例如《歧義志》中,“我”發現了人類普遍的生存心態:“排除不了做一個隱者的渴望,帶著內心的曲折,覬覦浮華的物質。”作家從個人化的體驗中提煉出人類的普遍困境。
在談及對自己影響深刻的作家時,閆文盛視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為第一知己。同普魯斯特、梭羅類似,佩索阿也是一位專注于心靈涉險的經典作家。其代表作《惶然錄》假托會計伯納多·索阿雷斯之名,深入對內在自我的探知,幾乎窮盡了思考的每一個角落。他以“一己之身直面人類的終極困惑,通過小我的書寫揭示了整個時代的不安”。閆文盛深受此書的啟發,希望能寫下一部類似的心靈之書,這成為《主觀書》的創作緣起之一。
閆文盛與佩索阿有著深刻的精神相通之處,二人的思考皆觸動了人類的生存隱痛。佩索阿說:“我是群體的組合,我們的存在是一片巨大的殖民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各別相異的思想和感覺全都共處其中。”于是,他“以他者的身份和視角檢視自己的寫作,尋求一種自我懷疑和自我對抗”。這一能力也是閆文盛所竭力追求的:“通過化身他人,變換于不同的人文視角,以達到對人世萬物的深切關懷。”《無限性》則表達了閆文盛的此種愿望。當“我”沉醉在“對于自我的無限追尋”中時,“我”疏遠了現實,而當“我”卸下思考的重擔時,“我便成為每一個人”。只有作家意識到他人的客觀性和差異性時,方能走出孤立的神的囈語,從容面對駁雜世象。作家正艱難地尋求自我突破,他不得不與以往創作慣性為敵,一步一步邁向更為廣闊的創作天地。
閆文盛是一位具有沉潛氣質的嚴肅作家,他行走于鄉村與城市的縫隙之中,深切感受著時代轉型帶給個人的生存痛感,他將這種孤獨的生命體驗轉化為歲月的文字留駐心間,在寫作中逼近靈魂的自由高蹈之境。在多年的文學創作中,他始終貼著地面飛翔,探索內心宇宙,在自我矛盾與掙扎中,堅守在夢想與時代的理性,從少年維特的煩惱走向“浮士德”式的思考。他的痛苦與分裂,也是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難題;他的個人探索,愈到深處愈切入到人的共性問題。當時代的浪潮鋪天蓋地地將人群卷入浮躁與欲望的荒漠,閆文盛安靜的訴說無疑為人們業已麻木的神經吹來一股清爽的海風,這氣息中也許裹挾著粗礪的砂石,也不乏咸澀的味道,但正因如此,才凸顯出其敢于直面慘淡人生的可貴品質。如果我們通過閱讀閆文盛的文字滋養了感受痛苦的能力,那“久久的凝視”,便無疑“會把我們心靈的防線打通”。
或許,正是由此出發,我們方能理解閆文盛作品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