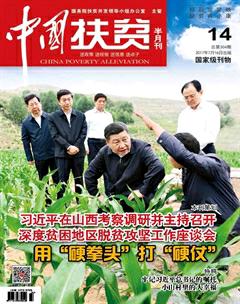決戰深度貧困的貴州解法
顧海凇+鄧萬里
路好,車比預計到得早。薄霧中,白墻灰瓦的洋樓閣院,若隱若現。遠處,綠松林、格桑花,不復往日石旮旯。
這里是六盤水市大灣鎮海嘎村,地處烏蒙山連片特困地區,平均海拔超過2400米,是貴州省海拔最高的一個村。
與高寒環境同樣出名的還有貧困。海嘎360多戶人家,7年前人均年收入還不足1600元。
2010年春節過后,駐村干部楊波來到海嘠。從此,海嘠在基礎設施、人居環境、產業發展全面提速,人均年收入增長到如今的8000多元。
海嘠之變,是貴州決戰深度貧困的生動樣本。
行走貴州山區,筆者常聽到的一個字眼就是“變”。如何變?讓我們一路行走一路探尋。
修路
——西部第一個實現“縣縣通高速”的省份,85%的鄉鎮有了客運站,87.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
貴州從來山多,自山腳到山頂、從這山到那山,綿延不絕的彎道常浮現面前。
山于貴州,曾經沉重。山高,路就遠,層巒疊嶂,擋住的不只是步履。山多,地就少,開荒開到天邊邊,種地種到山尖尖。
修路,曾一度是貴州大山深處老百姓的最大愿望。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思渠鎮,地處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腹地。邊疆村因地處思渠鎮最邊緣而得名。村寨建在一個大函窩里,四面都是山。沒通路前,村里一切東西都是靠人背,從山下到山凹,抄小路也要走個把小時。村民出山,唯一的路是一條掛在懸崖峭壁上的山路,稍不小心就可能滑落百米深淵。
因為交通不便、條件艱苦,村里的小學一直無法留住外來的教師,三年級以上的孩子只能到十幾公里外的學校就讀,住最遠的孩子天沒亮就得出門,放學回家已是黑夜。
2015年前的近十年時間里,村民齊心協力陸續鑿出了一條土路,但由于常年滑坡,汽車根本無法通行。
隨著脫貧攻堅不斷向極度貧困地區深入,政府用兩年時間,于2016年修通了邊疆村的水泥路,并逐漸完善農村客運設施,如今從村里到鎮上坐車只需20多分鐘。
邊疆村的出山路,是貴州改善農村交通基礎設施的生動縮影。
作為我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貴州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93%。山阻水隔的封閉環境,使貴州經濟社會長期相對欠發達、欠開發。
要實現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必須千山萬壑起通途。
2014年,貴州開始實施農村公路三年行動計劃,至2016年底,全省已實現87.5%的建制村通硬化路,85%的鄉鎮有了客運站,建制村通客運率達90%。
一路通,百業興。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打破了經濟發展的最大短板,貴州在發展的道路上越跑越快,“人暢其行、貨暢其流”也逐漸從夢想照進現實。
在平塘縣東部,坐落著貴州唯一的毛南族自治鄉鎮——卡蒲毛南族鄉。由于常年身居大山,毛南族同胞特有的佯美酒、“毛南三酸”只能深在閨中。如今公路修到了家門口,四面八方的游客如約而至,品賞著特別的風味風情。
同在平塘縣,一只“天眼”將這份改變演繹得更加淋漓盡致。2016年9月25日,被譽為“中國天眼”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在平塘縣克度鎮正式啟用。當地政府通過修建直達公路、打造配套設置,“無中生有”地將這一科研項目變成了熱門的旅游景點。
要想富,先修路。貴州把這樸素的道理化作了實際行動。一個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卻在交通建設上創造了多個奇跡。
2015年12月31日,貴州提前三年實現縣縣通高速的目標,成為西部地區第一個實現縣縣通高速的省份,也是全國為數不多實現這一目標的省份之一。
同時,貴州在航空、高鐵、水運等交通建設上全面推進。曾經單一、匱乏的貴州交通運輸正在立體化、快捷化、多元化。
行走貴州山區,山依然在那里,而路卻不再迂回。崇山間不時閃出高橋長隧,條條新路,山色一新。
產業
——因地制宜提升產業現代化水平,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產業扶貧覆蓋面不斷擴大、產業脫貧帶動力不斷增強
7月,地處烏蒙山區的娘娘山綠意盎然。
娘娘山下的六盤水市普古鄉舍烹村,這個曾是“貧困”代名詞的村寨,如今處處散發著生機與活力。
“以前從沒想過,我們的土地能入股,在村里還能當股東、當工人!”舍烹村村民劉美芬說,她和丈夫之前一直在浙江等地打工,老家的農業園區建成后,家里的10多畝山地全部流轉,夫妻倆在園區上班,每年收入六七萬元。
如今,在舍烹村,像劉美芬一樣,幾乎90%的村民擁有“股東”和“工人”雙重身份。而在5年前,舍烹村如同其他偏遠貧困村一樣——缺資金、缺技術、缺產業、缺致富門路,村級集體經濟空心化。
“這一切都源于‘三變改革。”娘娘山聯村黨委書記陶正學說,所謂“三變”就是“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2012年5月,在外闖蕩多年的陶正學返鄉成立了普古銀湖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按照“農戶出資多少,合作社無息借資多少”的入股模式,發動465戶村民籌集2000多萬元資金入股。
此后,合作社逐漸發展獼猴桃、藍莓、刺梨等2.18萬畝,把昔日令人“望山興嘆”的荒山野嶺變成了集生態農業、休閑觀光為一體的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
如今在貴州,“三變”改革模式已在全省得以推廣。“三變”改革變出了農民收益增加,變出了農業結構調整,變出了農村生產力解放。
在決戰脫貧攻堅中,貴州把產業發展作為又一關鍵法寶,廣泛激活農村資源,變“輸血”為“造血”。
全省各地把產業扶貧工作當成第一要務,加快特色優勢產業裂變發展、加強農業園區示范帶動、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升農業產業現代化水平、培育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引進金融資本和完善農業保險等,使產業扶貧覆蓋面不斷擴大、產業脫貧帶動力不斷增強。
同時,廣泛激活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通過示范引導、技能培訓、引導貧困群眾解放思想、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等方式增強貧困地區內生動力、提高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
發展求進,生態要守。貴州立足生態優勢,大力發展優質菜、果、茶、藥、薯和牛、羊為重點的特色生態產業,形成了“東油西薯、南藥北茶、中部蔬菜、面上干果牛羊”的扶貧產業格局。
行走貴州山區,山山水水已成為群眾脫貧致富的巨大優勢。大數據、大生態、大健康等新興產業逐漸成為普通老百姓口中的熱詞。
搬遷
——針對地處深山區、石山區、石漠化嚴重地區的貧困群眾,大力實施易地扶貧搬遷,確保搬遷對象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通過交通改善、產業發展,大部分貧困山區群眾看到了脫貧致富的希望。然而,在一些條件特別惡劣的地方,依然面臨“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困境。
貴州省長順縣代化鎮斗蓬沖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代化鎮境內多為巖溶低山區,坡地石漠化現象極為嚴重,水資源也極為缺乏,70%為深山區、石山區,耕作條件差,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弱。
47歲的斗蓬沖村擺孔組村民陳玉清,一雙兒女在縣城讀書,家里喂了2頭牛和1頭豬,每年收成的1000多斤玉米,僅夠人吃和喂牲口。
在外地打工的年輕人大多不愿回家,有的直接搬離了大山。陳玉清說,這里交通太閉塞,到鎮上趕集要走2個小時山路。“住在深山里很艱苦,早點搬出去,生活才會好”。
和陳玉清身處同樣生活環境的,在貴州省還有上百萬人,這部分群眾的脫貧,是脫貧攻堅戰中的“硬骨頭”。
貴州九成以上貧困人口地處武陵山、烏蒙山和滇黔桂石漠化三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后,就地扶貧成本高,返貧率較高。
搬出“窮窩”,是這部分貧困群眾的最好出路。
貴州針對條件十分惡劣的山區,圍繞 “建房難”“就業難”“拆除舊房復墾難”三大難題探索破解途徑,大力實施易地扶貧搬遷,真正讓搬遷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2016年,長順縣瞄準深山區、石山區、邊遠山區“三山”地區貧困戶,實施貧困村和災害村整村整組搬遷。分別在代化、廣順等鄉鎮建設易地扶貧安置點7個,建設住房累計170647.48平方米,搬遷貧困人口5572人。
斗蓬沖村擺孔組在整組搬遷之列,村民陳家華一家也因為這次搬遷住進新民居。
“住的是小青瓦、黃粉墻小樓,瀝青路延伸到家門口,路燈、綠化跟縣城里沒什么兩樣。”陳家華家中,只見寬敞的房間干凈整潔,堂屋內沙發、電視、冰箱等一應俱全。
如今,在代化鎮,一片新的移民新村拔地而起。搬遷出來的村民生活逐漸步入正常,還實現了就近就業。
針對搬遷戶,貴州堅持“挪窮窩與換窮業并舉、安居與樂業并重、搬遷與脫貧同步”的思路。貧困戶通過到當地企業和產業園區就業、到公益性崗位就業、由政府組織規劃培訓后外出務工等渠道解決就業,確保有勞動能力的農戶均有1人以上穩定就業。
自2001年起,貴州已累計搬遷近150萬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全省還將完成39萬余戶162.5萬人的搬遷安置……
行走貴州山區,一場扶貧搬遷攻堅戰正在徐徐展開。越來越多的山區群眾搬出大山,過上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