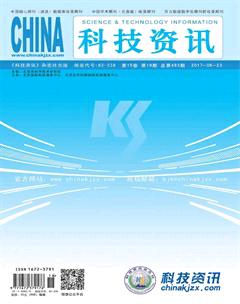大學生“工匠精神”探析①
劉忍
摘 要:在大學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行為已經初步具有了方向性和創新性。在強調“專、精、深”的專業密集型的大學教育中,“工匠精神”的內涵附著性已經越來越重要,這就要求工匠精神回歸到大學生主體。另外,這也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必然要求。工匠精神不是宏觀的口號,而是切實與實踐相結合,成為大學生的自覺,為社會個體的發展打好基礎。
關鍵詞:工匠精神 價值回歸 大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7)06(c)-0197-02
自古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推崇工匠精神,在現代社會,其依然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符號和文化象征,其內涵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愈加豐富和創新。在機械團結的現代化社會,社會團體的增加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使得“工匠精神”一詞被普遍使用。盡管如此,“匠”的核心內涵依然不變。在社會認同和人們認知日益嚴格的今天,如何將工匠精神真正回歸到主體本身,是極具現實意義和順應時代要求的。
1 工匠精神的內涵
從具象的視角看,社會有多少分工種類,便有多少種職業化的“工匠精神”;從抽象的視角看,工匠精神的原型即內核卻是一樣的,其也稱為“癡人”精神,是一種職業人格和職業態度,是職業技術的內化和升華。從外顯的技能“匠”到內隱的“理念”,是“匠人”到“匠心”的遞進,更是“術”與“道”的形神一致。
從培育方式來看,工匠精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的結論化的傳授方式,一種強調主體間際的人格化的領會能力,其可以稱為創造生成性的。奧斯瓦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認為,西方曾有兩種文化模式:一種他稱作阿波羅式的Apollonian;一種他稱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前者認定宇宙的安排有一個完善的秩序,這個秩序超于人力的創造,人的意義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維持它;后者則把沖突看成是存在的基礎,生命是阻礙的克服,認為沒有了阻礙,生命也就失去了意義,其把前途看成無盡的創造過程,不斷改變。這兩種文化觀念可以用來對比傳統結論化的工匠精神和創造生成性的工匠精神的差別——前者是集體產物的代表精神,依靠長期的共同學習和無差別的灌輸來影響個人的思維模式和相互行為,這種“無差別”使人感覺耳熟能詳,倒背如流,甚至成為自動的固化模版印在人的腦海中。在這些親密的群體當中似乎每人都達到了工匠精神的境界,其成為一種公式或者形式化的參考藍圖,但是工匠精神的實質內容卻未必凸顯。
而創造生成性的工匠精神是從集體走向個人的表現。工匠精神應是屬于個人的精神理念,是每個人對所從事行業的探險,是帶著興趣的主動探索。它跟傳統結論化的工匠精神不同,前者對問題的了解可以停留在某個預設的層面,但后者對問題的探索卻是不停止的,是不斷追求的。用浮士德式的文化立場來說,生命力越強,生活的意義也愈深。創造生成性的工匠精神最大的益處是能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隨時適應變化,它不以最終結果為目的,不脫離勞動,是生活經驗的創造,也可以說是生命意義的創造,是活的,能動的,持續依賴于推陳出新,不斷的克服阻礙,也是不斷的發現阻礙,它的動機是在于這一個過程,而目的卻不是這過程的結果。“能動”的工匠精神也在每一個“活的”人身上生發。創造生成性的工匠精神是從教化中將主體內在的精神潛質激發出來,使得主體主動的服膺于屬于自己的道德法則,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
2 工匠精神的價值回歸
在傳統社會中,生活是穩定的,很少有新的沖突,人們的生存依賴于傳統的、既有的不變模式,是一種類似于低等生物的新陳代謝作用,通過代際的承接來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典型的例子是事業的父死子繼——農人之子恒為農、商人之子恒為商、富人之子依舊富,那是一種職業的承續、身份的繼替、財富的傳播,是依賴于經驗的積累。而在當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人并不能只靠經驗作為指導,而需要依賴超出固化的單一體系或個別情境的原則,因此重要的不是經驗而是專屬個人的智力和專業。費孝通說過,“孩子碰著的不是一個為他方便而設下的世界,而是一個為成人們方便所布置下的園地。他闖入進來,并沒有帶著創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沒有個服從舊秩序的心愿[1]。”這句話很好的應用在當下工匠精神對學生主體的滲透上,是口服的并非是心服的,因為工匠精神并未分工,并沒能嵌合入不同的主體心中那一塊凹槽之上。
而現代社會已經顯現出了一種觀念:專業分工將會成為一種符合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相對的行為規范,同時在意識層面上,還會被當做是一種責任。無論是政府公務員、醫生、教師還是電工、泥瓦匠、保姆,凡是違反這種規范,雖說不會受到法律的處罰,但必然會受到公眾輿論的譴責和自我良心的懲戒。為了能夠更好的完善個人和促進社會進步,我們必須擁有更為有效的力量。這種有效的力量并不是各自為戰,而是那些稱職的人,他們追求的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各行各業有所成就的人,他們是把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邊界分明的工作中去,他們各安其業,不遺余力的深耕著自己的一片園地。
這種專業分工的教育理念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不能把所有孩子都束縛在統一的“工匠精神”氛圍中,好像他們將來注定要有同一的精神理念似的,而要因材施教,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找到自身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瑟克雷說:“要想完善自己,就得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讓自己完全適應自己的職業…我們要完善自我,絕不在于自得其滿,絕不在于我們在于去贏得聽眾的掌聲和一知半解者的贊譽,而在于我們各盡其責,在于我們再接再厲地繼續我們的工作的能力[2]。”教育不斷的專業化,工匠精神的不斷分工就體現了這樣一種觀念。總的來說,無論是時代的要求還是觀念的進步抑或是社會的變遷,我們應該感覺到這種氣息已經來臨,工匠精神在當下應該采取這樣一種形式,即各為其用、各盡所能,它暗示了主體先驗的呼聲——人應當各司其職,各盡其用。
3 工匠精神的培育方式
傳統的教育理念是在傳播工匠精神,是要符合公認合式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并不是讓學生領悟工匠精神,找到合我的、合目的的自由行動。這樣的工匠精神只是社會或個人所積累的經驗的延伸,人有學習的能力,上一代的經驗結果可以教給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的積累出一套模式化的“工匠精神”。對個體來說,在他找到屬于他的工匠精神之前,就已經有人替他準備好了一套似乎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配”。這套標配并不是個體根據興趣、方向自行設計或逐步發現的,就像給老虎準備好的食物太多,以至于老虎自身都不會找尋獵物,失去本能了。
當下是一個社會格局發生變化的時代,是史上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變化速率最快的時代,是一個充分競爭的時代,人的意義更加賦予了重要性和主動性,在教育過程中理念的因素決定了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反對教育工作者對學生自我的系統性干預應該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一樣,重分尊重學生的意志自由,用那只看不見的手把工匠精神間接的挖掘出來。如果我們對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加推究,只按著規定的要求做,而且不會懷疑和思考它的個體受用性,那這套體系化的“工匠精神”也就成為我們所謂的“儀式”了。傳統的“工匠精神”是從外限制人的,這就決定了它是極其缺乏穩定性的,一旦有外力打破,就會土崩瓦解。就像人可以逃脫法網,甚至還會感覺自己驕傲,得意。
在課堂教學環節方面,工匠精神是一種主體自發的行為,是生成性的而不是建構性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模式缺少工匠精神生根發芽的土壤,在教學過程中,知識的“傳授”這種教學方式還是為大多數教育者和學生所習慣,是一種單向的過程,在關系方面,是師對生的,教對學的,說對聽的,主體對客體的,主動對被動的,這種模式之下我們忽略了學生作為人的主動自發性,強調的是記憶,是一種接受,是注滿一桶水的教育模式。工匠精神是一種主觀的自發生成的理念,絕不是通過機械性的模仿或復制就可以出現的,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強調學生主體的地位,在教學關系上要改變傳統的認識,強調的是主體對主體,學生本身就是主體,這是一種通過引導的方式,柏拉圖的“產婆術”的方式,充分激發出人本身的自由意志,是人的一種先驗認識能力。在關系方面,這是一種雙向的互動,是點燃一把火的,在交流中碰撞出靈感的火花,使之產生興趣、激發活力,而這恰恰是工匠精神生發的源泉。
工匠精神應該是每個主體的個人自覺力與內心感受,是首先內化于心的對行業或個人的價值標準,不應該被認同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每個人的同一行業規范,否則就難免淪為口號式的宣傳標語。中國當下大學生由于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首先接受的是齊一的教育模式,是通識教育具有的系統化、統一化的知識體系,是知識面上的拓展,卻未曾教育職業分工化。因此大學生普遍理解的工匠精神是學習上的精神,是刻苦、勤奮、努力、用功這些概念。工匠精神并未真正的激活到每個人內心,并未形成職人的理念。工匠精神應該是一種自信,這是職業化的工匠精神的二次回歸,這種工匠精神自信的源泉應是從生命體驗中來,從價值觀中來,從社會交往中來,從社會文化中來,工匠精神不只是天才的專屬稱謂,有了精神自覺、精神自信,精神活力,每個普通人也可以是工匠。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蘊含著能量,但是,只有當一個人有方向的時候,能量才能轉化為力量。“工匠精神”的主體回歸才真正有了意義。
參考文獻
[1] 費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 埃米爾·涂爾干.渠敬東譯.社會分工論[M].三聯書店,2013.
[3]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