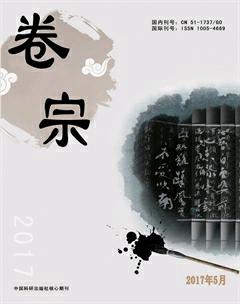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鬼神的新發(fā)展
摘 要:鬼神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huì),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由于其社會(huì)環(huán)境的特殊性,推動(dòng)了鬼神的新發(fā)展。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很多鬼神小說,人們從畏鬼逐步發(fā)展為分辨鬼之善惡,人鬼關(guān)系也更加緊密復(fù)雜。神的方面,出現(xiàn)了眾多的自然神、先祖神和歷史人物神,更興起了一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造神”運(yùn)動(dòng)。本文試圖搜集相關(guān)資料,探討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鬼神的新發(fā)展。
關(guān)鍵詞:鬼神觀念;靈魂不滅;鬼神信仰
1 早期的鬼神觀
我國(guó)的鬼神思想古而有之,原始社會(huì)時(shí)期早期的鬼神觀念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由于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自然認(rèn)識(shí)的相對(duì)落后,再加上萬物有靈觀念的影響,人們?yōu)榱私忉屪陨硭焕斫獾囊幌盗鞋F(xiàn)象,自發(fā)的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宗教神秘,這種宗教神秘就是早期的鬼神思想。到了夏商周三代,鬼神思想持續(xù)發(fā)展,殷人尊神,逢事必問天,事無巨細(xì)必行占卜,甚至可以說殷商就是“神主時(shí)期”。在殷商時(shí)期更是形成了系統(tǒng)的天神、地袛、人鬼的鬼神觀念。到了姬周時(shí)期,周公制禮樂之禮,成為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的基本制度,因此周人尊禮尚施,但同樣敬鬼神,詩經(jīng)的《綿》、《皇矣》等篇就明確表達(dá)了一種人卑神尊的思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鬼神觀系統(tǒng)化的過程繼續(xù)發(fā)展,這一時(shí)期人們把祭祀天地與崇敬祖先相結(jié)合,稱為“敬天尊祖”。由于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分裂時(shí)代的特殊性,各地域文化不同、風(fēng)俗各異,造成各分裂政權(quán)間鬼神的存在形式與表現(xiàn)形式紛雜不一,一些禮樂制度之下產(chǎn)生的鬼神在消逝,地域性質(zhì)的鬼神卻大量產(chǎn)生。再加上神仙觀念的出現(xiàn),人們開始追求仙術(shù),崇尚長(zhǎng)生不老,更加促進(jìn)這一時(shí)期仙怪內(nèi)容的發(fā)展。秦漢時(shí)期大一統(tǒng)專制王權(quán)的強(qiáng)化,天人理論急劇發(fā)展,天被塑造成為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人、鬼三者共存的局面更加為人們接受,上至統(tǒng)治貴族,下至貧苦百姓,均重鬼信神。秦漢時(shí)期的鬼神就已經(jīng)具有具體形象,在劉向編訂的《淮南子》中,其中多處用鬼神以伸戒。鬼神思想一直在流傳并發(fā)展著,并不因政權(quán)替換而有所中止。
2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鬼神觀
鬼神觀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有了大發(fā)展,如果說魏晉之前還只是那么些“孤魂野鬼”的話,那么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真的可以算得上是“群魔亂舞”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除了志怪小說如雨后春筍一般蔚然大興之外,在“鬼”的性格及形象上較之前代亦有很大不同。同樣的在“神”的方面,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不僅繼承了前代流傳下來的神的觀點(diǎn),更在這一時(shí)期開展了一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造神”運(yùn)動(dòng)。
(一)鬼、神產(chǎn)生基礎(chǔ)理論的完善——從“靈魂不滅”到“神不滅論”
《禮記·祭法》中載:“大凡生于天地之間皆曰命,其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皆所不變也。”1[1]這充分肯定了人死后形體雖腐,但是精神不滅,人的靈魂是可以獨(dú)立于形體所存在的觀念。但是這都只是一些零散的觀點(diǎn),并未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關(guān)于神滅還是神不滅這一問題,引起了佛、儒兩家的大爭(zhēng)論,佛教主張形盡神不滅,反佛者主張形神俱滅。廬山僧慧遠(yuǎn)繼承前代關(guān)于靈魂不滅的觀點(diǎn),又融入佛家輪回學(xué)說作《形盡神不滅》一文,使靈魂不滅觀點(diǎn)匯總成為系統(tǒng)的神不滅論。慧遠(yuǎn)之前“薪火之喻”是用來佐證神滅論的,東漢桓譚把人的形體比作蠟燭,把人的精神比作燭火,認(rèn)為人的靈魂隨著肉體的死亡而自然消散,就像燭火會(huì)隨著蠟燭的燃盡而自然熄滅一樣。但是“薪火之喻”最早卻并不是出于這里,《莊子·養(yǎng)生主》說“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2[2]指在這里就是油脂的意思。簡(jiǎn)單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油脂會(huì)耗盡,但是火的傳續(xù)卻是沒有盡頭的。慧遠(yuǎn)吸取莊子“薪火之喻”的理念,發(fā)展出自己的“薪火之喻”,慧遠(yuǎn)認(rèn)為人的精神就是火,形體就是柴薪,一根柴薪消耗完結(jié),火會(huì)傳遞到另外的柴薪上。人的靈魂也是一樣,一個(gè)形體死亡之后,人的靈魂自然也會(huì)傳遞到另外一個(gè)形體里去,因此,人的靈魂是可以不滅的。慧遠(yuǎn)運(yùn)用這一論斷進(jìn)一步駁斥了神滅論者。其后劉宋宗炳作《明佛倫》,進(jìn)一步完善神不滅論。神不滅論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迅速傳播,并形成了較大的影響,這一時(shí)期鬼神觀念的理論基礎(chǔ)就是神不滅論。
(二)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鬼的新形象
東漢之前,鬼大多數(shù)是以厲鬼形象出現(xiàn)的,是讓人畏懼、擔(dān)憂、敬而遠(yuǎn)之的。到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由于鬼神思想的不斷豐富,人們對(duì)鬼怪有了更加豐富的認(rèn)識(shí),更加上這一時(shí)期志怪小說蔚然大興,鬼的形象漸漸符合人的想象,趨于與人相同。這一時(shí)期的鬼更加具有人性,性格也極具分明。人們對(duì)于鬼的認(rèn)識(shí)也漸漸的從“畏鬼”發(fā)展成為“識(shí)鬼”,人們辨別鬼之善惡,對(duì)于善鬼人們感激、祭祀,對(duì)于惡鬼人們想盡方法驅(qū)散。如《列異傳》中次節(jié)與丁伯昭,次節(jié)死后感丁伯昭款待之恩,常送奇異物給丁伯昭家。對(duì)于這樣知恩圖報(bào)的鬼,人們便祭祀他,希望能與他更加親近,以求得到他的庇佑。對(duì)于像“黎丘奇鬼”“鬼子”等等這樣通過蠱惑或者幻化去害人的惡鬼,人們則就畏而遠(yuǎn)之,憤而除之。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鬼”的另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報(bào)應(yīng)觀念強(qiáng)烈,《三輔決錄注》中記載胡軫與游殷有隙,胡軫誣陷游殷,致使游殷被殺,其死月余,胡軫突然患病,并在將死之時(shí)自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3[3]其他的如孫策殺于吉,策常于鏡中見于吉之像等等,像這樣鬼魂報(bào)仇,因果報(bào)應(yīng)的記載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不可勝數(shù)。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人們心中的“鬼”,更加的像人,它會(huì)哭會(huì)笑,有慈善之心、有仰慕之心,但是它同樣有貪婪狡猾、殘忍無情的一面,這一時(shí)期的“鬼”更多的是人們借鬼用以反映現(xiàn)實(shí),人們借鬼的形象側(cè)面的反映了人性的壓抑、社會(huì)的險(xiǎn)惡和對(duì)美好生活的期寄。
(三)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神的新發(fā)展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興起了大規(guī)模的自然神崇拜, 人們認(rèn)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水火、植物等自然之中都蘊(yùn)含著神明,都是需要敬仰的。《三國(guó)志·魏書》注記曰“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4[4]另有《搜神記》卷四云:“風(fēng)伯、雨師,星也,風(fēng)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5[5]人們崇拜自然神、祭祀自然神,一方面希望能得到自然神的庇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面對(duì)自然災(zāi)害時(shí)無力的一種表現(xiàn),人們主觀臆想,萬物有靈,常祭祀之,可免受其害。除了對(duì)自然神的崇拜,當(dāng)時(shí)人們還興起了大規(guī)模祖先神化活動(dòng),魏晉南北朝時(shí)“祖先“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它被賦予了一層神化色彩,他不再是鬼,更像是神,或者說是受神庇佑的人。魏獻(xiàn)明皇后游于云澤,夢(mèng)到日出室內(nèi),欻然有感,果生太祖于參合陂北。更有宋高祖生時(shí)神光普照于室,甘霖自降于樹;齊高祖過驛夢(mèng)于仙游的記載 。對(duì)祖先進(jìn)行神化,一方面增強(qiáng)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適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人們下層民眾的崇神心理,所以為當(dāng)時(shí)多數(shù)統(tǒng)治者所采用。但是人們對(duì)祖先的過度神化,也造成當(dāng)時(shí)人神不分,淫祀盛行的后果。
魏晉南北朝時(shí),由于儒學(xué)的沒落,致使正統(tǒng)信仰缺失,所以人們便開始尋找其他信仰,在鬼神崇拜思想的影響下,一場(chǎng)轟轟烈烈的“造神”運(yùn)動(dòng)在魏晉南北朝拉開了帷幕。《晉書·地理志》載雍縣有五臓、太昊、黃帝以下祠303所,此外還有蚩尤赤松子、伏羲、女媧等上古人物的祠堂,這些傳說中的人物均被當(dāng)作神明,受到人們的祭祀。更甚者姜太公、衛(wèi)靈公、孫叔敖、曹操等著名歷史人物同樣被作為神明開祠祭祀。《魏書·地形志》載,汲縣有姜太公廟、長(zhǎng)垣縣有衛(wèi)靈公祠、安寧縣有孫叔敖廟,均可佐證。這場(chǎng)“造神”運(yùn)動(dòng)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蔣神”蔣子文了。《搜神記》卷五就載有蔣子文的來歷“漢末秣陵縣尉,追賊至鐘山下,賊傷其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6[6]由記載可知蔣子文并非什么杰出人物,甚至可以說才能平庸。但到吳主孫權(quán)初,有人見蔣子文乘白馬,持白羽,立于道,稱自己為山神,要求立祠祭祀,并以讖言迫使吳主改鐘山為蔣山,以表其靈,蔣子文成神由此始。其后宋文帝末年,太子劉劭殺父弒君,為了尋求神靈保佑,又立蔣子文為大司馬、中山郡王。南齊永明中又把蔣子文尊為蔣帝,到陳代時(shí),帝王將相均常去蔣祠祭祀。至此,蔣子文從小小的秣陵縣尉上升到一個(gè)國(guó)家的保護(hù)神。再如“鮑君神”和“李君神”,“鮑君神”只是因?yàn)樯倘四米喵缏沽粝迈U魚未告知獵人而已,小小誤會(huì)便讓人覺得神奇至極,而“李君神”則更只是空桑中長(zhǎng)出李樹而已,都只是一些誤會(huì)和奇異現(xiàn)象,人們便把它們當(dāng)作神靈去祭祀,更加尊以神明稱號(hào)。神明為什么在之一時(shí)期大量出現(xiàn)?因?yàn)樾枰.?dāng)現(xiàn)實(shí)統(tǒng)治者不能給與人民以足夠的保障的時(shí)候,人們就會(huì)把希望寄托于虛擬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世界,他們渴望神明能夠出現(xiàn),能夠給予他們以安定。
3 結(jié)語
從黃巾之亂起,到隋文帝開皇九年統(tǒng)一全國(guó)止,共歷時(shí)405年。在這405年間除了西晉有過短暫的一統(tǒng)之外,其他時(shí)間均是分裂割據(jù)、各自為政。各個(gè)統(tǒng)治者,為了各樣的理由發(fā)動(dòng)著各樣的戰(zhàn)爭(zhēng)。頻繁的政權(quán)更迭、連年的戰(zhàn)爭(zhēng),再加上頻發(fā)的自然災(zāi)害,人們無法從現(xiàn)實(shí)中看到希望的光芒。人們只能在生存困窘與死亡恐懼之下寄希望于鬼神,人們期寄能從鬼神處得到庇佑,期寄著鬼神能夠滿足自己的精神欲求。不安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死亡的隨時(shí)降臨,促使著人們對(duì)死后世界進(jìn)行探索、進(jìn)行假設(shè)。再加上佛道等宗教為了宣揚(yáng)本教理論,不斷對(duì)自身進(jìn)行神化;以及游牧文明的強(qiáng)勢(shì)侵入,民族的融合,更為傳統(tǒng)的鬼神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再加上志怪小說的盛行,人們極力發(fā)揮自己的想象把鬼怪盡可能的具體化,以緩解了人們對(duì)于死后世界的恐懼。這些種種都促使著魏晉時(shí)期鬼神觀的大發(fā)展、大繁榮。鬼神理念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其都是社會(hu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由于人們認(rèn)識(shí)世界、改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kuò)大和加深,人們無法解釋自身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所以便創(chuàng)造出來一種未知神秘,用來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進(jìn)行一系列的虛假反映。雖然鬼神思想是一種陳舊的迷信學(xué)說,但是其并不是一無所用的。首先,其就具有伸戒、勸人行善的作用,鬼神思想中具有強(qiáng)烈的報(bào)應(yīng)觀念,古人崇信鬼魂報(bào)仇之說,因此可以增加人們做惡事時(shí)的心理負(fù)擔(dān),用以減少人們的惡行。其次,其具有維系血緣宗族大家庭的作用,這一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先祖祭祀中,祭祀先祖可以增加血緣大家庭的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便于血緣家族維系親情。其更有精神依托的作用,人們信奉鬼神、祭祀鬼神,通過對(duì)鬼神的訴求,用以消除緊張感、恐懼感,得到精神鼓勵(lì)。任何一個(gè)事物能夠長(zhǎng)期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其都有一定的存在道理。鬼神思想起自上古,流傳至今,其社會(huì)功用是不容忽視的,更是值得我們研究討論的。
參考文獻(xiàn)
[1]朱彬撰.禮記訓(xùn)纂[M].北京:中華書局.1995.693.
[2]郭慶藩撰.王孝魚點(diǎn)校.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3.127.
[3][4][5]陳壽,裴松之注.三國(guó)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9.356,618,42.
[6]干寶.搜神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9.57.
作者簡(jiǎn)介
鄭吉偉(1992),男,漢族,河南許昌人,碩士在讀,河南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文中國(guó)史專業(yè),研究方向:歷史文獻(xiàn)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