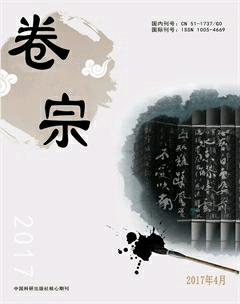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規范與保障
摘 要: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是加強反腐敗力度,實現反腐敗制度化、長效化的體制機制改革。但是,刑事案件需要經歷偵查、公訴、審判程序,缺少任何一環,或者任何一環出現濫權,都不能使改革取得卓有成效。而公訴作為中間一環,其權力的規范和保障具有關鍵性。檢察機關濫用刑事公訴權時有發生,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的體制改革背景下,欲實現改革成效,規范檢察機關刑事公訴權,避免不當起訴或不起訴,實現職務犯罪偵查成果獲得司法確認,職務犯罪得到法律制裁是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同時,檢察機關刑事公訴權在面對強勢的監察權,應當構建其具有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制度。
關鍵詞:監察機關;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刑事公訴權
檢察權從其產生之始,素有防止審判權擅斷和抑制偵查權恣意、保障人權的目的和作用。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在刑事訴訟領域,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檢察院行使公訴權、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即使在檢察院自偵案件中,檢察院行使自行偵查權和公訴權,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在語境的排列組合下,三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依然沒有脫離《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政框架。并且,依我國憲政制度的構建,檢察院行使的檢察權也具有實現溝通偵查權與審判權的橋梁、防止審判權擅斷和抑制偵查權恣意、保障人權的目的和作用。2016年10月27日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強調,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把監察機關提升至一府兩院的地位。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的三地區《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在試點地區設立監察委員會,同時強調監察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明確了監察委員會同一府兩院的平行關系,即人大之下一府一委兩院的憲政構架。《決定》第二條規定:為履行職權,監察委員會可以采取談話等措施;第三條規定: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刑訴法》第三條、第十八條、第一百四十八條以及第二編第二章第十一節關于檢察機關對直接受理的案件進行偵查的有關規定,《檢察院組織法》第五條第二項,《檢察官法》第六條第三項。可以明顯看出,第二條乃賦予監察機關偵查措施的行使權力,第三條乃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檢察院行使偵查權。據此,雖然仍處于試點階段,然而監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極高可能性。監察機關監察對象乃涉及本地區全體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包括檢察院和法院公職人員。“借助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威懾力,檢察機關的濫行起訴行為時有發生,且很少受到法院的制裁。”[1]同理,剝離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可以有效發揮檢察機關公訴權的充分和規范行使。然而,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威懾力從來不因其賦予何處而消減,并配合監察機關其他防腐敗職權,其威懾力,不亞于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威懾力。在我國,賦予監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反腐敗制度化、效率化功能和作用。只是,監察機關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同時,依然應當符合刑事訴訟領域內《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政框架,檢察權防止審判權擅斷和抑制偵查權恣意、保障人權的目的和作用也不因此落空。那么,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面對監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辦理職務犯罪偵查案件時,檢察院公訴權能的規范與保障問題應當獲得應有的討論和研究。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成立監察委員會,專司反腐敗工作,賦予其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反腐敗制度化、效率化功能和作用。但刑事訴訟程序領域,涉及刑事案件,除了加強職務犯罪的偵查權,仍然需要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進行審判的刑事程序,亦即,缺乏公訴權和審判權的合法和合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打擊和預防職務犯罪的目的依然存在落空的可能。公訴權和審判權的合法和合理行使亦可以有效實現在辦理刑事案件時《憲法》第三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公訴權架于職務犯罪偵查權和審判權之間,有效地制約職務犯罪偵查權和審判權。在職務犯罪偵查權隸屬于檢察院時,憑借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威懾力,檢察院有濫行公訴權的情況。但不能說就是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擁有導致公訴權的濫用,剝離職務犯罪偵查權就可以解決公訴權濫用問題。因此,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后,為保證反腐工作有效進行,同樣存在規范公訴權的問題;同時,在職務犯罪偵查權隸屬于檢察院時,紀委督辦反腐工作,查辦后,把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轉交檢察院提起公訴,檢察院例行提起公訴的模式,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監察機關與紀委“合署辦公”的改革方式下,把紀委監察職能上升為國家權力。如此一來,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與檢察院公訴權的關系即是權力與權力的關系,就有權力制約權力的關系,檢察院履行公訴職責就不能同紀委牽頭督辦職務犯罪案件一樣僅履行例行工作,而應肩負起防止審判權擅斷和抑制偵查權恣意、保障人權的職責,據此,保障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的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公訴權的充分和有效行使同樣是保證反腐工作有效進行的題中應有之義。
1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規范
為保證貪污、瀆職等職務犯罪行為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公訴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此過程公訴權應得到規范行使,不被濫用。在打擊職務犯罪過程中,檢察院一旦出現該起訴而不予起訴、不該起訴而予以起訴等濫用公訴權情形時,縱使監察機關具有強有力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力和權力的行使,職務犯罪行為也難得法律應有的制裁。而防止濫用公訴權的兩種方式是突破它或者規范它[2]。我國實行公訴國家壟斷主義,以公訴為主、自訴為輔,而職務犯罪案件不在自訴范圍。因此,不存在“突破它”的可能性,唯有“規范它”。在我國,在職務犯罪案件領域,公訴權濫用并應予以規范的幾種情形應包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起訴;歧視性(選擇性)起訴、報復性起訴、輕微案件不起訴等[3]。
1.1 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起訴及其規范
將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有利于檢察機關不被迫于外在壓力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職務犯罪案件進行立案偵查、提起公訴,有利于檢察機關充分行使公訴權,在審查起訴階段發現監察機關移送的職務犯罪案件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予以退回補充偵查。但,與其他犯罪案件相比,職務犯罪案件的顯性特征在于與政治之間的高度關系,同級之間的競爭、上級對下級的擠壓、該部門對彼部門的排擠,利用刑事手段是最迅捷和有效的方式。監察機關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本身具有獨立性,但是依然不能排除受制政治因素的影響。在極度倡導嚴打腐敗時期,也是其職務偵查權力極度擴充時期,其震懾力和影響力是極強的,為保持政府公信力,為社會樹立政府權威,一絲的違紀違法完全可以啟動職務犯罪偵查權肅清“異己”,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情況下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應當說,司法具有理性性,在社會極度狂熱時期,司法具有糾正之效能。檢察院公訴權是啟動司法裁判的一道關卡,若檢察機關能夠充分行使公訴權,分清罪與非罪界限,查明事實真相,在審查起訴階段消耗不符合職務犯罪構成要件的案件,實現《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互相制約功效,其實質更有利于樹立政府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規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起訴方式在于保持檢察機關同監察機關平行關系,在《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增加規定人民檢察院、監察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六章明確檢察機關對監察機關偵查措施的監督制約程序,第二編明確監察機關立案、偵查、移送審查起訴程序規定,同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應當擴充修正檢察機關辦理職務犯罪案件時關于退回監察機關補充偵查或建議撤銷案件的程序規定。
1.2 歧視性(選擇性)起訴、報復性起訴、輕微案件不起訴及其規范
歧視性(選擇性)起訴在職務犯罪領域指檢察機關在處理職務犯罪案件時采取不同的標準,對于國家機關單位人員或公職更大者不進行起訴或者選擇較輕的罪名進行起訴,而對其他履行公職人員或公職較小人員進行起訴或選擇較重的罪名進行起訴或共同犯罪中,將罪責移嫁給其他履行公職人員或公職較小人員,或者選擇性地起訴或不起書特定地區、特定公職人員或特定職務犯罪等;報復性起訴在職務犯罪領域指檢察機關在處理職務犯罪案件時因過去履行公職產生的糾怨等原因,對特定的不構成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或構成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實施起訴或重罪起訴。輕微案件不起訴應當是與報復性起訴相對,在職務犯罪領域指檢察機關在處理職務犯罪案件時因私情等原因,違反自由裁量權,對犯罪情節輕微,但依法需要判處刑罰或不存在免除刑罰可能的職務犯罪公職人員,應當起訴而不起訴。應當說,無論是歧視性(選擇性)起訴、報復性起訴、輕微案件不起訴都是違反《憲法》第三十三條、《刑法》第四條、第五條基本原則等的規定。
2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保障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保障在于防范監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配合紀委的紀律檢查對檢察機關公訴權的侵濁。該種侵濁會導致檢察院喪失獨立性;《憲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會失去其應有的效力;在職務犯罪案件領域會直接導致只講《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三機關互相配合,而不談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三機關互相制約;“以審判為中心”會淪陷為“以偵查為中心”,導致公訴、審判是確認職務犯罪偵查結果的工具和程序。監察機關對檢察機關公訴權行使的侵濁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監察機關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權,為履行上述職權可以采取談話、訊問、詢問等措施;二是監察機關監察對象乃涉及本地區全體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包括檢察院和法院公職人員。亦即,檢察機關在辦理監察機關移送審查的職務犯罪案件時,也是在監察機關監督的范圍內,監察機關可以監督承辦人員辦理其移交的案件的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情況,甚至是道德操守情況,為此可以對其行使或采取紀律處分、談話、訊問等職權和措施。為此應當防范監察機關明為行使監察權、實為代行公訴權,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公訴權。
3 結語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規范與保障是反腐有效果、人權有保障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的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機關刑事公訴權能充分有效行使方面的體制機制保證。在不當起訴與不起訴方面加強對檢察機關刑事公訴權的規范,有利于監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成果獲得司法確認,有效實現監察體制改革的初衷。在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保障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獨立行使不被侵濁而得以實現權力制約權力,促使檢察院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雙重作用得以發揮。在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監察機關的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院刑事公訴權能的規范與保障兩方面是體制機制改革發揮效用的必要性措施。
參考文獻
[1]周長軍:《公訴權濫用論》[J],法學家2011年第3期
[2]謝小劍:《公訴權制約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30頁
[3]同[2],第118~136頁
[4]林鈺雄:《檢察官論》[M],法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6~97頁
[5]王新環:《公訴權原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50~51頁
[6]王玄瑋:《中國檢察權轉型問題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88頁
作者簡介
賴景峰(1991-),男,福建泉州,漢族,福建師范大學2015級憲法與行政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