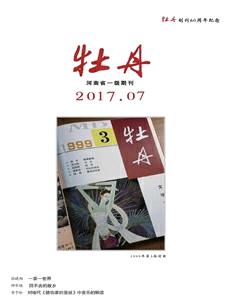解讀虹影《孔雀的叫喊》中的生態女性主義敘事
韓旭東
虹影的中國經驗多表現為袒露中國與對話穿梭,她常將一些中國符號進行鋪排,在重塑中國“神話”的同時也糅雜進一種異質文化的沖撞與對話。在這些可解與不可解的對話之間,有著一種文本的裂隙與歷史的重構。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解讀《孔雀的叫喊》中敘事人所表現出的生態保護意識,并批判了破壞自然與女性的男權文化。
饒芃子在《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國意識》一文中對虹影的創作做出了如是評價:“我們必須要面對越來越多的無關中國意識的海外作家,如近年來相當活躍的虹影,她的作品幾乎看不出一點海外的痕跡,她追求的是一種世界性的風格。”無疑,這段話將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世界、本土/世界經驗割裂,說明文學創作在抹去本土化、在地化的痕跡時,有可能通向一種更為廣闊的世界性眼光——即世界文學的書寫面向。虹影屬于這類作家,她的經驗既以中國本位的本土女性化話語為書寫基礎,更重要的是融入了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代表了一種海外的視野及書寫實踐成果。
“無關中國意識”表明虹影在創作時并非將自己的視野局限于國家、民族、自我的一種小范圍書寫視域,而是以中國經驗、中國場景為一種現實的鏡片,通向一種世界文學的書寫可能。“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最早源于歌德《塔索》的法譯本,這一能指如今已經變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研究的話語基礎,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也發生了諸多的變異。從學科語匯釋義的角度看,世界文學既指林立于世界文學史上的那些經典傳世之作,且經過了時間的考驗,在藝術價值上得到了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肯定,在世界各國已經家喻戶曉,如《人間喜劇》《傲慢與偏見》《源氏物語》《百年孤獨》等;它又指以世界主義為視角,觀照本民族文學的研究,在這種雙向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一種跨文化閱讀的效果。從創作經驗與作品主題上看,虹影更符合第二種世界文學的概念。她的作品譜系具有兩條線索:其一,書寫個人經驗,袒露自己家庭的故事,將自己成長過程中的體驗付諸于文字表征。如《饑餓的女兒》《好兒女花》《小小姑娘》等。其二,譜寫與自己個人身份無關的故事,將古舊、近代的中國展現給世界,同時也表現出一種異質文化之間的對話,如《上海王》《上海之死》《孔雀的叫喊》《阿難》等。因此,何謂“世界性”、如何“世界”、怎樣“文學”,也就變為解讀虹影非“自敘傳”小說的一個有效視度。
在第二創作序列中,虹影的中國經驗多表現為袒露中國與對話穿梭。她常將一些中國符號進行鋪排,在重塑中國“神話”的同時也糅雜進一種異質文化的沖撞與對話。在這些可解與不可解的對話之間,有著一種文本的裂隙與歷史的重構。中國、歷史、記憶和現實在此譜系中都變為了世界。也就是說,虹影筆下的中國是與世界密不可分的,中國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這回答了比較文學學科建制過程中對世界文學合法性的疑問:世界文學的研究是否以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為比較視閾產生作用的話語基礎?
在葛浩文所翻譯的《饑餓的女兒》英譯本中,他將該部作品的題目譯為the daughter of the river——大河之女。葛氏的翻譯揭開了虹影在這部作品的潛文本中所要表達的含義:“多余人”六六不僅是母親和生父所生的女兒,生于重慶的她更強調自己的本土身份,除了家庭之外,她更是南方的女人、重慶的女兒。她的書寫不僅表現了身為女性自身的一種性別、家庭、社會境遇,更重要的是要以小見大——她寫的是重慶,這也是虹影的小說為何在大陸發表當年能夠得到家鄉人民“力挺”的一個重要原因:她的經驗不只是個人的,更屬于群體。同樣,在描寫三峽故事的《孔雀的叫喊》中,虹影也做出了這樣的表示:
從199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建三峽大壩起,我的心就沒法平息。我是長江的女兒,我是三峽的女兒。我一直有個愿望,想寫一本關于三峽的書。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
在書寫完《饑餓的女兒》后,她擴大了自己的創作視野,不僅要表現個人經驗,更要書寫國家經驗,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家國同構。在此,她是“三峽”的女兒,所以《孔雀的叫喊》所要表現出的世界眼光是將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重大政策——三峽大壩的建立——呈獻給世界,表現出一個華裔女作家在書寫中國經驗時所具備的一種宏大視野與人文關懷。
無論是重慶的朝天門碼頭(《饑餓的女兒》《好兒女花》),還是三峽大壩以及貧民棚戶區(《孔雀的叫喊》),虹影的創作都離不開“水”——即長江。長江/大河/水作為一種原型出現在《孔雀的叫喊》中,本身便承載了一種文化、人文情韻。“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識屏幕上的散亂的印象,這些意象構成信息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統一。原型就是一個象征,通常是一個意象,它常常在文學中出現,并被辨認出作為一個人的整個文學經驗的一個組成部分。”以長江為典型代表的河流意象,在這部作品中不僅是作為一個創作切入主題出現的——故事所要表現的背景是對三峽大壩的改造,更重要的是河流所承載的哺育功能,它與母親形象是合二為一的。它不僅是重慶的代表,也為養育兩岸人民而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強調以大河文明、農耕文明為中心的中國,河流基本等同于生育與生命意識。“集體無意識是指人類自原始社會以來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經驗的長期積累,它既不產生于個人的經驗,也不是后天獲得的,而是生來就有的。這是一個保存在整個人類經驗之中不斷重復的非個人意象的領域。”對河流的認同,對水文化的青睞,是中國人自出生以來便蘊藏在腦海中的一種無意識,保護河流、保護長江,便等同于保護自己的母親、母國。同時,在這部作品中,長江的出現也與女主人公柳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誕生于長江,她的母親在懷孕時曾與父親在這個地方工作,且紅蓮與玉通的冤案也發生在這個地方。柳璀需要通過對自己身世的揭秘,一步步抵達歷史真相的所在,還原真相的前提條件便是回歸自己的出生之地——長江。
如果把河流原型——長江等同于中國人/柳璀的母親,符合客觀規律的做法是保護母親河,這就等同于對自己國家、國族的認同。但是,《孔雀的叫喊》偏偏以改造自然、人定勝天、經濟利益大于一切等口號為基礎,要對長江進行一番大改造——建立三峽水電站。按中國道家哲學的角度看,無為而無不為,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想要獲得經濟平穩健康的發展,需要以生態的平衡為前提條件。順應自然規律,保持長江原有的模樣,才是符合“道”、符合生態規律的做法。以柳璀的丈夫李路生為代表的一群人,為了經濟的發展以及滿足自己的私欲,打破了這種道統。文本在書寫長江、三峽之前,先以一種旁敲側擊的筆法給出了一個已經被破壞的自然境遇——北京的沙塵暴:
柳璀放下電話,這才注意到窗外有點異樣,玻璃窗上蒙著灰垢,剛才還可看到樹的綠色,現在看起來像一些牽牽掛掛臟舊的抹布。平時她只注意到實驗室必須一塵不染,絕對符合基因實驗的標準,全封閉空調恒溫。今天才發現辦公室的窗戶有一點縫,在往里瀉淺黃色的微粒。
她已經習慣了沙塵暴,但站在研究所門口的石階上,街上的場面還是讓她吃了一驚。整個城市涂上了一層土黃色,空氣中有一股土腥味。能見度只有百米左右,層層疊疊的高樓大廈一個個消失在灰霧中。連樹都被壓低了,長枝條隨風抽打著路沿。所有的車都打開了霧燈,緩慢行駛。行人偶然冒出,有如鬼魂,一個個蓬頭垢面,側身走在漫天風沙中。下落的夕陽有點像月亮,卻蔫蔫的,暗黃。
人類對于自然的破壞,已經遭到了自然的報復。由于過分開發自然環境,砍伐森林,北京的天氣已經變成了以灰黃色為主的暗黃天色。北京是柳璀生活、工作的地方,在北京她是一個異鄉人,自己的家庭情況始終是一個謎。要想揭開自己的身份問題所隱藏的真相,她必須由北京這個異鄉回到自己的精神“原鄉”——長江。
生態女性主義強調女性與自然的根本關系,探討女性與自然同被宰制的意識形態關聯性,認為男性對待環境或自然的方式與其對待女性的方式有著相似之處,即把二者皆視為可掠奪、占有的資源,號召女性作自然環境的保護人,宣稱人類與自然萬物都有其個別的差異性存在,提倡不以性別歧視或人本主義的觀點污損自然的原貌。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以女性主義為理論的論述基礎,承認男性文化、男權文化為主導的同時,將女性與自然等量齊觀,把二者視為在男性強權話語社會下被欺凌的、被侮辱的客體。人類對自然的侵犯與侵害,就像男性對女性的壓制與規約。這種觀點的言外之意,也將改造自然、破壞自然的力量等同于男性話語。在《孔雀的叫喊》中,以母親為原型的河流意象在文本中是被社會力量、男性力量所改造、改化的客體,二者進入了一種二元對立式的格局中:長江河流/社會力量、男性/女性、主體/客體、強勢/弱勢,這一組格局中的長江,即母親河形象已經完全被雌性化,這不僅是由于以生育繁殖為特點的河流本身所具備的一種功能特質,更是由于她也是男權社會、強勢話語下被掠奪的客體。父權文化將婦女自然化,通過宗教、藝術及文學,將婦女視為等同于物質自然的被動而低等的群體,理應服從創造了人類文化的男人的統治,婦女與自然皆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遭到嚴重的傷害。這種高等對低等的掠奪與侵害,主要表現為環境的破壞:
實際上長江里漂浮的塑料品、墊箱子的泡沫塊,甚至爛床墊,已經到處可見。柳璀可以想象水庫存水后,塑料泡沫塊漂流多少月也沒法沖入大海。李路生弄什么“花園施工”名堂!先管管這些臭烘烘的垃圾吧!
同時,以李路生為代表的一群人實質上是破壞自然/女性的男性文化的縮影,他們不僅將國家改造三峽的錢與港臺商人融資,私自發行債券而從中獲取暴利,更是不管不顧底層百姓的生存境遇,一味地中飽私囊。長江、三峽變成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噱頭,它們是男權話語下被無情掠奪的寶藏:
李路生處理這一切的才干真是絕妙,他干政治顯然最為出色,絕對會不安于搞技術,甚至不會安心做經濟、做管理,他能把一切事情做得讓參與的人信心十足,熱情高漲,最后不僅是一個投資的問題,而是把整個三峽工程弄成一個“成績”——他不僅要成功,更要耀眼的成功。
以李路生代表的工業化力量,在對自然改造的同時,也破壞了長江原有的生態環境。改造的背后,是一種個人權力的獲取與鞏固。長江改造、三峽大壩雖然是利國利民的百年工程,在實踐中,卻變成了一些人集權過程中掩蓋骯臟的噱頭。這是宏大官方話語敘事下被遮蔽的暗角,虹影的三峽書寫表達了一種在地人民言說故鄉變化的可能,畢竟在以報紙、網絡為代表的官方媒體上不可能看到這樣的“邊緣吶喊”。
(天津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