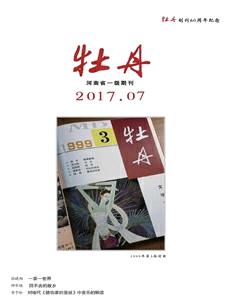美麗心靈
王菠
王爾德在其童話故事《快樂王子》中塑造了兩個至美的人物形象,故事以收獲不朽而美麗的鉛心和小燕子被安放天堂收尾,充分展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輝,包含了王爾德“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主張,但是故事的結局再次落到了道德的層面上。本文通過探尋王爾德藝術自律的審美語境,著重從人物塑造、結局的角度分析其與唯美主義的聯系,證明童話故事的結局與王爾德本身主張的藝術自律性相違背。
一、王爾德的審美語境
奧斯卡·王爾德的名字幾乎可以稱為19世紀后期歐洲唯美主義的代名詞。而唯美主義運動是現代西方審美精神逐漸發展的結果。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就強調恢復人性、肉體、感覺、心靈和智慧的地位。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不僅掃除了一切超驗的、昏暗神秘的東西,還培育出啟蒙運動現代性的對立面——審美的現代性。法國思想家盧梭指出:純粹理性的啟蒙運動聽不見或窒息了天然情感的聲音,因而達到了它無神論和利己主義的道德;知識的增長、人生的美化只是使人越來越不忠實于他的天職和他的真本性。他呼吁人們回到淳樸的、天然的情感中去,回到純真的、生機勃勃的自我中去。德國作家歌德同樣站在審美感性的立場上,以《少年維特的煩惱》為代表,抨擊平庸、鄙陋、充滿清規戒律的社會現實。盧梭和歌德的文學創作成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運動的先導。這一時期藝術審美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反抗,得到來自德國古典美學,尤其是康德、席勒美學的支持。德國古典美學的奠基者是鮑姆嘉登,發展到康德美學,其實質上的獨立才得以完成。康德認為,審美判斷是直觀的、自由的、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而后席勒提出了“審美游戲說”。1804年,貢斯當首次將“為藝術而藝術”筆錄于自己的日記中。戈蒂耶在小說《莫班小姐》的序言中,闡述了藝術無目的性、無實用性的觀念,被歸入“為藝術而藝術派”。
戈蒂耶之后,“為藝術而藝術”有三層意思:一是強調藝術獨立于認知活動、倫理判斷之外;二是捍衛藝術的純潔性,拒絕藝術通俗化、商業化;三是藝術被文化精英當作精神寄托和思想避難所。19世紀60年代,法國唯美主義思潮開始傳入英國。美國畫家惠斯勒、英國詩人斯溫伯恩在傳播過程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法國唯美主義思潮的刺激和引導下,英國本土也培育出了自己的唯美主義思想,湖畔詩人柯勒律治、威廉·布萊克和約翰·濟慈被視為英國唯美主義的先驅。之后,約翰·羅斯金和沃爾特·佩特對唯美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英國唯美主義的后起之秀,奧斯卡·王爾德承襲了戈蒂耶、佩特等老一代唯美主義者的基本觀點,堅持藝術的獨立和藝術自律。
二、王爾德的藝術自律性
王爾德認為,藝術創作是完全自律的,具有獨立的生命,而且純粹按自己的路線或者美的規律發展。1889年,王爾德在《謊言的衰朽》中首次提出“生活模仿藝術”,將藝術設定為第一性,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美學思想藝術創作對現實生活的依賴,賦予藝術創作以絕對的自由。他指出:“撒謊作為一門藝術,一門科學和一種社會樂趣,毫無疑義地衰朽了。”并且,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撒謊說”:“撒謊——講述美而不真實的故事,乃是藝術的真正目的。”他用“撒謊”一詞來表述藝術創作的特質,為藝術構建一個自由王國,將真實與否的問題徹底放逐出去。
另外,對于藝術自律,王爾德認為藝術與道德分屬兩個不同的范疇,藝術與道德功利無關。在《道連·葛雷的畫像》的序言里,王爾德說:“藝術家是美的事物的創造者。”同時,他還說:“藝術家也沒有倫理上的好惡。”在他看來,真正的藝術家為了純粹個人的愉悅才進行創作,在創作過程中,除了藝術本身的完美,任何東西都不會讓藝術家感興趣。并且,他還指出:“書無所謂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書只有寫得好的或者寫得糟的,僅此而已。”他甚至說:“一切藝術都是不道德的。”在王爾德看來,藝術作品作為美的載體,是超道德的。只有徹底擺脫功利道德的影響,才能真正建立符合唯美主義理想的關系,因為“藝術除了表現自己之外,不表現任何東西”。但是,在王爾德的作品中,作者一方面追求為藝術而藝術的崇高唯美主義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為道德服務的陷阱。本文以《快樂王子》為例,探討王爾德的藝術自律和撒謊的藝術,以此證明王爾德的作品與其主張的藝術自律性相違背。
三、藝術自律性與《快樂王子》
(一)美麗的王子
王子有著美麗非凡的外表。他滿身貼著薄薄的純金葉子,藍寶石的眼睛,紅寶石在劍柄上燦爛地發著紅光。作者字字珠璣地塑造了王子唯美的外在形象,正如王爾德特別重視美的形式,用閃閃發光的寶石和金子襯托王子華麗的形象,因為美的形式給人感官上的愉悅。在王爾德看來,藝術的美就在于它的形式,形式就是一切,是至高無上的藝術目標。而康德認為,從質上看,美是主觀的,它不取決于對象的感性存在,只與對象的感性形式相關。審美是無功利的靜觀,這就是主體的態度。市參議員認為王子像風信標那樣漂亮;母親告訴自己的孩子快樂王子不會哭著要東西;失意的人羨慕快樂王子的快樂;孤兒院的孩子們想象著快樂王子來自于天堂,是個天使。作者借用各個階層的人們的羨慕和仰望進一步升華快樂王子的形象,那是一種色彩絢麗、華麗非凡的美。在此,快樂王子被王爾德塑造成為美的代名詞、美的化身,正是作者所認為的“藝術除了表現自己之外,不表現任何東西”的真正體現。
然而,在王爾德看來,美的形式也有助于思想的表達、感情的傳遞。唯美主義強調靈肉合一,在王爾德的童話故事里真,正的美是心靈的美。任何美的事物的最高形式又必然是心靈美。所以,作者先把快樂王子塑造成美的化身,然后又添筆墨呈現快樂王子美麗、善良的內心。他不只是供觀賞之用的雕像,更是善良的天使。王子讓小燕子給在發高燒的孩子送去他劍柄上的紅寶石,孩子便甜甜地睡去;把一顆藍寶石的眼睛送給饑寒交迫的劇作家,另一顆送給賣火柴的小女孩,劇作家露出快樂的樣子,小女孩笑著跑回家去了;就連身上貼的金子也一片一片啄下來,送給窮人,此時小孩的臉頰上出現了紅色和笑容。王子無私地奉獻了自己最寶貴的東西,給他人送去關愛和溫暖。王子失去了華麗的外表,卻收獲了一顆散發美麗光芒的心靈。王子美麗的心靈,雖然體現了王爾德所追求的藝術理想——藝術至上,至善則至美,但是更重要的是這顆至美的心靈散發著人類道德的光輝,作者沒辦法單純地只為了創造美的藝術形式而創作,他給予王子善良的心靈,就是賦予了作品以道德的形式。快樂王子的塑造最后依然沒有逃離道德,無法單純作為美的載體,無法超越道德的范疇。
(二)美麗的小燕子
作者沒有塑造小燕子美麗的外表和高貴的出身,但是給了小燕子一顆柔軟善良的心。它首先愛上了一束蘆葦,但是蘆葦不愿跟它一起遠走高飛。這一情節的設置,作者讓讀者看到小燕子的可愛和童真,為后來遇到英俊的王子并為他留下埋下伏筆。只有心中充滿了愛,才能以滿滿的愛去愛別人。
當它看到快樂王子眼里裝滿了淚水,小燕子的心里充滿了憐憫,因為王子看見了窮人,痛心不已而潸然淚下。小燕子雖然跟王子說它的朋友在埃及等它,它也得盡快飛過去。但是在王子的哀求下,它看見王子憂愁的面容,它答應做王子的信差。小燕子的出現引出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它放棄了一次次去埃及的理想,給窮人帶去快樂、幸福,而自己寧愿挨凍、挨餓。小燕子用自己的善行收獲了美麗的心靈。王子一點點變丑,沒有了往日華麗的外表,不再受到稱贊和仰望,但是小燕子依然不離不棄守護在王子身邊。尤其是在王子失明之后,小燕子動情地表示“你現在瞎了,我要永遠陪著你”,他們至美的友誼令人感動。小燕子用盡最后一點力氣飛到王子面前,它親吻了王子的嘴唇,然后跌在王子的腳下。凄美的愛情故事令人落淚,但是至美的場景、凄美的愛情,也是王爾德美的一種表現形式。美麗的心靈、至美的友誼和愛情再次深化心中有愛才是美的主題,即至愛則至美。作者營造出來的至美和至愛的情節,不僅讓讀者領略了人間的真善美,更使讀者迷失在炫美的童話中,沉浸于藝術世界的謊言里。作者所創造出來的童話,恰恰就是王爾德所說的“撒謊說”,即講述美而不真實的故事。
(三)美麗的結局
快樂王子為天堂帶去一顆珍貴的鉛心,小燕子也在天堂里安睡。這一美麗的結局,沒有讓讀者完全絕望,而是看到了王子和小燕子都有了好的歸宿和結局。作者在看到美毀滅的同時,依然設置了對美的希冀,為讀者描繪出充滿希望的美麗畫面。小燕子和王子死亡的結局正是作者眼中生命之美的頂點,這樣的結局也恰恰體現了王爾德對美的無限追求。
在王爾德看來,藝術真正的目的是撒謊,即虛構的想象力。只有藝術家脫離了現實的糾纏,沉浸于想象力的世界,才能創造出真正的藝術品、真正的形式。但是,童話故事的結尾和所謳歌的內容,處處與道德有關,處處體現道德的內容和歸屬道德的范疇,快樂王子雖然失去了華美的外表,但是獲得了永遠不能融化的鉛心,小燕子犧牲自己給別人帶去快樂和幸福,不離不棄地陪伴在快樂王子的身邊,心靈至美,所以上帝安排他們進入天堂。他們的善良、無私、自我犧牲、博愛和純真的愛都是道德的真正體現。童話寓意深刻,顯露出唯美的主題,但是恰恰違背了作者的初衷,作者依然最后落腳于道德之上,因為心靈和外表的契合才是至美。作者無法只為了藝術而藝術,也無法在自己構建的藝術自律王國中獨善其身,因為唯美主義者對于真善美的追求從來就沒有變過,作者也從來沒有完全忽視道德和良知。
(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