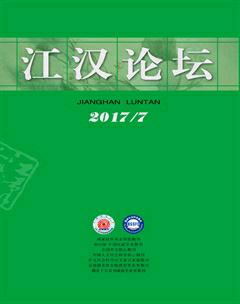國有企業的創新障礙與現實選擇
湯吉軍+張壯



摘要:在我國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國有企業對促進發展動力轉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承擔著重要責任,企業間競爭的關鍵手段并不僅僅是價格,更為重要的是創新,創新對每一個企業來說都是生死攸關的。但是,國有企業創新面臨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有待打開的“黑箱”,已經成為亟需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本文從交易成本角度來分析國有企業創新面臨的障礙問題,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產權屬性、壟斷特質、沉淀成本等是導致國有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培養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國有企業管理者,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降低國有企業沉淀成本數量,是提升國有企業創新能力的現實選擇。
關鍵詞:交易成本;國有企業;沉淀成本;創新障礙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7-0005-06
一、交易成本對國有企業創新的影響機理分析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在國有企業創新的動力、激勵、方式、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但大多忽視了交易成本。如果沒有交易成本,那么由科斯定理可知是不會存在創新經濟問題的,即使是國有企業也是如此。“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①。之所以會發生交易成本,主要是來自人為因素與環境因素相互影響下所產生的市場失靈現象②。事實上,交易成本真實存在于國有企業生產、銷售、分配等各個環節上,在國有企業總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毫無疑問對國有企業創新有著重要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
為了更加深入理解國有企業的創新問題,可使用供求模型來闡釋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如圖1所示。
圖1展示了交易成本是如何影響國有企業創新的。D表示國有企業創新之前市場對國有企業創新的需求曲線,S表示國有企業創新之前國有企業市場供給曲線,兩條線相交于均衡點E,均衡產量為Q,均衡價格為P。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一方面,國有企業創新行為會導致生產成本下降,產品供給增加,這樣供給曲線將向右下方移動,變為供給曲線S1;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創新行為會導致產品功能增強,消費者需求增加,這樣需求曲線將向右上方移動,變為需求曲線D1,供求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均衡點E1,均衡產量為Q1,均衡價格為P1。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況下,同不存在交易成本情況相比,一方面,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會增加產品的總成本,導致產品供給數量會低于無交易成本情況下的產品供給數量,這樣供給曲線S1將向左上方移動變為供給曲線S2;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會使產品價格上升,導致產品需求數量會低于無交易成本情況下的產品需求數量,這樣需求曲線D1將向左下方移動,變為需求曲線D2,供求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均衡點E2,均衡產量為Q2,均衡價格為P2。從動態角度看,從最初的均衡點E,向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均衡點E1變動,再向存在交易成本的均衡點E2變動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存在交易成本與不存在交易成本情況下的均衡水平明顯不同,存在交易成本的均衡水平(點E2)代表著更高的均衡價格P2和更低的均衡產量Q2。因而可以看出,交易成本導致國有企業創新有效供給不足,對國有企業創新起到阻礙和約束作用。
二、交易成本如何阻礙國有企業創新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交易成本廣泛存在于國有企業的各個環節,大大減少了創新收益。如果一個經濟體中存在較高交易成本,就不可避免地阻礙經濟體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制度影響了組織行為,導致創造性破壞的發展,這個過程發展了技術并引起社會財富的增加③。但是,我國國有企業目前仍然存在官僚化、行政化、封閉化、大企業病、競爭和危機意識不足等諸多弊病。通過深入挖掘產生這些問題背后的原因,發現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存在重大問題,而體制機制問題產生的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的性質。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公有產權屬性、壟斷特質和沉淀成本等問題的存在,導致國有企業在科學決策、搜尋信息、公關談判等各個環節產生大量的交易成本,成為制約國有企業創新的痼疾。
1. 國有企業的公有產權屬性
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Holmstrom(1989)則認為創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產的特殊屬性:不可預見性或不確定性、風險性、異質性、長期性和人力資本密集性④。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國有企業產權是指國家或政府可以根據與資本的聯系,對其施加控制和控制性影響的各種企業中歸屬國有的部分產權,這種產權性質決定了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激勵創新的中長期制度設計,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委托—代理問題嚴重。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即為全體國民所有,表面上看產權很清晰。但是,這樣的國有企業產權事實,既不是全體國民所有,也不是國有企業員工所有,所有權主體國家只是一個抽象的集合體的模糊概念。從理論上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全體國民,但是這個所有者十分分散和力量薄弱以至于無法實施監督功能,代理成本使股東(所有者)與經理人(代理人)之間產生利益沖突。由于國有企業存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監督鏈條也不會導致出現最終的委托者,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并不能完全消除代理成本,國家無法真正約束國企經營者,無法真正實現國有企業的“法人化”、“企業化”和“國有化”,難以直接行使國有企業所有者的權利,社會和公眾也無法對管理者起實在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從而使代理問題更加復雜。然而,創新具有高度風險性、不確定性和長期性等特征,產權不明、權責不清的公有產權屬性導致國有企業創新控制權與創新收益權相分離,又由于短期增加的創新投入而產生的長期收益并沒有明確的享有者,這樣不利于強化國有企業長期的創新行為,也不能有效激勵經營者和技術骨干的創新熱情。因而,不論從邏輯還是實踐上,國有企業創新受到很大約束,從而造成國有企業創新不具有可持續性。
第二,國有企業產權結構不合理。產權結構狀況對企業的創新行為和創新效果能夠產生直接影響,我國國有企業雖然進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的負面影響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產權主體單一,產權市場不發達,國有產權涉及范圍過廣,國有企業內部變相私有化,在原始技術創新利益分配上不明確等一系列問題,導致國有企業的創新動能和創新效果等方面缺乏有效激勵。所以,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不合理,激勵機制存在扭曲問題,使得國有企業從上到下創新的積極性不高,也直接影響集中大量雄厚科技實力的研究機構參與國有企業進行原始創新的可能性。
第三,國有企業具有封閉性。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證明開放性和流動性對國家經濟發展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隨著國有企業規模日益龐大,憑借政治地位實現壟斷市場之后,就越來越僵化封閉、固步自封,不再鼓勵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排斥外來進入者,設置貿易壁壘,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通過政治身份和壟斷地位,排斥市場競爭的策略,雖然可以獲得短期利益,但長期利益將受到損害,導致很多優質資源無法利用,整體運行效率下降,競爭力明顯不足,最終喪失創新活力。在人才使用方面,國有企業封閉性表現尤為明顯,實施“蘿卜招聘”,“國二代”、“國三代”現象比比皆是。實踐證明,通過關系網結成封閉性小圈子,排斥外來競爭,導致用人方面的逆向選擇,人力資源錯配,造成巨大人才浪費,從而導致國有企業沒有真正的創新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將會更加依賴外部行政和政治權力做大,而不是由內生要素做優、做強,其結果是侵蝕國家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 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理性選擇
Shleifer(1998)指出,當所有權為政府所有時,企業經理通常沒有激勵進行降低成本和改善質量的創新投資⑤。國有企業經營者往往扮演著經濟人的角色,作為理性的決策者,國有企業經營者會根據私人收益與私人成本的比較來決定自身行為,只有當決策行為的預期收益超過其預期成本時,國有企業經營者才會采取行動。
第一,政治利益最大化。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是由政府委派,且具有一定任期和行政級別,與其說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是一個企業家,不如說是一個政府官員。國有企業這種高度等級化的管理體制,使得經營者無法真正按照市場的方式進行決策,導致經營者工作的主要目標是迎合上級偏好,滿足上級需要,而不是以追求創新、提高效率,為國家和社會創造財富為目標,抑制了國有企業長期創新發展。同時,每一級行政級別都代表的是利益和特權,特別是可以享受到一種橫跨政商兩界的利益和特權。對于大多數理性的國有企業經營者,追求職務晉升,追求行政級別,追求特權待遇要比追求企業創新、經濟效率更為重要,這使得國有企業經營者把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貨幣等用在謀官謀權上,而在冒風險創新的精力投入上明顯不足,因而國有企業創新動力不足。
第二,經營行為短期化。一方面,缺乏股權和分紅激勵的長期辦法。創新活動不同于一般的生產性活動,它往往具有長周期、高風險、高投入及異質性等特點⑥。國有企業的公有產權屬性不能有效激勵創新的長期行為,國有企業經營者很難享受到增加短期創新投入而產生的長期創新收益,受益主體不明確,容易出現偷懶和搭便車現象。因此,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理性選擇是那些能在短期內帶來收益、風險小又能顯示政績的投資項目,而那些長期創新項目,由于缺乏投資激勵,這類項目往往投資不足,造成創新效率的嚴重損失。另一方面,經營行為短期化導致國有企業經營者普遍存在不穩定感。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位置是任期制,并且任命的標準也不完全依據企業家精神的高低和經營者長期績效的好壞,這樣國有企業經營者對未來普遍缺乏長期穩定的預期。國有企業的無效率主要是缺乏對管理者的有效監督和激勵機制⑦。目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考核制度,也存在考核短期化的缺陷,不論是年度考核還是任期考核,都不能有效解決創新激勵長期動力問題,而且這種考核制度還增加了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不穩定感,這種不穩定感會嚴重妨礙國有企業的長期創新行為。
第三,追求風險最小化。國有企業管理者不是市場篩選的產物,而是國家任命的政府官員,這些人的競爭意識、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偏好普遍較低,往往是典型的風險厭惡者,他們往往會減少影響個人發展的創新性風險投資項目。創新本身就是一項風險很高的長期性活動,投入不一定有產出收益,甚至還可能失敗。一旦失敗,創新投入將無法收回,國有企業效益將會遭受重大損失,并直接影響國有企業管理者的經濟利益、政治地位和未來的政治前途。所以,理性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在面對高風險的創新項目時,當他無法確信創新能否成功,能否享用創新利潤時,他最優的選擇是選擇風險最小、見效最快,能帶來回報和顯示政績的短期非創新項目,而那些風險大、周期長,在任期間難以見到效果的創新項目不是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理性選擇,因而國有企業經營者往往會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不利于企業創新的決策。
3. 國有企業的壟斷特質
柯茲納曾指出壟斷會對創新機會的發現產生不良影響,政府限制自由進入市場,甚至限制利潤水平與收益率,這樣做將直接導致經濟無效率和產生混亂,將減少利潤機會被關注的概率。由于壟斷的存在,消費者的需求變化被注意到時候會更晚,技術創新出現并被采用速度也會更慢⑧。目前,幾乎所有主要的行業,例如國防、電力、石油、電信、煤礦、銀行和保險等都是由國有企業占主導,大部分屬于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企業。這類國有企業前期需要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入行門檻很高,民營企業往往無法與之競爭,這就造成天然壟斷。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普遍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具有行政壟斷偏好,利用權力和地位(尤其是優先權)壟斷市場,獲得壟斷利潤,阻礙潛在市場競爭和創新發現過程,阻礙高管發揮創新精神。因而,在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創新惰性”問題。
第一,政府庇護下的國有企業壟斷,分散創新重視程度。國有企業自產生以來,就與政府在聯系和對話上具有天然優勢,國有企業獲得政府資金支持、政策補貼、市場主導和廉價生產要素比較容易,從而導致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壓力,創新動力不足是其致命的缺陷。這是由于擁有政府的授權和保護,人為設置限制競爭者進入的壁壘,國有企業獲得行政壟斷權,獲得利潤更為容易,沒有降低管理成本的內在動力和有效約束,因而會在尋求保護的活動中投入過多,必然分散國企高管發現新知識和新技術創造利潤的重視程度,不但扭曲資源配置,而且無形中抑制了國企高管的發現和創新精神。比如,歧視性許可收費不僅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創新激勵,而且產生了創新激勵扭曲效應。
第二,缺乏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壟斷,扼殺創新積極性。波特在其《國家競爭優勢》中指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是否在某些行業里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大型企業⑨。然而,占據我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國有企業雖然經歷了商業化、公司化和兼并,仍然政企不分,不需要為創造市場而競爭,感受不到強烈的生存競爭壓力,沒有優勝劣汰的危機感,法人治理結構仍然一股獨大,沒有形成適應市場化結構和競爭格局的現代企業制度。由于有效競爭不足,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擁有定價權,無論產品是否創新,價格是否合理,市場消費者都要被動接受,不用擔心經營效率低下或缺乏創新而面臨破產倒閉,存在嚴重的軟預算約束這樣的道德風險問題。引進新設備、開發新產品或進行管理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對于國有企業生存不是充要條件,因為沒有競爭壓力,市場需求剛性,壟斷利潤獲取方便。因此,壟斷國有企業廣泛存在高價格、高利潤、低產出的低效率現象,而且嚴重抑制競爭性發現過程,阻礙技術創新和擴散,扼殺創新原動力。而且,國有企業憑借其行政壟斷獲得的市場優勢,更容易同外資進行合資合作,國有企業在技術、產品和市場上更加依賴跨國公司,從而進一步助長國有企業的“創新惰性”。
第三,尋租下的國有企業壟斷抑制創新動力。創新只是獲得利潤的一種方式,國企經營者通過權衡發現尋租比創新更有利可圖。Guriev(2004)強調,賄賂會給腐敗官員提供制定更多繁瑣規則的足夠激勵,這顯然妨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了企業創新的交易成本⑩。由于一些部門和相關官員在國有企業中存在部門利益,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方便,國有企業創新受到條塊分割的制約,國家投入的大量資金、資源寧可分掉,也不愿冒風險去創新搞研發,進而導致創新投入不足,創新效率、創新成果轉化和國有企業創新激勵受到重大影響。另一方面,腐敗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國有企業同樣在政府擔保和金融機構貸款等方面存在腐敗行為,甚至有些高管人為設租,給創新設置重重障礙和關卡,增加了創新的交易成本,成為國有企業創新的“絆腳石”。同時,國企高管一般是哪里有錢賺就朝哪個方向工作,很多高管將他們的創新觀點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壟斷和改變規則上,往往通過采取措施,限制對手采納新技術,以維持自己的特權和壟斷地位,這樣會大大提高進入市場壁壘,從而降低國有企業的創新動力。
4. 國有企業沉淀成本的存在
沉淀成本(Sunk Costs)是指一經投資承諾,便無法收回的那部分成本。國有企業的生產要素專用性很強,比如,人員、設備、廠房由于市場不完全很難轉為他用,會產生很高的沉沒成本,因此,沉淀成本在國有企業是普遍真實存在的。
第一,不存在沉淀成本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創新情況。假設一個國有企業采用新技術(用N來表示),保持當前舊技術(用O來表示)。使用新技術,效率高,成本低,但是需要購買相關的技術和設備并重新進行人員培訓,這部分沉淀投資或專用性投資很大。用VC表示采用新技術的操作成本,用I表示前期投資成本,兩者相加小于繼續使用舊技術加上前期投資的成本,國有企業基于節省成本考慮將采用新技術,其條件為:VCN+IN 其中,IN-IO=ΔI,VCO-VCN=ΔVC。(1)式表明,國有企業采用新技術的條件是,采用新技術新增投資成本ΔI要小于采用新技術節約的操作成本ΔVC;反之,國有企業依據成本收益計算,將不會采用新技術。 第二,存在沉淀成本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創新情況。假設國有企業在舊生產技術上已經做的沉淀投資為IO,它在舊技術上的操作成本為aVCO(0 (2)式表明,只有當新增投資 ΔI,加上沉淀成本[(1-a)VCO+ IO]之和,要小于采用新技術節約的操作成本ΔVC,新技術才會被國有企業采用,沉淀成本可以得到補償;反之,國有企業由于缺乏技術和制度創新的激勵,將不會采用新技術,前期投資的沉淀成本將得不到補償。 第三,比較(1)式和(2)式兩種情況,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同新增投資ΔI大小成反比;二是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同節約操作成本ΔVC 大小成正比;三是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同沉淀成本大小成反比。當沉淀成本存在時,國有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時不能忽視沉淀成本的存在,如果沉淀成本過多,國有企業將會對當前舊技術模式產生路徑依賴,直接影響未來的創新活動。 三、交易成本視角下國有企業創新的現實選擇 在交易成本理論視角下,判斷國有企業體制機制優劣,創新能力強弱有兩個基本因素:一是交易成本問題;二是獎懲機制問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鼓勵國有企業創新, 重在重構國有企業獎懲機制,鼓勵國有企業員工追求個人目標,同時也能實現國有企業創新的總體目標,實現兩者目標的有機結合。 1. 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 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市場經濟就好像一部創新機器,憑借利益驅動,實現優勝劣汰,激勵整個社會提高效率。那些效率更高,更能滿足消費者需要的企業將會獲得更好的回報,獲得市場的認可。這樣,市場機制會以強有力的方式激勵國有企業創新,并決定其生死存亡。迄今為止,己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國有經濟生產效率和資金利用效率下降,甚至對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產生了拖尾作用。因此,國有企業必須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趨勢,在堅持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的大方向下,對于競爭性國有企業要完全按市場規則來運作,不再承擔公共職能,使之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首先,政府必須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種種偏袒和保護。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最有希望推動創新活動的方式,就是減少非生產性或破壞性尋租行為的收益。嚴格按照市場規則,減少行政干預,真正實現資源配置市場化,職業經理人市場化,薪酬制度市場化。國有企業要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依靠市場價格機制,迫使國有企業不斷進行創新,激發豐富的創新能力。其次,完善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以體制機制改革為手段,在治理結構與體制機制設計上,要嚴格按照現代企業治理的基本要求,建立黨組織、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職代會有效制衡協調的現代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明晰股東、董事會和經營者的責權利關系,特別要明確董事會同經營者之間監督和被監督關系,真正保障股東權益,構建“黨政工”民主共治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為國有企業創新奠定堅實基礎。最后,要大力推進落實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加強體制機制創新,進行資產重組,實現股權多元化,使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有機融合,對激發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力,提升國有企業創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2. 培養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國有企業管理者 長期以來,企業家始終在為經濟增長提供關鍵性的技術突破,企業家精神一直被視為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與經驗相一致,實證證據也表明,在產出和生產力增長進程中企業家的作用至關重要。首先,為國有企業管理者提供適合創新的環境。要促進創新型企業家的出現,自由、公平和法治的環境對創新非常重要,產權保護嚴格,法治健全的環境,將鼓勵國有企業管理者去創新而不是去套利。通過市場來選擇國有企業領導人,面向世界遴選最優秀、最有信譽的國有企業經營者。其次,盡快建立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市場。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Hart)在談到債轉股時說,破產企業(高杠桿企業)不是公司本身有問題,而是經營班子出了問題。因此,國有企業改革要向世界汲取職業經理人市場的治理經驗和教訓,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同時,必須增加透明度,對敏感信息進行定期披露,財務、人事等信息可以通過現代的信息手段讓全民進行監督。最后,要重構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激勵約束機制,通過改變他們面對的激勵,創造允許失敗的創新氛圍,遵循市場經濟和人才成長規律,施行定期輪換制,讓企業家的創新潛能充分迸發,這是國有企業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3. 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
經濟新常態下,國有企業改革要提高競爭力和創新力,必然涉及到反壟斷和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改革。首先,要設定國有企業合理的邊界,首要目標是彌補市場失靈。如果國有企業定位不明確,國有企業將到處擴張,擠占民企生存空間,而且會出現“國進民退”和“與民爭利”等問題。因而要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從那些不涉及國家重大安全領域退出來,積極發展民營企業,在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服務、金融服務、國防、電力、電信、鐵路、航空和石油等行業開放,從而提升潛在競爭程度。只有國有企業定位清晰,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獲得生存發展,而不是通過尋租方式謀求發展。其次,國有企業要保持開放性。目前,國有企業日益封閉,在選人用人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國有企業要實現創新發展,就需要同其他企業開展人才競爭,而保持開放性,利用市場篩選,是打破國有企業壟斷,獲得優秀人才的一種有效辦法,這才是提升國有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所在。第三,鼓勵國有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與合作。引入競爭機制是提高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打破其壟斷地位的一種有效方法。國有企業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依靠創新提升產品品質,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采取參與、合作、并購和聘請國外專家等方式,引進、消化和吸收國際先進科技成果,為提高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服務。
4. 降低國有企業沉淀成本數量
如果國有企業創新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那么通過價格機制就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就會獲得充分的創新激勵。然而,國有企業背負巨大的沉淀成本,國有企業創新會不同于標準競爭性模型,從而使創新激勵不充分。所以,降低各類沉淀成本數量是促進國有企業創新的一種重要方法。首先,積極構建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加快形成統一開放、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可以大大降低資產專用性程度和不確定性,盡量消除生產要素市場進入與退出壁壘。這樣不僅可以激勵國有企業增加創新投資,而且還會提高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其次,要大力完善非市場治理結構。采取重新簽訂契約,確定國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合并重組和所有權重新配置等方法,降低經濟性和體制性沉淀成本。最后,充分發揮政府處理沉淀成本的作用。政府要采取適當的退出政策,引導國有企業轉型升級。比如,加速折舊、繁榮二手市場和穩定未來預期等,減少沉淀成本對國有企業創新的影響。此外,政府還要制定管理沉淀成本相關政策。比如,搭建公共信息共享平臺、完善社會安全網絡、進行人力資源再開發、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減少沉淀成本和未來不確定性,增加要素的流動性,為國有企業創新提供良好條件。
注釋:
①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Economica, 1937, 4(16), pp.386-405.
② O.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③ [美]蒂莫西·耶格爾:《制度、轉型與經濟發展》,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頁。
④ B. Holmstrom, Agency Costs and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9, 12(3), pp.305-327.
⑤ A. Shleifer, 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4), pp.133-150.
⑥ D. Hirshleifer, A. Low and S. H. Teoh, Are Overconfident CEOs Better Innovato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4), pp.1457-1498.
⑦ J. J. Laffont and J. Tirole,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 MIT Press, 1993.
⑧ I. M.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⑨ 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頁。
⑩ S. Guriev, Red Tape and Corruptio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2004, 73(2), pp.489-504.
戴靜、張建華:《金融所有制歧視、所有制結構與創新產出——來自中國地區工業部門的證據》,《金融研究》2013年第5期。
湯吉軍:《沉淀成本效應與國有企業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12年第9期。
作者簡介:湯吉軍,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長春,130012;張壯,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長春,130012。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