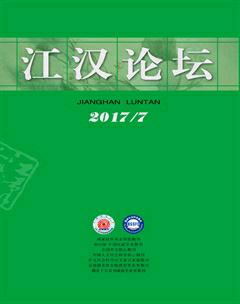論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
張三元+孫虹玉
摘要: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深入發(fā)展,資本及其邏輯已經(jīng)深度地“植入”并“融入”到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之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不同就在于能否以及如何駕馭資本邏輯。倫理調(diào)控是駕馭資本邏輯不可或缺的手段。資本邏輯和倫理雖然有對立的一面,但也存在著內(nèi)在聯(lián)系,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借鑒和運用資本邏輯以及市場經(jīng)濟的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從而使倫理調(diào)控成為可能。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的基本進路是: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根基,實現(xiàn)道德規(guī)范的制度化,弘揚社會主義道德。
關(guān)鍵詞:資本邏輯;倫理調(diào)控;中國道路;社會主義道德
中圖分類號:B82-0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7-0031-08
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深入發(fā)展,中國已經(jīng)事實上進入到世界資本邏輯的中心,資本已經(jīng)深度地“植入”并“融入”到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之中。毫無疑問,我們已經(jīng)無法回避資本及其運行規(guī)律這個客觀現(xiàn)實了。雖然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但兩者具有質(zhì)的不同,中國道路以西方發(fā)展道路為基礎(chǔ)或前提,但又超拔了西方道路,走的是一條新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說,資本雖然還是那個資本,但它存在的土壤已不再是那塊土壤。在這種條件下,資本邏輯必然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盡管如此,資本邏輯作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存在是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被忽略的,利用資本,發(fā)展資本,使資本參與夯實我們現(xiàn)實生活基礎(chǔ)的過程是我們的一個必然選擇。葉險明教授指出,可以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稱為“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①。這個判斷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在資本問題上,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不同就在于能否以及如何“駕馭資本邏輯”。這是理解和把握中國道路的一個重要視角。那么,如何“駕馭資本邏輯”呢?竊以為,可以從制度、道路、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方面進行綜合考量,但倫理調(diào)控是不可或缺的——當然,這是一個十分復雜而敏感的問題。
一、資本的倫理調(diào)控何以必要
我們借鑒和運用資本,并在一定范圍內(nèi)嚴格地遵循著資本邏輯,當然也就應(yīng)該管控好它,因為我們借鑒和運用的是作為手段的資本,而不是作為目的的資本,手段只有符合目的需要才是合理的和有效的。當然,管控資本的手段和方法不是現(xiàn)成的,而是在運用資本過程中逐漸探索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倫理調(diào)控一直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資本無倫理”的觀點有較大的市場,甚至有學者認為,在當代中國,道德倫理成為社會的熱點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悲哀,似乎資本與道德無涉,與倫理無關(guān),或者說,對資本而言,倫理只是一種消極或解構(gòu)的因素。其實不然。在運用資本以及汲取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的過程中,倫理調(diào)控是必要手段,這既有理論發(fā)展上的考量,更是出于現(xiàn)實生活的迫切需要。
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缺少倫理維度。阿爾都塞就斷言,“把《資本論》歸結(jié)為倫理學的構(gòu)想是一種兒戲”②。這種觀點具有相當?shù)拇硇裕瑢ξ覈R克思主義的研究也頗具影響。譬如,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唯物史觀一直缺少倫理維度。這種觀點和做法是錯誤的,它極大地妨礙了我們科學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觀的真精神,從而使唯物史觀成為一個“人學空場”。大家知道,唯物史觀的崇高理想或歷史使命是實現(xiàn)人的自由解放,而人是有倫理的。也就是說,唯物史觀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不能沒有倫理的維度,否則,唯物史觀就不是一種關(guān)于“事情”之“意義”關(guān)懷的價值學說,而是關(guān)于“事物”之“事實”陳述的科學之科學,一幅冰冷的面孔,拒人于千里之外。唯物史觀之所以成為科學,就在于它是屬人的,即關(guān)注人的意義、價值以及命運,是關(guān)于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科學。所以,唯物史觀與道德倫理并不沖突,而是有機統(tǒng)一的。唯物史觀包含著道德倫理的意蘊,道德倫理構(gòu)成唯物史觀的重要支撐。
可以認為,資本邏輯批判是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馬克思建立唯物史觀的核心原則,馬克思正是在資本邏輯批判的基礎(chǔ)上昭示了人類解放與自由的理想及其實現(xiàn)道路。正如俞吾金教授所言,這種批判主要是一種政治批判或歷史批判,即把資本邏輯放在人類自由解放的對立面或階梯性上展開批判。但必須看到,馬克思的這種批判蘊含著深刻的倫理意蘊,它以道德評價為基點,從道德批判出發(fā),經(jīng)過道德實踐,到達道德理想,展示了一條十分清晰而深刻的倫理維度③。應(yīng)該說,馬克思資本邏輯批判的深刻性和徹底性就在于他從道德批判出發(fā),把道德批判化作歷史批判的利刃,深深地插進資本邏輯的本質(zhì)之中。這個批判的深刻性和徹底性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初露端倪,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集中而徹底的展現(xiàn)。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異化勞動”為核心原則和根本立足點,揭示了資本邏輯對人性的戕害,對人發(fā)展的限制。“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zhì);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④ 顯然,這種批判蘊含著深刻的倫理批判,或者說,是以倫理批判展開資本邏輯批判的。
在《資本論》中,這種倫理批判又進一步上升到歷史的天空,成為歷史批判的核心維度或基礎(chǔ)性維度。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yīng)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交換關(guān)系”⑤,簡單地說,就是資本及其邏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社會關(guān)系”,“資本是一種社會生產(chǎn)關(guān)系。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⑥。這種“歷史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只存在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不是永恒的,它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中產(chǎn)生,又必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中消亡。因此,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主要是一種歷史批判。“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jīng)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guān)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jīng)濟的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理解為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guān)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guān)系負責的。”⑦ 在這里,馬克思強調(diào)的主要是歷史的規(guī)律性,即把資本看成是一個體現(xiàn)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歷史范疇。但馬克思對資本的歷史批判,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道德批判這個基本維度。馬克思認為,資本最大的問題是只重視價值增殖而罔顧人性,進而阻礙了人的發(fā)展。“資本把財富本身的生產(chǎn),從而也把生產(chǎn)力的全面的發(fā)展,把自己的現(xiàn)有前提的不斷變革,設(shè)定為它自己再生產(chǎn)的前提。……資本的限制就在于:這一切發(fā)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生產(chǎn)力,一般財富等等,知識等等的創(chuàng)造,表現(xiàn)為從事勞動的個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當做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做他人財富和自身貧困的條件。”⑧ 在這里,馬克思明確地指出,依靠資本原則來解決人類的幸福和共存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邏輯在根基上具有反人性的一面,是沒有道德底線的。“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樣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⑨ 不僅如此,資本為了利潤還具有內(nèi)在的違法沖動。“一旦有適當?shù)睦麧櫍Y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⑩ 違法沖動,實際上是對道德底線的踐踏。所以,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的倫理批判來展示自己的道德理想——消滅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
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觀總是面向“事情本身”,面向“生活世界”,面向“此在人生”,關(guān)注現(xiàn)實的人的生存以及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當代哲學的生存意蘊因而展開。也就是說,唯物史觀總是以切入當代中國現(xiàn)實生活并為中國道路明確方向為己任,照亮人的精神生活是其矢志不移的目標。唯物史觀在肯定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是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的同時,也透徹地闡明了精神生活之于人的生存以及生活的重要意義。毫無疑問,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道德理想居于基礎(chǔ)乃至核心的地位。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個核心思想,即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思想是基于道德上的考量,是一種道德理想。沒有這種道德上的追求,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充實與高尚。因此,我們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旗幟,廓清籠罩在人的心靈之上的、由資本的惡所帶來的物的“霧霾”,還人們一個精神上的朗朗乾坤。
隨著中國市場機制的不斷推進,資本邏輯的負面效應(yīng)也越來越凸顯出來,其突出表現(xiàn)是物化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地宰制著人的靈魂,人們的物質(zhì)貪欲越來越大,甚至為了一己私欲而不擇手段。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身的矛盾不斷激化,這些無非是物化的必然結(jié)果,從而也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jié)果,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的道德問題。近些年來,理論界熱議“道德滑坡”或“道德爬坡”的問題,其實,這種爭論并沒有實質(zhì)性意義,因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擺在人們面前的現(xiàn)實是道德狀況不容樂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于是,在道德問題面前,有人就走向了形而上學,把道德問題歸咎于資本邏輯,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質(zhì),這是有道理的。當然,道德問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把道德問題完全歸咎于資本邏輯,是不公平的,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資本邏輯難逃其咎,或者說,資本邏輯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過去的因素。從根本上講,資本邏輯是由人操控的,或者說,資本邏輯體現(xiàn)出資本所有者對利益的貪婪,是人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物化。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是資本家,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也就是說,道德問題與人性有關(guān),是人性沉淪的表征。在資本邏輯中,人性的基本特征是墮落,即人的主體性的喪失,人在物欲中迷失了自我。我們可以批判“經(jīng)濟人”假設(shè)的虛妄性,但不可否認經(jīng)濟利益對人巨大的誘惑力。正當?shù)摹⒑侠淼睦媸侨税l(fā)展的重要動力,而沒有道德底線的利益追求則常常使人失去自我而成為物的奴隸。可以說,普遍的物化是資本邏輯對人性的戕害而致使其墮落的結(jié)果與表征。就此而言,物化與社會主義本質(zhì)要求背道而馳,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嚴重消解。因此,駕馭資本邏輯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而對資本邏輯進行倫理調(diào)控則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二、資本的倫理調(diào)控何以可能
那么,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有沒有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當然,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以對兩個基本問題的澄清為前提。一是資本邏輯與倫理是否存在著一種內(nèi)在的或天然的聯(lián)系。這又有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倫理是否能統(tǒng)攝或涵蓋資本邏輯,即能否在倫理的視域中對資本邏輯進行考察,或者,是否能以倫理標準審視資本邏輯。另一方面,資本邏輯是否具有倫理維度,即資本邏輯是否有接受倫理調(diào)控的可能。這是在一般意義上講的。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中,資本邏輯和倫理是否可以對接并相互融合,即資本邏輯是否具有倫理意蘊和倫理是否把管控資本作為自己的任務(wù)。這是在特殊意義上說的。
毫無疑問,資本邏輯與倫理之間存在著一種內(nèi)在的或天然的聯(lián)系,“資本無倫理”是一個假命題。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證明。
首先,資本是一種社會關(guān)系,盡管它以物為中介,但物的因素不可能完全遮蔽掉社會關(guān)系中的道德因子。所謂社會關(guān)系,首先表現(xiàn)為勞動關(guān)系、交往關(guān)系,特別是其中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進而表現(xiàn)為道德關(guān)系、政治關(guān)系等,因而在根本上是人和人的關(guān)系。“凡是有某種關(guān)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guān)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fā)生‘關(guān)系,而且根本沒有‘關(guān)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guān)系不是作為關(guān)系存在的。” 作為一種“歷史的社會關(guān)系”,資本實際上體現(xiàn)的是人和人的非人化的關(guān)系。而且,人的關(guān)系是在實踐活動中確立的,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在活動之前,并不存在抽象的一般關(guān)系,“并不‘處在某一種關(guān)系中,而是積極地活動”。離開了社會關(guān)系,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強調(diào),在現(xiàn)實性上,人的本質(zhì)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人和人的關(guān)系必然表現(xiàn)為一種倫理關(guān)系。一方面,倫理是人的倫理,是人與人在相處中堅持的道德準則。在社會中,個人不僅意識到自己的個性和利益,而且意識到他人的、整體的存在與利益。另一方面,處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實踐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而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實際上是在人和人的關(guān)系上被確認的。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待自然,關(guān)鍵在于人以什么樣的方式對待他人和社會,這既包括對待代內(nèi)個人與社會整體的態(tài)度,也包括對待代際之間人與社會整體的態(tài)度,歸根到底,這是一個道德倫理問題,否則,人和人的關(guān)系就成為純粹的物物關(guān)系。
其次,資本邏輯具有兩面性,即融邪惡性和文明性于一體。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是辯證的,既揭露了資本邏輯的邪惡性,也揭示了資本邏輯的文明性。資本邏輯的邪惡性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層面。一是資本形成過程中的殘酷性。資本是通過原始積累的方式形成的。原始積累是資本家用暴力手段強迫勞動者與生產(chǎn)資料相分離的過程,是一部“掠奪史”和“殖民史”。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二是資本生產(chǎn)過程中的殘酷無情。資本生產(chǎn)的本質(zhì)是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因而,它必然帶來異化勞動——對人的確證的生產(chǎn)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卻表現(xiàn)為對勞動者——工人的奴役。三是資本增殖結(jié)果的非人化。異化必然造成物化,即人成為物的奴隸,物成為人心靈的實際主宰,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人的道德淪喪。特別是對于資本所有者而言,道德只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在追逐物質(zhì)利益的過程中,人是沒有道德的——這是“經(jīng)濟人”假設(shè)的重要根基。顯然,在這三個層面中,異化勞動是核心,正如伯爾基所言,異化勞動是馬克思資本邏輯批判的核心范疇、邏輯起點和核心原則。“異化既表現(xiàn)為我的生活資料屬于別人,我所希望的東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別人的占有物;也表現(xiàn)為每個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個東西,我的活動是另一個東西,而最后,——這也適用于資本家——則表現(xiàn)為一種非人的力量統(tǒng)治一切。” 由此看來,人與人的異化即人與自身本質(zhì)相異化是勞動異化的根本所在,而人與人的異化,則深刻地表現(xiàn)著人的道德倫理關(guān)系的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就在同他人相對立。因為一般地說,人同自身的任何關(guān)系,只有通過人同他人的關(guān)系才能得到實現(xiàn)和表現(xiàn)。因此,人同它的本質(zhì)相異化,也就是說一個人與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同人的本質(zhì)相異化;每一個人都按照他本身所處的那種關(guān)系和尺度去觀察、評價他人。這種批判思想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當然,是在更廣闊的背景中——歷史批判中探尋消除異化,從而實現(xiàn)人的自由解放的現(xiàn)實路徑。資本與勞動相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道德倫理關(guān)系異化的條件,因為資本對直接生產(chǎn)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qū)使下完成的,資本是死勞動對活勞動的主宰。正因為如此,有人把資本邏輯看成是一種純粹的惡,從而認為“資本無倫理”,其實,這是一種悖論,因為惡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評價。作為一種道德評價,“沒有倫理”是指道德跌入塵埃與污泥之中,并不是說與道德無涉。譬如,說一個人沒有道德,并不是說他與道德無關(guān),而是說他的道德低下。正因為資本邏輯的惡,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要消除異化勞動以及異化的道德倫理關(guān)系,唯一的途徑是終結(jié)資本邏輯,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chǔ)上,在協(xié)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chǎn)的生產(chǎn)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chǔ)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資本邏輯與倫理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還可以從資本邏輯的文明面中得到進一步的證明。馬克思對資本邏輯文明面的概括是:“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nóng)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有利于社會關(guān)系的發(fā)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tài)的各種要素的創(chuàng)造。” 可以把資本邏輯的文明面歸結(jié)為“三個更有利于”,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倫理意義。資本邏輯的文明面當然是一種善,而善與惡是相對應(yīng)的道德范疇,也就是說,資本邏輯的文明面彰顯出資本邏輯善的倫理向度。無論如何,不能把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看成是與道德無關(guān)的事情。實際上,“更有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是資本邏輯最大的善,因為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構(gòu)成社會進步和人的發(fā)展的當然基礎(chǔ)和前提。一方面,不能把生產(chǎn)力看成是一種純粹的客觀的經(jīng)濟力,因為勞動者是其中首要的、起主導作用的因素,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首先是人的發(fā)展,沒有人的發(fā)展,就不可能有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因此,“更有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的實質(zhì)是更有利于人的發(fā)展,這本身就是善,是最大的善。盡管這不是資本的故意,但卻是其造成的一種客觀結(jié)果。而人的全面發(fā)展意味著人的道德水平的提升,甚至可以認為,在人的全面發(fā)展中,道德水平的提高居于基礎(chǔ)或核心的地位。一個道德素質(zhì)不高的人,肯定不是一個全面發(fā)展的人;一個全面發(fā)展的人,肯定是一個道德素質(zhì)很高的人。另一方面,在唯物史觀中,生產(chǎn)力主要是人們處理人和自然關(guān)系的能力,即物質(zhì)生產(chǎn)的能力,而在物質(zhì)生產(chǎn)“這個領(lǐng)域內(nèi)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lián)合起來的生產(chǎn)者,將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把它置于他們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tǒng)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zhì)變換”。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一靠科學技術(shù),二靠人的道德。人是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明者與應(yīng)用者,人的道德水平?jīng)Q定著人們應(yīng)用科學技術(shù)的狀況。只有在人的道德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條件下,先進技術(shù)才能真正成為科學,才能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說生活還有別的什么基礎(chǔ),科學還有別的什么基礎(chǔ)——這根本就是謊言”。同樣,也不能把社會關(guān)系的發(fā)展看成是一個脫離倫理規(guī)范的過程,因為社會關(guān)系本質(zhì)上是人與人的關(guān)系,是人與人之間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市場經(jīng)濟作為資本規(guī)約下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必須要有一定的規(guī)范,既要有制度規(guī)范,也要有道德規(guī)范。市場經(jīng)濟既是規(guī)則經(jīng)濟,也是道德經(jīng)濟,公平正義、自由平等、誠實守信、童叟無欺、遵守規(guī)則以及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diào)的“同情心”即利他性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規(guī)約因素。沒有道德因素的規(guī)約,市場經(jīng)濟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更談不上發(fā)展。這個觀點可能會引起歧義,但事實卻是,當人們還沒有建立起普遍的公平、自由、誠實守信等觀念以及對規(guī)則的認同和遵守時,市場經(jīng)濟就很難有效地確立和運行。因此,規(guī)則意識是市場經(jīng)濟確立的首要前提。“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tài)的各種要素的創(chuàng)造”則給我們提供了更大的闡釋空間。可以把“更高級的新形態(tài)”理解為自由人聯(lián)合體即共產(chǎn)主義社會;“各種要素”包含極廣,但倫理道德即人的思想道德品質(zhì)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真正共同體的建立,除了生產(chǎn)力的高度發(fā)展和物質(zhì)財富的極大豐富外,人們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關(guān)鍵或核心因素,而道德素質(zhì)則構(gòu)成了精神境界的關(guān)鍵或核心。沒有精神境界以及道德素質(zhì)的極大提高,只靠物質(zhì)的東西是不可能支撐起共產(chǎn)主義大廈的。資本邏輯構(gòu)筑起物的依賴性基礎(chǔ)上的人的獨立性,人的獨立性構(gòu)成自由個性的現(xiàn)實基礎(chǔ),而精神以及道德因素則構(gòu)成自由個性的真實意蘊或邊界。換言之,資本邏輯使人從“人的依賴性”中擺脫出來,從而奠定了道德生長的基礎(chǔ)。
再次,我們談?wù)撡Y本邏輯與倫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不是說資本本身趨善或趨惡,而是指資本增殖的手段或方式有善惡之別。其實,資本本身并不具有善惡屬性,資本邏輯的邪惡性主要是在資本增殖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的確“資本無倫理”。但是,資本從來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資本,資本總是與一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相聯(lián)系,而一定的歷史發(fā)展階段都有相應(yīng)的倫理基礎(chǔ),因此,資本邏輯與倫理必然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lián)系。大家知道,資本邏輯與價值增殖相聯(lián)系,價值增殖是資本邏輯的本質(zhì)要求或根本目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但資本本身并不能實現(xiàn)價值增殖,資本實現(xiàn)價值增殖的主要條件有兩個,一是人,二是方法或手段。一方面,“資本并不天然具有道德屬性。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無論是作為資本價值實體的生產(chǎn)要素和勞動力,還是資本實現(xiàn)價值增殖的目標,本身都不具有善惡屬性。但是,資本終究由人掌握、使用和管理,因此,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價值取向、善惡評價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判斷和行動,必然對資本的形成、使用及增殖的實現(xiàn)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資本邏輯實現(xiàn)價值增殖的手段或方法的殘酷性和非人性,從而導致資本邏輯的惡。在某種意義上,價值增殖并非惡,而是善,問題在于以何種方式實現(xiàn)價值增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價值增殖的方式是“異化勞動”,這顯然是一種惡。當然,不能以對手段的批判來代替對本質(zhì)的批判,相反,應(yīng)該把對手段的批判作為對本質(zhì)批判的延伸。總的來說,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chǔ)上,資本邏輯的邪惡性暴露無遺。
問題在于,資本邏輯以及它存在的基礎(chǔ)——市場經(jīng)濟作為手段被引入到中國,如何認識資本邏輯與倫理的關(guān)系便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wù),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不能沒有資本邏輯這個因素,也不能沒有道德這個基礎(chǔ)。應(yīng)該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nèi),資本邏輯扎下根來并努力壯大自身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其存在的環(huán)境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按照唯物史觀的理解,資本邏輯必然隨著環(huán)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毫無疑問,中國的道德環(huán)境必然對資本邏輯產(chǎn)生影響,資本邏輯不能與中國現(xiàn)實的道德環(huán)境相脫離,否則,資本邏輯就根本沒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梁漱溟曾經(jīng)說過,中國是一個以倫理道德為宗教的國家。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環(huán)境中,道德是至關(guān)重要的要素,資本邏輯必須適應(yīng)這個環(huán)境。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中,資本邏輯當然要實現(xiàn)價值增殖,否則,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但價值增殖必須以守德為邊界。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資本邏輯必須與倫理相結(jié)合。一方面,資本邏輯必須倫理化。這可能存在著歧義,原因是資本邏輯一旦倫理化,資本還是不是資本?這個問題不斷地被人提了出來,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不可能沒有道德的基礎(chǔ)。其實,資本倫理化并不是要弱化資本邏輯的力量,而是要通過增加倫理因素來消解資本邏輯的惡和強化資本邏輯的善,從而使資本邏輯煥發(fā)出一種新的力量。彰善懲惡,是倫理的本質(zhì)功能,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倫理必須把管控資本邏輯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wù)。道德的基本功能是調(diào)整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以及實現(xiàn)人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說,調(diào)控社會關(guān)系是它的主要任務(wù)。不能否認,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中,資本邏輯構(gòu)成了整個社會關(guān)系特別是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重要基礎(chǔ),社會關(guān)系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資本邏輯之中,或者說,社會關(guān)系必然受到資本邏輯的影響,資本邏輯所展現(xiàn)出的善與惡,都會直接影響到社會關(guān)系。人們只有在一個平等、公平和自由的環(huán)境中交往,社會關(guān)系才有可能健康發(fā)展,道德也才具有向上的力量。因此,調(diào)整社會關(guān)系,必須對資本邏輯進行倫理調(diào)控。沒有對資本邏輯有效的倫理調(diào)控,社會關(guān)系的發(fā)展和完善就是一句空話。
三、資本的倫理調(diào)控何以實現(xiàn)
可以肯定地說,資本主義條件下也存在著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否則,資本主義社會早就崩潰了,但是,這種倫理調(diào)控是不自覺的,因為資本是社會的主體,資本邏輯是整個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邏輯。與之相反,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中,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則是自覺的,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真正主體是勞動者即人民群眾,因而,市場經(jīng)濟不僅要有資本邏輯的基礎(chǔ),更要有倫理的要求,或者說,資本邏輯不僅要在合乎憲法和法律的基礎(chǔ)上,而且還要在合乎道德倫理的基礎(chǔ)上理性地運行。但是,由于資本邏輯的本性使然,這個過程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發(fā)生的,而必須是一個重構(gòu)或重塑的過程,即賦予資本邏輯以倫理性的特點,或者說,給資本邏輯以倫理限制,使其在倫理的框架中理性地運行。“現(xiàn)代工業(yè)的全部歷史還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 不可想象,沒有倫理基礎(chǔ),我們在市場經(jīng)濟中仍能堅持中國道路而不迷失方向。所以,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
那么,如何實現(xiàn)資本邏輯的倫理調(diào)控呢?
首先,改造資本,把資本邏輯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的軌道中來,堅持以人為本。對于當代中國而言,資本是一個外來物,它的身上帶有很濃的制度或意識形態(tài)色彩,存在著很多道德上或與道德有關(guān)的瑕疵。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即如何對待資本?我們在汲取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的過程中就必然會遇到這類問題:如何剝離附著其上的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等,使其融入我國的經(jīng)濟、政治和廣義的文化環(huán)境中,從而內(nèi)化為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tài)意義的堅實基礎(chǔ)?這個“剝離”和“融入”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改造或重塑的過程。
這有三個層面的任務(wù)。一是必須明確,資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手段是為目的服務(wù)的,千萬不能顛倒目的和手段的關(guān)系。從根本上講,社會主義不是以資本原則構(gòu)建的社會,而是以人為本、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因此,實現(xiàn)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是我們的根本目的。我們之所以要引入資本以及市場經(jīng)濟,看中的正是它的“三個更利于”,即它的有用性或手段的效用性。作為手段,資本邏輯必須服務(wù)于目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邏輯實現(xiàn)價值增殖的手段必須符合善,即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前面說過,價值增殖并非惡,在一定意義上是善,關(guān)鍵在于不能不擇手段,而必須是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以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為根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二是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上必須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其價值取向、善惡評價以及相應(yīng)的行為必須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賺錢沒有錯,但必須要有一個道德底線或邊界,必須與社會道德相一致。如果說“經(jīng)濟人”假設(shè)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這個合理性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是講道德的,因為人首先是社會的人。正如馬克思所言,“要生產(chǎn)商品,他不僅要生產(chǎn)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chǎn)使用價值,即生產(chǎn)社會的使用價值”。既然如此,商品生產(chǎn)者就必須具有道德,即所生產(chǎn)的商品以及生產(chǎn)商品的手段必須符合善和美的要求。三是不斷控制并逐步消除資本邏輯對人的統(tǒng)治。資本邏輯對人的統(tǒng)治集中表現(xiàn)為抽象勞動對具體勞動的僭越,其后果是物化,即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的盛行。這個被馬克思、盧卡奇等人深刻批判過的現(xiàn)象,在當代中國仍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nèi)存在。物化是對道德的消解,對人心的遮蔽,對精神世界的占領(lǐng)。“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力量和獨創(chuàng)性,是怎樣照亮現(xiàn)代精神生活的。” 盡管這種理解過于偏狹,但它確實揭示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責任——照亮現(xiàn)代精神生活,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這三重任務(wù)的本質(zhì)和核心是以人為本。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邏輯以對活勞動的宰制為本,以價值增殖為最高價值。“資本主義生產(chǎn)比其他任何一種生產(chǎn)方式都更加浪費人和活勞動,它不僅浪費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費人的智慧和神經(jīng)。”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chǎn)則以人為本——這是社會主義生產(chǎn)與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本質(zhì)區(qū)別之所在。發(fā)揮人的主體性和首創(chuàng)精神,是運用和發(fā)展資本以及市場經(jīng)濟的前提和目標,從而為人的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其次,堅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根基,賦予資本邏輯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基因,最大限度地彰揚資本邏輯的善。資本邏輯也是一種文化,或者說,資本邏輯是現(xiàn)代社會塑造文化的基礎(chǔ),這種由資本邏輯塑造的外來文化要在中國大地上開花結(jié)果,就必須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否則,就會產(chǎn)生排異現(xiàn)象。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有其獨特稟賦,也有其極大的包容性,包括對資本邏輯的包容。但這種包容是有條件的,即資本邏輯接受這種包容。資本邏輯具有一個優(yōu)點,它把一切能為自己所用的東西,包括文化在內(nèi),一并吸納進來,成為謀求自身發(fā)展的能量。資本邏輯接受這種包容,也就意味著資本邏輯并不否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根基,從而使自身發(fā)生某種變異。事實證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基因并不減弱資本邏輯的力量,恰恰相反,它能使資本邏輯的正能量充分發(fā)揮出來。
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民族共同尊崇的價值原則。“當今世界,人類文明無論在物質(zhì)還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物質(zhì)的極大豐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時,當代人類也面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xù)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guān)系日趨緊張,等等。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fā)現(xiàn)和發(fā)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 毫無疑問,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倫理道德是“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的重要內(nèi)容。可以說,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突出的難題,而這個難題的出現(xiàn)、發(fā)展與資本的引進、發(fā)展基本上同步,它與資本邏輯密切相關(guān)。對資本邏輯進行調(diào)控,需要運用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智慧和力量。勤勞奉獻、重義輕利、謙和禮讓、真誠有信等傳統(tǒng)美德與資本邏輯以及市場經(jīng)濟并不沖突,而是具有高度的相容性。換言之,資本邏輯以及市場經(jīng)濟也需要這些道德規(guī)范的制約。所以,資本來到中國,必須要接受這些優(yōu)良的道德傳統(tǒng)并內(nèi)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唯有如此,資本邏輯的中國化生存才有了現(xiàn)實的基礎(chǔ)。當然,資本邏輯在接受并內(nèi)化這些道德傳統(tǒng)時,并不是單方面的,同時也賦予這些道德傳統(tǒng)以現(xiàn)代性的某些特質(zhì)。套用馬克思的一句話:資本改造環(huán)境,環(huán)境也改造資本。
再次,把資本邏輯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用制度規(guī)范資本邏輯。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資本邏輯也是一種權(quán)力,當然也應(yīng)該有制度的規(guī)約。這有三層意思。一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guī)約資本邏輯,資本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合乎邏輯地展開才是合理的和有效的。二是資本邏輯必須遵從法制的規(guī)范,即符合憲法和法律規(guī)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必然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當然包括調(diào)控資本邏輯能力的現(xiàn)代化,而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因而,也要依法管控資本邏輯。資本邏輯以及市場經(jīng)濟只有在符合憲法和法律規(guī)范的基礎(chǔ)上依法展開,才是合理的、有效的,也才是符合道德的。三是道德規(guī)范的制度化。一般來講,道德規(guī)范是一種非制度化的規(guī)范,具有非強制性,內(nèi)化是其基本特征。正因為如此,道德的遵守需要高度的自覺。但是,市場經(jīng)濟的逐利原則有時候使人放棄了道德自覺的防線,使道德不自覺成為一種常態(tài)。因此,倫理道德的制度化就成為一種必然。在這一方面,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批判資產(chǎn)階級虛偽性的同時,將道德作為一種具有內(nèi)在獨立結(jié)構(gòu)的制度來研究的倫理制度思想給我們以重要啟示:道德只有上升為制度,才具有有效的規(guī)范性。實際上,制度和道德存在著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制度是道德的規(guī)范,道德是制度的內(nèi)核。但道德無形,界定較難,而制度有形,邊界清晰可見,只有把道德轉(zhuǎn)化為制度規(guī)范,執(zhí)行和裁判才有明確的量度界限。市場經(jīng)濟是規(guī)則經(jīng)濟,這種規(guī)范既包括道德,也包括制度,道德是通過制度體現(xiàn)出來的,因此,制度是保證其有序運行的根本。同樣,資本邏輯也應(yīng)該有明確的不可逾越的邊界,這個邊界必須是明確且易于制作的。因此,只有使倫理制度化,獎懲有度,裁量有方,才能使資本邏輯逐利而不逾矩,增殖而守德。
最后,堅持社會主義道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lǐng),引導好資本邏輯的發(fā)展方向。社會主義道德的內(nèi)容極其廣泛,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核心內(nèi)容無疑是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guān)系。這就涉及到怎樣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人的利益,而把利益看成是個人不懈奮斗的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克思贊同黑格爾所說的“惡”是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把利益分為兩種,即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所謂共同利益,是指共同體中每個人的共同利益,即集體利益。所謂特殊利益,是指共同體中每個人獨特的利益需求,即個人利益。市場經(jīng)濟是利益經(jīng)濟,資本邏輯的內(nèi)核是利益,因此,個人利益是資本邏輯以及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動機。這樣,就勢必導致一個矛盾,即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矛盾。處理這個矛盾,要靠制度來規(guī)范,但更重要的是要堅持道德原則———集體主義原則。集體主義原則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核心原則。“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則,那就必須使人們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類的利益。” 當然,我們強調(diào)集體利益,并不否定個人正當?shù)摹⒑侠砗戏ǖ睦妫喾矗瑓s正是對個人正當?shù)摹⒑侠砗戏ǖ睦娴目隙ǎ驗椋瑢崿F(xiàn)集體利益的真正目標是保障每個人利益的實現(xiàn),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有機統(tǒng)一的。這是資本邏輯所面臨的一個全新的道德環(huán)境,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邏輯的規(guī)范化運行方向。
注釋:
① 參見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一種批判性的審視:“話語體系”何以能打造———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中一個方法論問題》,《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論》,《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②[法]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版,第159頁。
③ 參見張三元:《馬克思自由倫理的四重意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533、193、335頁。
⑤⑥⑦⑨⑩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77—878、10、306、871、871、54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頁。
宋希仁:《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101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928—929頁。
王露璐:《道德與資本的沖突與整合》,《哲學研究》2011年第9期。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
參見葉險明:《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論》,《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近些年來,“生態(tài)人”或“理性生態(tài)人”之類的概念不斷地被人提出。其實,“生態(tài)人”是生態(tài)倫理學家提出的一種新的人類行為模式,是對“經(jīng)濟人”概念的批判和揚棄。作為一種人性假設(shè),“生態(tài)人”具有科學知識和倫理道德兩個前提,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倫理道德是一個更重要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生態(tài)人”實際上一種“倫理人”的假設(shè),但我們往往不敢承認這一點。試想,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提出之前,我們是用什么來反對和揚棄“經(jīng)濟人”假設(shè)呢?一般地說,是“社會人”。正由于人是社會的人,因此,人是道德人。當然,這里所講的“道德人”與亞當·斯密的“道德人”有本質(zhì)的不同,前者以社會性為前提,后者則以自私性為基礎(chǔ)。問題在于,我們不能否認人的倫理屬性。
[美]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xiàn)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版,第113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頁。
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
作者簡介:張三元,武漢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武漢,430205;孫虹玉,武漢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430205。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