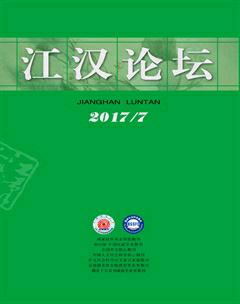生產力定義的解構和重構
韓東屏+胡丹丹
摘要:生產力是什么?這并不是一個已經得到有效解決的問題。以往學界關于生產力的定義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只有關于人類物質資料生產的生產力定義。其二,即便是這個意義上的生產力定義,也存在偏差和不足。既然如此,只有重構新的生產力定義。而重構要想避免以往出現的種種偏失,就只有先定義一般意義的生產力概念,再分別定義各種特殊意義的生產力概念。一般的生產力可謂有生命的活動者取得所欲對象的活動能力。它分別有四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人類的物的生產力、動物的物的生產力、人類的生命生產力、動物的生命生產力。人類的物的生產力,即所欲之物的生產力,又有物質產品的生產力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力之分。其中,物質產品的生產力,就是被歷史唯物主義所特別看重的“物質生產力”。
關鍵詞:生產力;物的生產力;生命生產力;人類生產力;動物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0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7-0039-05
生產力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繼歷史唯物主義者用于解釋社會歷史的基本工具。
在解釋人類社會歷史方面,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如此看重和強調生產力,除了在于認為它是其他各種社會因素的基礎或社會結構的第一要素,還在于這個道理:“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① 因此,恩格斯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② 由于“物質生活的生產”和“生產力”在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那里屬于同等概念,是對同一個事物的不同說法,所以,“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③,并且服從這一規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④ 總之,生產力既決定社會形態,也決定人類歷史的發展。
可是,生產力究竟是什么卻并不是一個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和沒有問題的問題。
一、解構以往的生產力定義
我認為,以往學界關于生產力的定義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只有關于人類物質資料生產的生產力定義。
自從世界學界有了“生產力”的術語以來,人們基本上都是從物質資料生產的視域來對生產力進行論述的。從“生產力”概念的首創者魁奈,經亞當·斯密、李嘉圖、李斯特到馬克思,再從馬克思到今天的國內學界和國外學界,莫不如此。然而,是不是除了物質資料生產意義的生產力之外,就再沒有其他意義的生產力?如果是沒有,學界這樣論說生產力就是可以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論說不說是錯誤的,也至少是片面的。那么,實際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回答是“不是”。
首先,由于在物質產品的生產之外還有精神產品的生產,這就說明在物質生產力之外還有精神生產力的存在。事情很明顯,人類除了有物質生活方面的各種需求,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的各種需求,而用于滿足人類精神生活方面需求的文學藝術作品和科學知識、人文知識和價值理念之類的精神產品,自然也是由人用精神生產力生產出來的。正因有此事實存在,所以在馬克思那里,也有“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⑤ 的分類與表述,只不過馬克思一直沒有對后者展開專門的具體論述。既然事實上確實也有精神生產的存在,我們怎能只有物質生產的生產力定義?
其次,在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外,還有與這兩種生產的性質截然不同的人類自身生命的生產,亦曰人本身的生產或人口的生產。人口的生產也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沒有它就不會有人類后代的繁衍和世代的承續。既然人口的生產的存在不容置疑,那就一定也有人口生產的生產力。人口的生產不僅對人類的續存必不可少,而且同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大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有“兩種生產的原理”,其創始人早在1845年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就已有所論及,他們在開篇部分便提出了人類既有滿足其衣、食、住等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也有“生命的生產”的觀點,認為這二者都是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并由此總結道:“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⑥ 后來他們到了晚年,在研讀了人類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著作后,又更加明確地論述了“兩種生產的原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說:“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⑦ 既然兩種生產都是生產,并且還都是“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今天的歷史唯物主義,怎么可以只講物質生產而不講人的生產?怎么可以只有物質生產力的定義而沒有人口生產力的定義?
其三,在人類的生產力之外,還存在動物的生產力。如果說人繁衍后代屬于人自身生命的生產,那么,動物繁衍后代也屬于其自身生命的生產;如果說人類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也包括早期人類賴以維生的采集與狩獵,那么,食草動物的采集、食肉動物的狩獵和雜食動物如猩猩、狒狒的既采集又狩獵,也應屬于動物的物質生產。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也的確有關于“動物的生產”的用語和論述,并曾在論述人類的物質生產時,以其為參照,進行相互比較:“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⑧ 既然動物也有生命的生產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那自然也有它們的生命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如此我們怎能僅有一個人類生產中的物質生產的生產力定義,而沒有一個既涵括人類的兩種生產也涵括動物的兩種生產的最一般意義的生產力定義?并且,在我們不知道或者不承認這個最一般的生產力定義的情況下,自然也不會知道或承認有最一般的生產,這時,我們又憑什么把不同于人類的物質生產力的“生命的生產”及其生產力和“動物的(物質)生產”及其生產力,也都認定為“生產”和“生產力”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東西?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以往學界不僅從不界說其他意義的生產力,就是對人類的生產物質生活資料意義上的生產力概念的界定,也均存在偏差或不足。
“生產力”一詞首先出現于經濟學,雖說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和基本術語,卻并不是馬克思的創造。據考證,歷史上首次使用生產力概念的是法國古典經濟學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不過,他并沒對這個概念做任何界說,只有“土地生產力”、“人口生產力”這樣的說法。其后,亞當·斯密把生產力視為生產的能力或勞動生產率;李嘉圖把生產力看作是各種不同因素的自然力;李斯特把生產力理解為人們獲得物質財富的一種能力或手段⑨。以上這些表述,基本上都屬于關于人的物質生產力的說法,但也僅僅只是一些簡單的說法而已,都還算不上是對生產力的本質性界定。
到了馬克思,由于他是將人類的物質生產力視為社會結構的第一要素和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所以對之有大量的論述。可令人遺憾的是,馬克思也從未對其給出過一個明確的定義。盡管他關于“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⑩;生產力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而“有用的具體的”“勞動過程本身,就是勞動通過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材料” 等一系列說法,已經是在對人的物質生產力進行界定,可所有這些還是不能稱為標準定義或嚴格定義。
是故,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繼承者就只有根據自己對馬克思諸多相關說法的理解用自己的語言給出生產力定義。當下的主流定義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入手,將生產力視為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如國內權威哲學教科書的定義是:“所謂生產力,是指人們改造自然,使之適應人的需要的物質力量,標志著人類改造自然的實際能力和水平。” 權威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定義是:“生產力是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能力。” 工具書《生產力經濟學辭典》的定義是:“人類在與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中,把自然物改造成為適合人類需要的物質資料的力量。亦稱‘物質生產力或‘社會生產力。它表明的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
從改造自然的維度解說人類物質生產力不能說不對,因為它客觀上確實有這種效果。但需要思考的是,人們從古至今,難道都是為了改造自然才進行物質生產,并擁有了物質生產力的嗎?顯然不是。當然,其中有兩個定義有明確交代,說是為了“適應人(類)的需要”。即便如此,從古至今的蕓蕓眾生,在為了適應自己的需要而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的過程中,他們又何曾意識到了自己是在進行這種交換?是在改造自然?這就說明,“改造自然”并不是生產者的自覺,也不是生產者必須有這種意識才能進行生產。既然如此,為什么要將這種不必要的東西放到生產力定義中加以強調?將生產力這種如此經驗可感的每日每時都在大量發生的具體現象用一個如此抽象而廣大的概念來加以界定,即便不算錯,至少會給人以“小頭戴大帽子”的不當之感。
誠然,如此下定義者可以說,這是因為人的物質生產過程或生產力,客觀上確實有改造自然的作用。這一點我也承認。但是,這個過程客觀上其實也有改造人類自身的作用,不僅能改造人的身體或體質,也能改造人的大腦或智慧,在恩格斯看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祖先”才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過渡”,最終變為了“完全形成的人”。如是,那又為什么在定義中單單只提“改造自然”的客觀作用?這又是何道理?人類物質生產力所具有的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客觀作用,可以在定義了人類物質生產力的概念或者揭示了其本質之后再說,而不應用它們或其中的某一個來對人類物質生產力概念進行定義。否則,為什么所有曾經界說過生產力的前人,尤其是馬克思這位最重視改造自然和改變世界的思想家,在界說人類物質生產力概念時,都從不提“改造自然”這個茬兒?
不僅如此,從改造自然的維度定義生產力還會導致定義不周延的問題。試問:人類之初的采集時代,乃至后繼的采集—狩獵時代,有沒有生產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顯然也是有的,否則人類就是連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可是,對植物的采集和對動物的獵殺,能叫“改造自然”嗎?如能,豈不是動物的采集和狩獵也屬于“改造自然”?如果回答是“也屬于”。那就再次表明,我們有何必要將并不屬于人類物質生產力之特點、特性的“改造自然”,也放到生產力定義中加以強調?
對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的生產力的解釋,在前蘇聯,主流觀點是斯大林根據馬克思的一些說法概括出來的:“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但它其實仍然算不上是標準定義,只是對生產力的各種構成因素的一個大致說明。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也缺乏有亮點的建樹。一些人認同斯大林的解釋;一些人只強調生產力的技術性,“將生產力簡化為技術力量”;一些人給出了雖有新意卻更加片面的解釋,如阿倫特的生產力定義是“創造更大量直接消費品的能力”;還有一些人由于認為馬克思的生產力存在把人變為被動客體的傾向,干脆拒斥生產力的概念。
二、重構新的生產力定義
既然以往的各種生產力定義均不能令人滿意,那就只有重構,而重構要想避免以往生產力定義中所存在的那兩個層面的問題,就只有先合理地明確定義一般意義的生產力概念,再分別定義各種特殊意義的生產力概念。
所謂一般意義的生產力概念,就是其前面沒有任何限定詞的“生產力”,它究竟應該怎么定義呢?在我看來,術語“生產力”首先是一個由“生產”加“力”構成的組合詞,因而它應該就是指生產的能力。這種能力,既可以是現實的、已經發揮了作用的能力;也可以是潛在的、尚未發揮作用的能力。但是,對生產力的定義不能像當年的亞當·斯密那樣就到此為止,而是還需繼續解釋“生產”。并且,這一步的解釋才是定義生產力的關鍵。
“生產”這個詞看似簡單易懂,可要準確定義并不容易,乃至迄今也未見一個。與生產力的定義不同,關于生產的定義要少得多,甚至在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重視生產及生產力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著述中都難得一見,這就只能以兩種權威詞典的解釋為例來說其不足。一為哲學詞典的:“生產是以一定的生產關系聯系起來的人們利用工具改變勞動對象以適合自己需要的過程。” 一為政治經濟學詞典的:“生產是以一定的生產關系聯系起來的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利用生產工具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資料的過程。” 這兩個在表述上略有不同的生產定義,不但也像以往的生產力定義一樣,只是關于人類物質生產的定義,而不是一般意義的生產的定義,存在片面性,而且同樣也存在定義不周延的問題。人類物質生產的定義,應能涵括人類不同時期和不同類型的具體生產,可是按照這兩個辭典的定義,人類初期先后出現的采集和狩獵,乃至現在也常有的捕撈自然水生物,就都不能被稱作生產。因為這些活動與動物的采集、狩獵并無不同,既不屬于“創造”,也不屬于“改變勞動對象”。于是,從這類人類物質生產的定義出發,就只能說人類初期沒有物質生產,且一直到今天也存在的捕撈自然水生物也不屬于生產。此外,這兩個辭典的定義還存在循環定義的毛病,這就是在對“生產”的定義語中,又出現了含有“生產”一詞的“生產關系”的用語,形成解釋的循環。
有鑒于以往學界在“生產”和“生產力”定義上的失誤,以及生產概念、生產力概念本應有的廣泛所指,現在給出這樣的定義:生產是有生命的活動者取得所欲對象的活動。這個定義中,“有生命的活動者”包括人和動物,是故生產就有人類的生產和動物的生產之分。正因有此區分并常有必要對人類的生產與動物的生產進行比較,所以在此定義里才使用的是“有生命的活動者”的表述,而沒有簡單地使用“動物”一詞。試想,如果“動物”這個概念的外延也包括人類,那么當我們說人類的生產與動物的生產有何不同時,豈不在邏輯上就是混亂不清的?猶如問:“男人和人有何不同?”更何況人類實際上也早已不是動物,而是超越了動物及動物世界已有多少萬年的另類活動者,亦即不同于動物的活動者。至于此定義為何要選用“有生命的活動者”的表述而不是“有生命的存在者”的表述,那是為了將有生命而不會活動也沒有任何生產的植物排除在該定義域之外。
又由于此定義語中的“所欲對象”既可以指所欲的“物”,也可以指所欲的“后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象,所以不論是人類還是動物,都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一種是對所欲之物的生產或說物的生產,一種是對所欲后代的生產或說生命的生產。根據我剛給出的一般意義的生產的定義和這兩種生產實際所存在的種差,可將這兩種生產分別定義如下:物的生產,就是有生命的活動者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之物的活動;生命的生產,就是有生命的活動者通過兩性結合取得所欲后代的活動。現在,還有必要解釋物的生產的定義語中的“勞動”,否則可能也會被懷疑存在定義循環。勞動與生產,以及勞動過程與生產過程,確實經常被人們混為一談,交換使用或當作一回事,實則有所不同。勞動是指有生命的活動者為所欲之物付出自己的體力和腦力,而勞動過程就是指這個付出體力和腦力的過程。這就是說,勞動強調“付出”,生產則強調“取得”。
綜上可知,“生產”這個概念如果其前面不加任何限定詞,就存在四種所指,這就是:人類的物的生產、動物的物的生產、人類的生命的生產、動物的生命的生產。與之相應,生產力自然也應有這四種所指。根據上面關于物的生產和生命的生產的定義和更前面對“生產力”的“力”的解釋,人類的物的生產力就是人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之物的活動能力;動物的物的生產力就是動物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之物的活動能力;人類的生命生產力就是人通過兩性結合取得所欲后代的活動能力;動物的生命生產力就是動物通過兩性結合取得所欲后代的活動能力。
人類和動物在生命的生產方面,沒有實質性差異,都是用身體器官取得后代,但在物的生產方面全然不同。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有前面已引述過的馬克思的那些解釋,而且還可以有其他形式的分辨。動物的物的生產幾近全部都是用自身器官進行的,只有極其少數的動物即靈長類動物和海獺,在極其偶爾的情況才用了天然工具。而人類的物的生產則相反,除了人猿揖別的初期,幾近全部都是在用自身器官的同時還要使用自制工具,只是在極其偶爾的情況才直接用自身器官,如用肢體搬運生產資料。這是一種差異。
如此又有一種差異。雖然在勞動方面人和動物都要付出體力和腦力,但在“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方面,還是存在差異。在動物那里,被作用的外在對象全都是自然的原材料和為數極少的天然工具;而在人這里,除了也有自然的原材料之外,還有種類越來越多的自制勞動工具。并且,在作為勞動對象的原材料中,也還有大量人為的原料,即經過加工或改良的自然原材料。
第三種差異是,動物的物的生產所取得的所欲之物,都是其需要的東西;人的所欲之物則除了有其需要的東西之外,還包括其想要的東西。因而動物的所欲就是“需要”。而人類的所欲,則是同時包含需要和想要的“需求”。“需要”屬于先天本性,是以自然界中的已有之物為滿足對象,因而動物生產的取得方式都屬于“獲取”;而“想要”屬于后天想象的結果,其滿足對象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只能通過自己的創造或制造來生成,因而人類生產的取得方式除了也有“獲取”之外,還有動物所沒有的“造取”。
人類所獨有的想要,不僅僅有物質方面的想要,也還有精神方面的想要,所以人的所欲之物的生產,就既有物質產品的生產或曰物質生產,又有精神產品的生產或曰精神生產。而動物的所欲之物的生產則僅有物質產品的生產。同時可知,人類的“所欲之物”和“物的生產”中的“物”,乃是廣義所指,既包括實體性的有形之物,也包括非實體性的無形之物。實體性的有形之物呈現為器物,非實體性的無形之物呈現為符號,故我們也可以將物質生產稱為器物生產,而將精神生產稱為符號生產。此乃第四種差異。
既然人類的物的生產與動物的物的生產存在以上四種差異,那么人類的物的生產力與動物的物的生產力自然也同樣會存在這四種差異。
生產或生產力的四種特殊形態或四種所指,可以被歸結為兩類,并且有兩種不同的歸類方式。一種是歸為人類的生產(力)和動物的生產(力)這兩類,每類之中又各有物的生產(力)和生命的生產(力)兩種;另一種是歸為物的生產(力)和生命的生產(力)這兩類,每類之中又各有人的生產(力)和動物的生產(力)兩種。根據第一種分類方式,被歷史唯物主義所特別看重的物質生產力,就屬于人類生產力中的物的生產力中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力;根據第二種分類方式,被歷史唯物主義所特別看重的物質生產力,就屬于物的生產力中的人類的物的生產力中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力,與之相對的另一類是精神產品生產力。人類的物質產品生產力和精神產品生產力有所不同,前者取得的所欲之物是物質性的,后者取得的所欲之物是精神性的。因而物質產品生產力就是人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物質之物的活動能力,精神產品生產力就是人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精神之物的活動能力。
人類的物質產品生產力包含兩種實體性要素。一是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的人即生產力中的勞動者,也可謂生產者;二是被勞動所作用的外在對象,既包括作為勞動原料或生產原料的對象,即用于生產勞動的原料,也包括作為勞動工具或生產工具的對象。至于該活動能力最終取得的所欲之物即勞動果實,或曰產物、產品,則是已被勞動改變了的原料。在這一生產力所包含的兩類實體要素中,以勞動作用外在對象的勞動者屬于主體,居主導地位;被勞動所作用的外在對象屬于客體,處于被主導的地位。
與人類的物質產品生產力一樣地同屬于人類的所欲之物的生產力的精神產品生產力,自然也同樣包含有這兩種實體性因素,以及主體、客體之分。所不同者是物質生產力的外在對象一般都包含有自然物;而精神生產力中的外在對象,亦即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都是筆墨紙張、電腦、膠片、舞臺、影視等信息媒介一類的人工制品或人為物質,即便是用符號表達的最終產品,也還是要借助于一定的人為物質性載體方能得以顯現。
既然人類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全都在于要得到所欲之物,那么,人類的物的生產之目的就是為了取得所欲之物,即能滿足自己需求的產品;而發展人的物的生產力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取得所欲之物的活動能力。
三、重構生產力定義的意義
最后,似有必要再通過簡明的總結來凸顯本文重構新生產力定義的意義。
第一,本文之所以要重構新的生產力定義,乃是因為國內外學界關于生產力的各種已有定義不但僅僅是關于物質生產力的定義,而且就是這種特殊意義的生產力定義也都存在不足,均未能揭示出物質生產力的本質。尤其是國內學界關于物質生產力的主流定義,由于其重點在于強調“改造自然”這一點,不僅未能比前人更接近物質生產力的本質,反而偏離得更遠。因而重構新的生產力定義,就是要扭轉這些不良狀況。
第二,本文之所以要將生產力分為一般意義的生產力和四種特殊意義的生產力,并先后分別對之進行定義。一是如果不知“一般”,就無法說清楚“特殊”,因“特殊”總是相對于“一般”而言的。所以,從邏輯上講,也應先給出一般意義的生產力的定義,再來定義各種特殊的生產力。二是如果我們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和動物都有生產的說法,認同他們關于生產又有物質生產和生命生產之分的觀點,以及認同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劃分與表述,就應當在理論上給出關于這些分類意義上的特殊生產及其生產力的定義,并使它們相互之間及其與一般意義的生產力定義之間,都內在地保持一致或統一。易言之,在學理上,只有對一般意義的生產力和特殊意義的生產力都有定義,并且是那種邏輯自洽的定義,才能使整個生產力理論完善起來。
第三,本文之所以將歷史唯物主義所看重的物質生產力定義為人通過勞動作用于外在對象而取得所欲物質之物的活動能力,除了在于這個定義能將馬克思在解釋物質生產及物質生產力時所著重強調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勞動”、“人的需要”都有機結合地涵括于內,更在于此定義就是對物質生產力的本質的準確揭示,因為它不僅與一般意義的生產力定義保持一致,而且也能將自己與其他各種特殊意義的生產力定義從種差上區別開來。所以說它應該已是一個可以經得起任何拷問的定義了。
有喻道:基石正,大廈亦正;基石歪,大廈亦歪。凡以生產力為第一范疇的理論大廈,都應讓自己的生產力定義不生偏差。本文所給出的這套生產力定義就可以為這種理論大廈的合理建構預先提供一個端正而堅實的基礎。
注釋:
①③⑥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80、46—47頁。
②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2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頁。
⑨ 參見王偉光:《生產力概念歷史考》,《理論前沿》1993年第9期;吳成達:《生產力概念的歷史考察》,《管理觀察》2009年第5期。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頁。
馬克思主義哲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頁。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編寫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張志成、張佐友等主編:《生產力經濟學辭典》,立信會計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9—993頁。
此段所用資料參見于姜海波:《國外學者論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求是學刊》2007年第6期。
《辭海·哲學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頁。
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頁。
作者簡介:韓東屏,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4;胡丹丹,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湖北武漢,430074。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