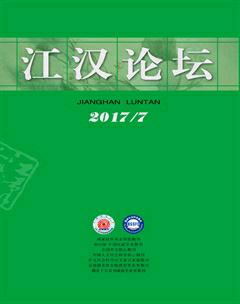象牙塔的陷落?
肖楚楚+樊星
摘要:二戰后英美大學、學界生態、學者處境的風云變化反映在文學中便是學界小說主題的不斷深化和拓展。脫胎于校園小說的文學傳統,學界小說多以諷刺的基調反映大學校園及學界的各種亂象,揭露骯臟的學術政治、荒唐的情愛逸事和學者生活的個人悲劇,戳破人們對學者、學界、大學的烏托邦想象,卻也嚴肅甚至憂傷地探討著個人生命意義、學術自由及教育困境等現實問題。走出坍塌的象牙塔,退去神圣光環,人們才能對學者、學界、大學有更多期待。面對現實世界中暗潮涌動的高等教育和學界風云,學界小說雖有局限,卻充滿生機,依然具有無限可能。
關鍵詞:學界小說;大學;學界;想象的烏托邦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7-0078-05
一、從“校園小說”到“學界小說”
在世界文學中,以大學校園為背景的小說并不罕見,但多零碎散落,統歸在“校園小說”這一豐富龐雜的概念中。然而在內容豐富的英美文學中,卻衍生出以大學為背景、以教職員工為主人公的學界小說這一獨立的小說(次)類型,成為二戰后當代英美小說中引人注目的一個分支。
二戰后英美對教育的投入以及大學準入門檻的降低,不僅為退役士兵提供了教育機會,也接納了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使得大學不再是封閉的象牙塔或貴族精英的自留地,轉而向社會大眾敞開了它的大門。然而教育的特殊性又始終賦予大學一種世外桃源的超脫色彩,與當代大學的本身形態——除正常的教學之外,它還為相關人員提供食宿、醫療、金融等一切服務,儼然是一個日常自足的小社會——產生一種微妙的矛盾性,為小說創作提供新的出發點。另一方面,創意寫作專業在大學的普及培養了眾多有大學經驗的作家,再加上曾經長期游離在學界之外的作家群體也樂于在大學內部尋求一份安穩的職業,大學與大學中人自然也就成為他們觀察和寫作的素材,與大學有關的故事就這樣豐富了起來。
在大學校園中,學生自然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青春記憶與校園情結緊緊相連,曾經占據了校園小說的絕對主流。但與終將畢業的學生們相比,教職員工特別是學者們才是大學校園中真正的長期住戶和核心人物。因此,當學者的生活、院系間的故事越來越多地為普通人特別是作家所熟悉,以教職員工為中心人物的學界小說自然也就成為一種新興的小說類型,成為作家筆下常見的故事,也開拓出了新的文學園地。
雖然學界小說在二戰后就初現雛形,但在英美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乃至新世紀之前,學者仍習慣于將“學界小說”劃歸在“校園小說”中來研究,對學界小說也沒有單獨的命名。但隨著學界小說創作的繁盛,文學研究者們也日益意識到學界小說的“個性”,將其從“校園小說”這一大類型中劃分出來,成為一種單獨類型。小說類型的分界常常是模糊且交叉的,因而梳理這一從“校園小說”到“學界小說”的變化過程就顯得必要,有助于我們對“學界小說”概念的認知。
英美文學歷來有關注校園文學的傳統,如學者們常常提到的普羅克托在《英國大學校園小說》一書中就對英國19世紀的校園小說進行了細致研究,但彼時的校園小說,主要還聚焦于大學生的學習生活。而在學界小說的研究中,里昂和克萊默的貢獻則功不可沒。
里昂在其著作《美國校園小說》中認為校園小說是關于學術生活的小說,它們對待高等教育的態度應該是嚴肅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可以是學生也可以是教授。因為強調一種“嚴肅性”,里昂把以校園為背景的青少年讀物和謀殺、偵探、滑稽等通俗小說排除在外,大致限定了學界小說的范圍和基調。克萊默在里昂研究的基礎上,對美國1828—1979年間可被稱為“校園小說”的作品進行細致收羅和介紹,在其著作《美國校園小說:目錄與提要》的序言中,將校園小說的主要場景限定在高等教育機構內,小說的主要人物則可以是研究生、本科生、院系教員、行政人員,以及其他與學術相關的人員,同時他明確列出了八類與上述定義相關但并不屬于校園小說的作品①。最重要的是,在正文中克萊默將每一時段的校園小說都區分為以學生為中心和以教職員工為中心的兩類來加以介紹。之后的學者常常認可并借鑒克萊默的分類方式,將以學生為中心的小說依然稱為“校園小說”;將以大學教師為中心的小說稱為“學界小說”。
類似的,在中國學界,對英美文學中的這一類小說的命名和翻譯也并不統一,除了較籠統的“校園小說”的譯法,宋艷芳、張榮升、李莉等學者習慣采用“學院派小說”這一說法,新星出版社引進布雷德伯里的《歷史人》、盧里的《愛情和友情》,以及上海三聯書店出版肖爾瓦特的《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時采用的則是“學界小說”這一譯法。
根據宋艷芳的定義,“學院派小說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熟悉學界生活和小說創作技巧、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學院派作家創作的,以大學校園或高等教育、科研機構為背景,以大學生、教職工、教授、研究員等為主要人物,以諷刺的筆調討論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知識分子境遇等話題,在滑稽幽默的表象下揭示學院生活百態的一類小說。”② 這樣的定義自然詳細而全面,但“學院派小說”這一譯法容易將焦點從小說的背景、題材、情節、風格轉移到作者“學院派”的身份上,強調作家的專業背景和寫作深度。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學院派作家”,不如說是“學院內作家”,學界小說的作者確實有不少是教授創意寫作的老師,或者本身就是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學者,但對前者來說,他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作家而非教授、學者;對后者來說,學術研究和小說創作則是完全不同的經歷和狀態,如果一定要說“學院內作家”的“自我指涉、炫耀理論知識、引經據典以及后現代主義的游戲性”③,那只是源于他們自身的知識素養和生活環境。因此本文更愿意采用“學界小說”的譯法,更加關注小說的背景和人物,賦予其更多的靈活性。
二、從“象牙塔”到“小世界”:學界小說主題探究
大學曾有“象牙塔”之稱,隱于其中潛心學術,既能逃避庸常瑣事的煩惱,又能遠離現實社會的重重矛盾,還能獲得探求知識與真理的快樂與滿足,給人以超凡脫俗之感。但在學界小說中,大學從來都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世外桃源,終身教職的壓力、科研時間的缺乏、難以教導的學生、費時費勁的行政瑣事,院系內部或院系之間的學術政治、官僚作風,抑或由多情或好色的教授惹出來的風流韻事、流言蜚語,一直游蕩在這個看似封閉的小圈子內,難得安寧。若是學界小說的忠實讀者,在閱讀不同作品時,一定會有一種熟悉感,甚至感嘆五十年前的學界小說和五十年后的學界小說是何其相似,無休止的院系紛爭、學者間的明爭暗斗,以及源源不斷的桃色新聞,似乎貫穿了整個學界小說發展史,曾招致重復性過高、模式化的批評。
然而一旦打破對學界小說的刻板印象,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隨著戰后校園人口的增加和多元化,“學界”早已不是過去那個完全封閉的、由少數精英掌控的象牙塔,而是隨著外在世界的風云變幻不斷變化,圍城內外的差別也在進一步縮小:學者的活動范圍不再局限在校園之內,他們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可以居住在校園之內,而必須頂著經濟壓力自己解決住房問題,自然與大世界發生了關聯;學者之間的交流也從一系、一校、一地、一國走向了全世界;大學制度的改革使得教授治校與行政擴權之間的沖突也將更多的矛盾帶入了大學校園;最重要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學者們的處境和心境早已不同于往日。因此,在看似風平浪靜、按部就班的教學生活之下,學界小說的主題實際在不斷變化和擴張。
學界小說的內容十分豐富,每個時代都涉及諸多話題,但以各個時代經典的學界小說為代表,展開深入研究,還是能整理出一條粗略的發展線索。在學界小說初現鋒芒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小說的關注點還比較局限于院系內部的權力斗爭、教員聘用、獲取終身教職等話題。斯諾的《大師們》描述了多人競爭院長寶座的故事,其中,年輕教授麥克斯·南丁格爾為了能獲得最大限度的回報,采取各種卑劣手段將一個名不副實的競選人推上了院長之位。在麥卡錫的《學界叢林》中,英文系教師亨利·瑪爾克西既不是合格的老師,也不是合格的學者,在面臨被解雇的危急時,只能通過傳播謊言、利用他人同情、鉆制度漏洞等手段保住了自己的教職。在作家們筆下,看似清高的學界和人們想象中的政界一樣骯臟,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或者為了爭取更高的職位,道貌岸然的學者一樣可以采用言語攻擊、傳播流言、撒謊博同情等不道德的手段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60年代的學界小說慢慢走出了院系和教職的封閉回廊,出現新的主題,開始關注學者作為個人的生存狀態,也漸漸與婚姻家庭、中年危機等敘事匯流。如盧里的《愛情與友情》描繪了生活在康弗斯校區內一家中產階級夫婦追尋生活出路的故事,雖然小說中充滿了學術生活和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但主線還是一段由不知是愛情還是友情的曖昧感情引發的震蕩。
七八十年代被視為學界小說發展的一個巔峰,雖仍以學界或校園為聚焦點,依然醉心于學界政治和學者們的情愛逸事,卻也折射出當時社會、政治與文化生活的巨變。在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的《歷史人》中,社會學家霍華德·科克和妻子秉持貌似激進的政治觀點和極為現代的婚姻觀念投入社會的政治風潮中,卻事與愿違,跌入自我迷失與沉淪的深淵。在對他們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雙向書寫中,小說描繪出一個盛行極端自由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混亂時代,同時也展現出個人內心的不安與痛苦。戴維·洛奇的《小世界》則揭露了當代學術界的空泛與浮華。小說采用類似“圣杯傳奇”的結構,展現了國際學術會議中的學者百態。在各種學術會議中,相比言之有物、通俗易懂,學者們似乎更愿意用一些時髦的理論術語堆砌出即使是同行也不懂的晦澀論文,更投機地把同一篇論文改頭換面之后便用于另一個學術會議。至于熱鬧的國際學術會議,已變相成為學者們的公款旅游和社交游戲,成為他們提升學界聲譽、打擊學術對手的工具,反倒失去了學術交流的意義。
正如《小世界》的副標題An Academic Romance的直譯——“學者羅曼司”所表明的,在學術式微的同時,欲望敘事,特別是與性愛有關的敘事,大量出現在學界小說中。除了對聲譽和權力的追求,學界小說自然少不了學者出軌外遇、追逐性愛的情節,戴維·洛奇的《換位》中兩位教授互換工作、職位,乃至互換妻子、家庭的故事早已為人熟知;《欲望教授》中沉迷于瘋狂性愛游戲,又在婚姻與愛情中迷失自我的主人公也并不是個例。
20世紀90年代及之后的學界小說延續了之前小說主題不斷擴大的趨勢,學界似乎更多的成為了一種背景,學界小說不再限于學科、院系之間及內部的爭斗和圖謀,進一步融入更廣闊的社會文化之中。正如威廉斯所認為的,近20年來的當代學界小說早已不是曾經被認定的孤立的、古怪的小圈子文學,而與主流的文學類型匯流,延續著學界小說的生命力④。經歷了新的文化浪潮,學界小說也成為了文化戰爭的舞臺,使得學界小說常常可被看作是充滿影射和諷刺的真人真事小說;學者的光環進一步退去,中年危機、就業壓力,都是逃不開的話題,學界中人越來越成為后現代社會的普通一員。
三、諷刺的基調與笑中帶淚
學界小說的主題雖不斷變化,但似乎始終證明著大學從來都不是常人想象中超凡脫俗的象牙塔,其中學者的形象,也正如西方文化對“象牙塔”中人脫離現實生活從事學術研究的指責,常常是敏感懦弱而不通世故的窩囊廢,沉迷于疊床架屋的理論而對現實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在書本和現實的脫節中苦苦掙扎。至于那些能夠主動融入時代大潮的學界泰斗和校長院長們,雖然表面光鮮亮麗、彬彬有禮,能夠獲得基金支持和學界名聲,卻也總被揭露出陰暗狡詐的一面,要么被描繪成濫用權力的好色之徒,要么被塑造成唯利是圖的野心家,因此學界小說的基調常常是諷刺的,某種程度上恰好符合了局外人對當代大學的失望和刻板印象。正如沃麥克所說,學界小說簡直就是一場能夠摧毀現代大學的知識、真理、智慧的寡廉鮮恥的利己主義者的展覽會。
學界小說的諷刺性自然不必多言,戰后世界的迅猛發展鬼使神差地塑造出了一個追求效率和利益的當代社會,學界小說中許多“失敗者”的痛苦一方面源自精神世界被物質世界所擊碎,另一方面則來自于自身敏感懦弱的性格,在令人同情的同時,也讓人反思學者在新時代該如何自處;過于順應潮流的“成功者”又常常為獲取地位、聲望、金錢、美色而采用各種不正當手段,盡顯卑劣和無恥,由此,小說的諷刺批判色彩就十分明顯了。
那么,學界小說中對學者的描述是否太過刻薄,對學界黑暗面的揭露和對大學教育灰暗的描繪是否又太過夸張,是否是現實學界的反映和代表?不少學者堅決主張學界小說的真實性,亨利·貢夏克說:“這些小說中對學界黑暗面的描繪,雖然有夸張的成分以滿足戲劇效果的需要,但基本上是真實的。我可以很容易地再寫一篇文章,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不是小說中的虛構來舉出各種學界不端行為的例子——專業投機者,制造陰謀,惡意告狀,同事勾心斗角,教授死木頭,忽略教學等。”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界小說描述的學術生活與學者的日常生活太過脫節,只是為了產生沖突、寫出讓人感興趣的故事才熱衷于揭露學術生活的枯燥乏味、披露學界中的各種丑聞,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件聚集起來寫在了一部小說中,過于夸張,而缺乏公平和真實,這也是許多學界內讀者不喜歡學界小說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諷刺之外,對學界內讀者特別是學界小說的研究者來說,學界小說還有另一重普通讀者容易忽略的魅力——“學界小說中最吸引我的卻是它的嚴肅性,甚至可以說是悲哀。我們這些教授之所以求助于諷刺,或許是因為學術生活中充滿了無盡的辛酸苦痛,多少人被糟蹋或毀掉了”⑤。無論是學界內作家作為局內人來“觀察同事們之間的部落式的禮儀”然后創作學界小說,還是出于孤芳自賞使得大多都是英語系教授的文學批評家們“樂于為英語教授創作的描寫英語教授的小說撰寫文學評論”⑥,作為大學及學界的長期住戶的學者們,總是更能懂得學界小說諷刺中的那一點“淚”。學術研究本身就是孤獨的,在年復一年的學術時間和學術壓力之外,他們也不得不承受普通人都要承受的生活壓力。曾經自以為崇高的學術追求,卻在無奈中被現實壓力磨平了棱角,現實生活經驗和經典著作中崇高道德的沖突更凸顯出現實的灰暗。希望的破滅,對生活和學術追求的反思和懷疑,以及對生命本質的嚴肅思考,這些常常是只有學界內部人才能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
《大師們》等早期學界小說雖然揭開了學界政治的亂象,但彼時的教授對于自身的社會價值都毫不懷疑,認定學術生活是值得擁有且為之獻身的;或如金斯利·艾米斯的《幸運的吉姆》,無論歷經多少倒霉與麻煩,最終卻仍能重獲獨立生活、收獲真正愛情,以成功者的姿態離開學界。即使是《學界叢林》中的瑪爾克西所使的陰暗手段,也能顯示出大學權力機構對學術和政治自由的尊重——當時的大學,仍可被視為學者的庇護所。《小世界》雖然從單個封閉的校園擴展至世界范圍內的整個學界,但終究還是局限在了學界內部,但到了唐·德里羅的《白色噪聲》、 理查德·魯索的《正派人》及之后的時代,學者們已無法在學術研究中確立自我的價值以獲得成就感。教授自治和行政擴權之間的矛盾在共同掌權中導致了更為官僚化的體系,對于學術成果的強調以及教學本身不受重視限制了學者上升的空間,終身教職的縮減以及簽約制的盛行使得學者這份曾經安穩的工作也似乎岌岌可危。大學已無法為學者提供足夠的保障,婚姻、家庭、生存各方面的壓力撲面而來——學術已然不是學者生活的中心,在風雨中飄搖。
至于學界小說探討的另一問題——質問大學教育的本質和目的,則更難形成共識。學界小說中的大學,既是一個實體存在的高等教育機構,又代表著人們對大學這一理念的想象構建;人們一方面既希望大學能延續“象牙塔”中好的一面,能夠以知識和真理本身為目的,與功利、復雜的現實世界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學能教給學生切實的生存技能,找到好的工作,獲取好的生活,不與現實脫軌。這樣的矛盾貫穿整個現代大學發展史,自然也反映在小說中,學術生活在16—18世紀的文學作品中常常是保守批判的,充斥著腐化愚昧的大學教師(尤其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和浪蕩墮落的大學生們;19世紀在牛津和劍橋發生的改革也相應地反映在19世紀晚期的小說中,開始把大學、學生、教師都塑造為更加正面且備受尊敬的形象。到20世紀初,大學生活已被描繪成一種浪漫的理想形態,正是普羅克托在《英國大學校園小說》中所說的“牛津崇拜”。二戰之后的學界小說則告訴我們,大學教育往往承諾很多,實現的卻很少。
受難于反復無常的世界經濟衰退和大學預算縮減,學術研究更多地受資本控制和影響,高等教育似乎逐漸變成了一種學術資本主義,走向實用主義,不再是教導宇宙真理、教人如何道德自律地思考與言行的精英教育,轉而成為一種成果可供衡量的大眾化教育,向著“職業化”的方向發展,從一個追求真理、知識、人文價值的“大學”變成了培養工程師、經理人、律師、商人的職業培訓機構,而學生則變成了消費者,家長變成了投資人,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找到一個得體且安穩的工作,而不是成為一位有修養的知識人。
美國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曾于1984年出版《走出象牙塔》一書,希望美國大學走出“象牙塔”的牢籠逐步融入社會中去,但“醉心于追逐利潤”的商業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沖擊,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學之道,寫作出版《回歸大學之道——重塑大學教育的目標》一書⑦。然而高等教育的普及雖喪失了過去的精英感,但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如今美國已有70%以上的公民能接受大學教育,與百年前只有1%富家子弟能進入大學的比例相比,大眾化教育顯得十分必要。因此大學教育真正的問題也許并不全在于大眾化和職業化,而在“聚斂財富和道德缺失”的功利性。學界小說反映出功利化社會中大學面臨的困境,與人們想象中的大學大相徑庭,自然也就有了文學的諷刺及其背后的嚴肅與憂傷。
四、重建烏托邦
英美學界小說中的許多主角都是人文學科例如英文系的教授,對這些深諳人文主義傳統的學者來說,他們似乎更愿意遵循歐洲大學的古老傳統,將獨立、自治、民主、自由和批判精神視為大學的本質和精髓,以學術為志,保留“象牙之塔”的環境,因此面對迅猛發展的現實世界,常常表現出一種手足無措和無所適從。因此,無論是學界小說的作者還是研究者,在單純的憤怒和氣惱之外,在對高等教育的冷嘲熱諷之中,常常暗含著一種改變現狀的期待,希望學者和大學都能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在后現代主義理論盛行的時代,重申善良、美德、責任的價值和意義——傳統大學的理念以及知識分子的神圣感并不曾完全消失。大學之所以與諸多社會機構不同,就是因為它并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始終承擔著追求和傳承知識真理的重任;多數愿意成為學者的人也并非是為了大富大貴才進入這個領域,他們最初都懷有一份自由科研、教書育人的純潔理想。相對于其他行業,學者依然是一份令人羨慕和崇敬的工作,有一份相對穩定的薪酬,一些不受監督能夠自主安排的時間,以及追求知識的自由——無論有多少負面聲音,人類始終抱有追求知識和真理、自由的熱情。
但正如肖爾瓦特所說,“所有的烏托邦最終都不免流于乏味”。學界小說的諷刺和嚴肅,一方面正印證了我們對大學和學者的過度想象,只將大學看成是一個能夠進行獨立思考和學術研究的烏托邦,而忽略了現代大學在博雅教育之外,可能和其他機構一樣需面對現實、考慮職業教育的問題,而學術界自然也和其他行業一樣中立,無所謂更好或更壞;而大多數學者也并不能完全逍遙隔絕地沉浸在學術研究之中,他們一樣有人性的弱點,一樣有物欲和性欲,一樣有生活重壓以及“發表還是毀滅”的學術壓力。在一個不斷祛魅的后現代社會,要將包括學者、學術、大學在內的任何事物推向中心或神壇都希望渺茫。如今,象牙塔的坍塌似乎已成共識,理想主義的失落自然會激發感傷、沮喪和絕望,但并不一定都是壞事,“當前學界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憤懣可能是夸大其辭,但是,對英語系及其居民或許不抱有田園詩般的幻想,才是更健康、更明智的做法。”⑧
學界確實是個小世界,卻與大世界緊密相連,能在其中觀照自身的,不只是小圈子內的學者型讀者或學院派的批評家,而應該是每一個人,自有自己的苦樂和無奈。至于學界小說,面對現實世界中暗潮涌動的高等教育和學界風云,依然具有無限可能,相信學界小說的作者們,一定能不斷突破自身的局限,寫出更多雅俗共賞的好作品。
注釋:
① 這八類作品是:短篇小說集、商業目的極強的青少年讀物、科幻小說、懸疑小說、僅涉及校際或學院間運動題材的小說、以西點軍校和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為場景限制的小說、主人公雖然是教職員工和學生但主要情節與學術無關的小說、以情色為主題的商業性小說。
②③ 宋艷芳:《學院派小說》,《外國文學》2013年第6期。
④ Jeffrey J. Williams, The Rise of the Academic Novel,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12, 24(3), pp.561-589.
⑤⑥⑧ 肖爾瓦特:《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124、13頁。
⑦ 參見劉道玉:《中國教育反思錄》,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7頁。
作者簡介:肖楚楚,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樊星,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