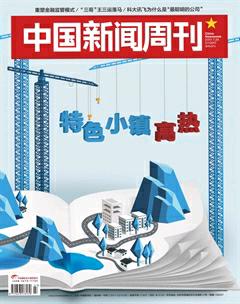見墓如面
阿冷
生如夏花,逝如秋葉,就如同大自然本身。
在旅行中,我喜歡去看墓地。
西人的教堂往往有墓園或者墓堂。最特別的一個教堂,是捷克的人骨教堂,位于布拉格以東約70公里的小鎮庫特納·赫拉。14世紀的黑死病和宗教戰爭導致歐洲尸橫遍野,傳教士們為了安慰亡靈,帶人搜集了遺骸,清洗整理后用來裝飾教堂。于是,就有了這座人骨教堂。
幾百年的時光,人骨并未腐朽垮塌,給人的感覺不是腐爛和黑暗,而是整潔而精致,滿足了一個處女座強烈的秩序感。燭光下,人骨組成的燈架、盾牌和墻飾很是別致,甚至有俏皮之感。對于有信仰的人,無論是教堂建造者,還是這些遺骸自身,這里一定是通往天堂最近的路吧,這樣的路理應沒有恐怖,充滿笑聲和歌聲。
在意大利比薩,游客們對著斜塔擺出各種姿勢照相,我倒是對斜塔旁邊的納骨堂一見傾心。這是座長方形回廊建筑,白色大理石,鏤空式大窗格,陽光隨意潑灑進來,仿佛一曲輕松的小步舞曲。
其實要論西方教堂陵墓,位于佛羅倫薩圣洛倫佐教堂的美第奇家族陵墓是最偉大的,沒有之一。這里所有雕塑都出自米開朗琪羅之手,雖然沒有完全完工。面對以《晝》《夜》《晨》《暮》命名的四座雕塑,會覺得從大理石中誕生的人物充滿生命的復雜和彷徨。這是藝術史上的巔峰,以我微薄的見識,不敢造次去論述和評價。
據說,佛羅倫薩詩人喬凡尼·巴蒂斯塔·斯特羅茨見到《夜》后,寫下了一首熱情的詩:“夜,為你所看到嫵媚的睡著的夜,那是受天使點化過的一塊活的石頭;她睡著,但她具有生命的火焰,只要叫她醒來——她將與你說話。”米開朗基羅讀后殊為傷感,用另一首詩作了酬答:“睡眠是甜蜜的,成為頑石更幸福;只要世上還有罪惡與恥辱,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于我是最大的快樂;不要驚醒我啊!講得輕些。”
米開朗琪羅本人的墓堂,卻沒有這種百轉千回的感覺。他的墓位于佛羅倫薩圣十字教堂,與但丁、伽利略、馬基維利、羅西尼等同居一室,墓雕由他的學生瓦薩利設計。我一直在想,瓦薩利在設計的時候,是不是壓力山大,弄得不好,老米會從石棺里蹦出來大罵這是神馬破玩意兒吧?估計瓦薩利也是這么想的,所以本著中規中矩不出彩也不要出錯的宗旨,替老米刻了個胸像,以及三個人物雕像,分別代表老米在繪畫、雕刻和建筑上的藝術成就。看上去,真的蠻平庸的。不過也不要緊,梵蒂岡西斯廷小堂,在末日審判的群像中,老米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留下了自己的自畫像。
我的一位好友是作曲家,她曾獨自一人去拜訪在奧地利的莫扎特墓,坐了很久,跟墓主對話,她說:“你知道嗎,因為你,造就了我的音樂人生。”
作為一個更傾向于無神論的人,我常常覺得,墓園其實是為了生者而設。亡者已經煙消云散,無知無覺,是榮光大葬也好,挫骨揚灰也好,都沒什么區別。是生者需要這些,來彌補失去和撫慰傷痛。當人們站在一塊實地上紀念憑吊時,才能確認那些過往真實存在過,也才可以更鎮定地面對每個人終將面對的命運。
我所見過世間最美麗的墓,是奧黛麗·赫本的墓。

捷克人骨教堂內景。
瑞士莫爾日是一個安靜的小鎮。奧黛麗·赫本最后的居所。只知道她的墓在小鎮附近,但不知道在哪個方向,于是跑去問路邊三個老人。
三個老人很和氣也很熱情,只是他們完全不懂英語,我們完全不懂法語,歡快地聊了半天,誰也不知在說啥,彼此唯一聽懂的就是奧黛麗·赫本這個名字。同伴祭出手語大法,做了個睡覺的姿勢,又做了個掩埋的姿勢,老人家們恍然大悟,其中一個指著一條街的方向,往前一伸胳膊劃了條直線,又使勁畫了個圓圈,然后做了個斜上方的示意。我們還是有點茫然,他只是反復做這幾個動作。我們只好假裝完全明白了,順著他指的方向先走著。
走到路盡頭,我們倆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圓圈是環島,環島過去就是來時汽車上看到的那個小山坡,斜上方自然就是爬上這個山坡。墓園就在那棵樹邊。推開低矮的木柵欄門走進去,奧黛麗·赫本墓很好找,墓地上的小天使像和墓前的鮮花是如此醒目。她的墓很樸素,只有名字和生辰。《羅馬假日》的公主就長眠于此,見墓如面。
晚上在莫爾日小鎮上的中餐廳吃飯。老板娘是一位華人阿姨,很親切,我們點了很多菜,被她制止了,一再說你們吃不了。阿姨來瑞士幾十年了,說80年代末的時候在超市見過赫本一次,我們趕緊問她怎么樣怎么樣。
雖然時隔那么多年,阿姨依然有點激動地說:“風采無可抵擋!”我跳起來說:“阿姨我們要跟你合個影!見不到赫本,見到你也好幸運。”
在《夏日走過山間》一書中,約翰·繆爾這位美國國家公園之父在約塞米蒂留戀忘返,在自然的風貌和樹木花草的榮枯中,欣賞著“如生命般美麗的死亡”。我覺得,參觀墓地也有如欣賞這種美。生如夏花,逝如秋葉,就如同大自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