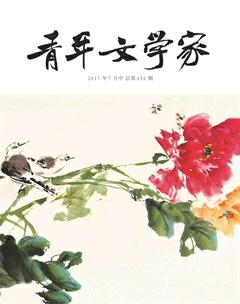探尋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的真正價值
摘 要:從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的發(fā)生的淵源背景、五四新文化運動參與者所發(fā)表的言論,以及對所謂文學革命的偏激之處進行再解讀,三個方面對“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造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斷裂”的論調進行駁斥、論證探尋。
關鍵詞: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文化斷裂
作者簡介:張雪怡(1993.2-),女,漢族,河南信陽人,河北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現(xiàn)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01
隨著近年以來“國學熱”的興起,以及市場經濟下人們信仰、價值觀念的缺失,傳統(tǒng)文化再一次引起重視。而以反傳統(tǒng)為核心的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再一次進入人們視野,并興起了關于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造成傳統(tǒng)文化斷裂的論調,把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失落歸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上,指責五四一代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否定,而造成的近百年的文化“斷裂”。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是否造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還是要重新回到歷史現(xiàn)場,來進行探究。這種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顛覆的批判,脫離了整個歷史語境,并未做到尊重歷史。
首先是要從源頭來證實新文化以及五四文學革命并未造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對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歷史背景的探討。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結束了中國天朝大國的神話。中國人民各階級階層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而封建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巨大阻礙。1911年發(fā)起的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但革命派所期望的宣傳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卻并未實現(xiàn),根深于中國民眾頭腦中的君權觀念、綱常名教和封建傳統(tǒng)思想依舊“統(tǒng)治”著人們。利用人民大眾這一思想上的局限性,封建舊勢力反攻倒算,北洋軍閥掀起了“尊孔復古”的逆流,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于1917年扶植溥儀復辟,康有為也主張要把孔教奉為國教并列入民國時代的憲法。這一系列擁護帝制的逆潮,才使得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發(fā)動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在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上進行變革,就此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人物以《新青年》為思想陣地,以中西文化對比的方法,來抨擊各種傳統(tǒng)觀念。就現(xiàn)代人怎樣對待孔子和儒家問題展開了爭論,作為對復古逆流的批判,以達到維護共和政體的目的。
其次,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否造成了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最直接的依據是要從革命參與者入手,從他們在運動中所發(fā)表的一系列言論取得實證。自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開始,陸續(xù)發(fā)表了易白沙、高一涵、李大釗、吳虞等人的各種論說。猛烈地抨擊了孔子和傳統(tǒng)道德,易白沙在《孔子評議》文中所說“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志,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于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此來評判歷代統(tǒng)治者借孔子為偶像來實行自己的獨裁統(tǒng)治的不合理性,從而反對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張勛的復辟。
李大釗所言道“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提到了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對象問題,明確了批判的并非孔子本身,也非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是歷代為統(tǒng)治者為謀權而利用的偶像權威。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中的評孔批孔,絕非針對整個傳統(tǒng)文化以及孔子本身,他們抨擊的是傳統(tǒng)文化的劣根性,以及以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權威、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專制主義文化。
當然當代學界一直總要詬病這場文學革命的偏激之處,甚至把后來“文革”的過錯以及當今人文精神的缺失也全部算到五四的賬上。其實自己也犯了偏激之錯。不可否認的是新文化五四文學革命先驅者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的態(tài)度確實是決絕的。但作為五四運動的先驅在無先驗者的情況下進行革新難免要犯幼稚病,對革命的理解有所偏激;但要對傳統(tǒng)文化中的封建性、落后性的東西進行猛烈批判,他們就必須通過這種偏激,來調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庸思想,來達到革命應達到的預期效果。五四先驅者之所以采取決裂的姿態(tài),也是出于對中國傳統(tǒng)中庸思想的考量,通過這種偏激,來調和中庸.另一方面,人們只注意到新文化五四一代的偏激、不寬容,而忽略了舊有思想保守主義代表者的強硬與決絕。新舊之間本身就存在著立場差異、有利益糾葛,雙方均不能做到坐下來平心靜氣、條分縷析地討論問題,因而雙方必然會引發(fā)一場罵戰(zhàn)。這樣把五四一代的偏激置于“舊壘”之中,放于新舊雙方尖銳矛盾之下,那么學界對五四一代“偏激”的譴責就太過極端化。由此可見,“偏激”并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方面,雖有幼稚之處,但這場運動確實是先驅者理性的建樹,對中國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理性選擇。
無論是肯定或否定,脫離總體歷史即成為片面的抽象的論證,任何理解都有理解者本身的歷史性因素在內。歷史離不開歷史解釋者本身的歷史性。我們能做到得就是從歷史現(xiàn)場取證,來論證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革命的價值。在今天這種完全嶄新的條件下,來獲得對歷史和現(xiàn)實清醒的自我意識,而不是一味地抨擊與批駁,要從而在歷史的探尋中尋求文學革命的真正價值。
參考文獻:
[1]易沙白.孔子平議,上下篇,載《新青年》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第2 卷第1號,1916年3月.
[2]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載《甲寅》,1917年3月.
[3]陳獨秀.憲法與孔教,載《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
[4]溫儒敏.《新青年》并未造成文化的斷裂,載《中國青年報》,2015年5月.
[5]嚴家炎.“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問題之考辨,載《問題研究》,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