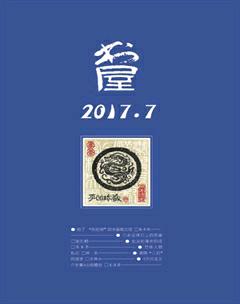《芥川龍之介全集》出版感言
文潔若
面對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芥川龍之介全集》,便是面對一顆純粹、深邃的心靈。煌煌五大卷,洋洋三百萬言,乳白色封面,裝幀設計樸素大方。他是迄今唯一的一位能在中國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由主編高慧勤、魏大海以及陳生保、鄭民欽、羅興典、林少華等十五位合譯,個個都是日本文學翻譯界的佼佼者。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代的短篇小說巨擘。自1915年起開始出席夏目潄石的“木曜會”,從此拜這位長他二十五歲的文壇泰斗為師(魯迅曾稱譽夏目為“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青出于藍。夏目的《趣味的遺傳》和芥川的《將軍》,同樣是以日俄戰爭為背景寫乃木希典,芥川的思想境界卻比老師高出一大截。夏目的長篇小說《我是貓》于1905年問世。《我是貓》連載期間,他將中篇小說《趣味的遺傳》一揮而就。此作迄未譯成中文。據《近代日本文學翻譯書目》(國際文化會館圖書室編,講談社1979年版)第184頁,《趣味的遺傳》曾于1973年由伊藤愛子、格雷姆·威爾遜合譯成英文,刊載于《日本季刊》上;1974年又將這篇譯文與《琴音幻聽》、《夢十夜》二篇的英譯合成一個集子,由京都的塔特爾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關于《趣味的遺傳》,伊藤整在“解說”中寫道,它“作為寫實小說比較完善……反映了現實”。小說的背景是日俄戰爭。乃木希典率領導的第三軍在1904年8月至12月的“旅順戰役”中,經過多次爭奪戰,以傷亡五萬九千人的代價,迫使俄守軍投降,1905年2月在水師營簽約。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簽訂了“和約”。
這場戰爭的戰場主要是在中國領土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作者對這些毫不關心。小說中的“我”像是作者的化身,兩耳不聞天下事,這一天也是偶然來到火車站的。然而,看到從戰場上凱旋的將軍又黑又瘦,他的心靈被震撼了。盡管沒像狂熱的群眾那樣喊萬歲,他卻真誠地淌下兩滴淚。這淚,表達了他的“忠君愛國”思想。要想了解夏目漱石,不可不讀《趣味的遺傳》。
《將軍》脫稿于1921年12月。文中的N閣下影射乃木(Nogi)希典。日本的《文藝春秋》雜志2004年6月號上曾刊載了文藝評論家、慶應大學教授福田和也的《“百年詢問”——乃木是名將還是愚將》一文,對乃木的“人海戰術”以及“個人魅力”予以全面肯定。一百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在戰爭狂熱席卷全國的七十五年前敢于挖苦被奉為“軍神”的乃木,是需要勇氣的。這篇一萬七千五百字的小說,有二十來處被檢察官開了天窗,達一百余字。戰后也未能恢復。譯文依校畫葫蘆,用XX來表示被刪除的字。
乃木的“個人魅力”,使夏目漱石筆下的“我”淌下淚水,芥川卻在《將軍》中借用一個美國人的評價,說乃木的“眼睛里,有著近似于Monomania(偏執狂)的特征”。
從斬死兩個中國人的下面這段描述中,鮮明地看得出作者的立場。
“‘是俄國間諜呀。將軍的眼睛里倏然掠過了偏執狂式的光芒,‘斬掉!斬掉!”
“騎兵當即揮動大刀,一下子朝那個年輕的中國人頭上砍去。只見那個中國人的腦袋翻滾著……”
“很好!干得不錯!”
“將軍一面喜形于色地點著頭,一面驅趕著馬兒走遠了。”
“騎兵目送著將軍離開之后,又提著沾滿鮮血的大刀,站到了另一個中國人身后。他的一舉一動給人一種感覺,似乎比將軍更喜好殺戳。”
下面再看看芥川筆下的中國人的形象:“那兩個中國人不約而同地回頭望著他,但臉上并沒有流露出半點驚慌的表情……就像是已經豁出去了一般,那兩個人大義凜然地向前伸出了脖子……留著胡子的中國人卻只是默默地伸出腦袋,連眼睫毛也沒有動彈一下……”作者顯然是站在被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一邊的。
《將軍》的末尾耐人尋味。明治天皇于1912年病逝,乃木在為其舉行葬禮的當天,與妻子一道殉死。此舉產生了轟動效應,家家都掛起了他的遺像。1918年10月一個傍晚,乃木手下的參謀中村,發覺掛在客廳里的乃木肖像畫被兒子撤換掉了。在大學讀書的兒子解釋說,乃木在自殺之前竟特地把攝影師請到家里來拍標準相,他不以為然。原來乃木不僅有偏執狂的傾向,還老謀深算,連殉死后的光環都考慮到了。
芥川所寫關于關東大地震的文章也被當局開了天窗。那是第五節,芥川和菊池寬聊閑。芥川說:“大火的原因是XXXX。”被菊池寬駁斥了。接著又說:“據聞,XXXX是布爾什維克的走卒。”也遭到菊池寬的怒斥。眾所周知,自大震災發生的9月1日傍晚,就流傳起朝鮮人要掀起暴動的謠言,日本警察和軍隊趁機殘殺三千多名朝鮮人。日本革命家河合義虎、大杉榮、伊藤野枝等也遇害。被刪掉的文字肯定與這個大環境有關。
1910年5月,日本發生了所謂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當時的政府為了鎮壓工人運動和社會進步力量,就捏造了“陰謀暗殺天皇”的罪名,逮捕了日本平民運動領袖、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處以死刑。這下子起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夏目漱石在《我是貓》、《哥兒》、《三四郎》、《礦工》、《其后》等早期作品中對社會進行了批判,這幾部小說寫于1905年至1909年之間。大逆事件之后,1910年至1916年間問世的《門》、《過了秋分為止》、《行人》、《心》、《道草》、《明暗》等,則用個人內心世界的剖析取代了社會批判。永井荷風曾寫過《冷笑》(1900)等作品,嘲罵明治社會的庸俗丑惡。1919年,他在《焰火》一文中回顧了大逆事件對他的影響:“我既然是個文學家,就不應該對這個思想問題保持沉默……可是我和社會上的文學家都一言不發。”最后,他跟菊池寬一樣,變成了通俗小說家。
芥川龍之介至死不改初衷,忠于藝術。關于他的自殺,西鄉信綱認為:“在日益猖狂的日本法西斯和同它進行的階級斗爭劇烈起來的處境下,小市民知識分子注定要感到本身的軟弱無力,芥川在這條路上走到了盡頭。”現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會長高慧勤在前言中稱譽芥川的“最佳作品……即便列世界短篇名家之間,也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