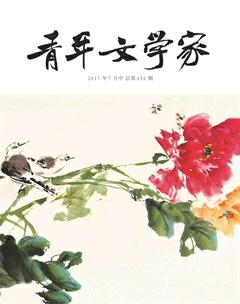中國小說中的父權與父愛
劉緒君
摘 要:父與子的關系描寫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小說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父親這個角色在中國封建歷史文化中屬于權威的象征,代表著一種權利,也是封建社會秩序的主要矛盾關系之一。當然,父權與父愛總是交織在一起的,有社會化的父權,就有自然化的父愛,這種血緣家庭關系紐帶是不可替代的。基于此,本文從父權與父愛的不同視角探析了中國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關鍵詞:父親形象;父權;父愛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01
總體來看,父親形象會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不斷演變。父親嚴格來說屬于社會化的范疇,在家庭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在經歷了封建禮教思想的洗禮后,父親形象不可避免地會呈現出獨斷專橫的父權特征。
1、獨斷專橫的父權與隱藏含蓄的父愛
關于至高無上的父權描寫在許多小說中都有所呈現,例如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關于賈政、賈赦等父親形象的描寫可以說是對中國封建禮教獨斷專橫父權的最好演繹。當然在描寫父權的同時,中國小說中也不乏對父愛的演繹。盡管在多數小說文學作品中,關于父親形象主要以權威為基本特點,但是,即便是在牢固和穩定的封建社會關系,也不能割舍父親對子女的愛。只不過,中國小說對于父愛的描寫大都是采用隱藏含蓄的方式呈現,不像父權那樣描寫的直截了當。例如西周生在《醒世姻緣傳》中既塑造了一個傳統父權意識的父親形象,又隱含著對父愛的認同。盡管薛父不可能超脫封建禮教衛道士的身份,但在這種封建社會化的父權背后隱藏著深深的父愛。再如吳趼人在《恨海》中也描寫了對子仁愛的慈父形象,作為父親的陳啟遵循儒家理念,悉心教導孩子,展現出一幅“父慈子孝”的溫馨畫面。同時,在家庭危難之際能夠堅決地保護妻兒,這些都閃現著父愛的光芒。因此,中國小說對于父親形象的描寫集中體現為對至高無上父權的披露,但在父權框架下隱藏著清晰的父愛。
2、父親形象的批判、解構與重構
文學作品是對一定歷史時期社會關系的展現。中國長期處于一種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級秩序中,封建禮教思想映射在家庭組織關系中,就是父親有著絕對的統治力。所以,中國小說中對于父權的諷刺性批判顯露無遺。父權的獨斷專行,成為封建禮教的一把牢固的枷鎖,年青一代尋求獨立自由必然需要與傳統權威的父權進行抗爭。并且,中國小說中對于父權基本上都是單向的批判。例如巴金的《家》中的高老太爺,就被描寫中一個封建暴君,父權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包辦子女婚姻,掌控子女事業,強制安排子女命運,可以說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了子女身上,象征著封建父權對子女追求自由的束縛,也是對專斷父權的深刻批判,表達出作者反抗封建父權的思想情感。
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小說對于父權的批判越來越強烈,開始解構傳統封建禮教下的父權形象,這既帶有文學色彩,又帶有政治色彩,象征著封建禮教下逐漸腐朽的父權開始走向下坡路,中國小說開始展現子女對父權的審視和反抗,新文化思潮開始推動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革。例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蔣捷三,是一個傳統封建父權意識依然很濃重的父親,他獨攬大權,肆意支配子女命運,最終與兒子蔣少祖發生沖突,并且兒子的離家出走也反映出子女開始敢于對父權做出反叛。可以說,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小說對于父權的批判一度上升到頂峰,張愛玲更是塑造了精神殘缺、身體殘障的父親形象,將父親描寫成自私無比、冷酷無能的符號。而余華的小說對于父親形象給予特別的關注,通過損父、無父、尋父等一系列創作來對父權進行了解構,尤其是在《在細雨中呼喊》中將孫廣才描寫成一個丟失道義、禽獸不如的父親形象,徹底解構了高高在上的父權,并把父愛也拉下了圣壇。蘇童筆下的《南方的墮落》、《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罌粟之家》等小說作品也徹底打破了父親形象,父權與父愛被顛覆,長期以來的封建父權制度開始分崩離析,在此基礎上新型父子關系開始重建。例如余華在后期創作的《許三觀賣血記》,通過描寫父愛的責任重構溫情的父親形象。再如秦文君的《男生賈里》開始塑造父權與父愛相對平衡狀態的父親形象,體現了新時期民族平等的父子關系。
3、結語
中國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大都是有一定的社會文化根源可追溯的。而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孝道”衍生而成的家庭組織關系中,父權與父愛相互交織,獨斷專橫的父權與隱藏含蓄的父愛自然成為中國小說中的經典主題之一。
參考文獻:
[1]中國本土職場小說中的父權制意識色彩[J]. 閆寒英.求索 . 2011 (07):65-66.
[2]跨越世紀困惑的“父親”想像——試論后新時期三種父親形象的書寫[J]. 賀玉瓊,程麗蓉.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04):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