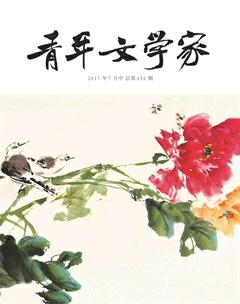從“打工春晚”看“新工人”文化的自覺
摘 要:“打工春晚”是由民間組織“工友之家”即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主創,以打工者為主體,而為天下的勞動者創辦的一種文化活動形式。不同于主流中央春晚的大制作,他沒有華麗的舞臺,也沒有家喻戶曉的明星,“打工春晚”以他獨特的節目內容與形式深切表達著打工者們自己對于社會的切身思考和對文化的渴求。打工者摒棄以往所謂主流文化強加給他們的稱呼“農民工”,而自稱“新工人”。新工人們自發組成團體,主動申訴自己的文化需求。新工人們以這種方式打破了以往傳統主流文化一統天下的格局,一種新的文化時代局面正要到來。它的影響在舞臺之上,更在舞臺之外。
關鍵詞:打工春晚;新工人;文化自覺;階級意識
作者簡介:尹咪(1992-),女,漢族,湖北鄂州人,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2
一、“打工春晚”——打工者文化訴求的舞臺
“打工春晚”是迄今為止中國電視歷史上唯一一臺由基層勞動者自編、自導、自演的春節聯歡晚會。“打工春晚”總策劃孫恒說:“選拔節目有三個標準,演員必須是一線工人、節目必須是原創、必須真實反映工人群體的現實生活。”而且2015“打工春晚”的總導演許多也認為:“節目不是才藝展示,要反映工人的真實生活。主流春晚關于農民工的節目不能真實反映農民工的生活,我認為優秀的文藝作品來源于生活,真實才能打動人,所以打工春晚的節目要接地氣,盡可能還原工人們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實表現工人們的生活,這在這些為打工者服務的群體里已經成為一種共同意識。而“打工春晚”的總策劃孫恒、總導演許多及眾多“打工春晚”的表演者等都是“北京工友之家”這家公益性團體的工友。這家公益性團體在成立之初便旨在為打工群體服務。
而“打工春晚”這個想法也只在2012年春節前兩個月才被提出來,盡管沒有華麗的服裝、周全的設備,也沒有大牌云集的明星、璀璨的舞臺,這次晚會匆忙而簡陋,但參加這次春晚的工友及群眾依然興高采烈。“打工者春晚”的聲音雖然有點粗糙,他們在舞臺上的動作還有些生硬,面對觀眾還有點局促忸怩,但這些節目來自機床轟鳴的車間、鋼筋水泥腳手架,在他們工作的角角落落,是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他們期待用這樣的方式向社會展現他們的藝術夢想,也傳達他們內心文化訴求的聲音。“打工春晚”,這一種與大地默契合拍的藝術心跳,與打工者訴求心心相通的“工人標準”,同樣是一種藝術精粹。
二、“新工人”——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
與打工者們強烈的文化訴求相對應的是,打工者們開始以“新工人”自居。與“農民工”這樣的消極被動的稱呼不同的是,打工者們意識到自己作為社會主體而存在的一面,他們開始正視自己內心的對于文化層面的精神追求,他們作為文化主體的意識開始覺醒。而發生這一轉變的原因有三點:
(一)“農民工”一詞首先與農民這一文化類型的負面內涵有關。而“新工人”之前,這一團體也經歷過幾個不同的稱呼時期。“新工人”這一群體是伴隨著改革開放與全面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中國現存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雙重作用下,農村居民自發向城鎮流動的歷史進程的產物。[1]在其最初,是被稱作“盲流”的存在,“盲流”即盲目流動,可見這一稱謂所內含的極具歧視性的意味。而對于進入城鎮的農民而言,他們已經被貼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賤民”的標簽,這是城鎮居民對他們的一種的歧視與排斥。其他還有一些相關詞匯在特定的情形下也用來指稱農民工群體,例如,民工潮、外來工、打工妹和打工仔,等等。所有這些稱呼都無一例外地帶有一定的文化偏見,將農民工群體描述為被排斥者、外來者或入侵者。
(二)現實原因——“新工人”不再純粹為生存而打工。以“新工人”自居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們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打工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對土地缺乏真正的依賴。汪暉說:“對于新的打工者而言,農村的家越來越趨于一個回不去的符號,城市已經成為他們的真正的歸宿。”[2]不滿于現狀的“文藝青年”,想要通過藝術逃離庸碌的日常生活,帶著成名的想象,從家鄉啟程前往首都,成為北漂,因此有學者指出,“他們對個人發展和自由有著更多的追求,工作變換更為頻繁,對工作的忠誠度不如上一代”。[3]而不僅僅是只為生存迷失在都市里的農村打工者。
(三)新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覺醒。在汪暉先生那里,新工人既不能被稱為農民工,“‘農民工概念是一個從城市身份,尤其是從城市消費者的角度對新來者的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打工群體的成員構成的變化,對于新打工者而言,農村的家越來越趨于一個回不去的符號,城市已經成為他們的真正的歸宿。”[3]也不能稱之為工人階級,只能稱之為新工人或新工人群體。一方面因為與階級緊密相關的集體的概念在新工人這里已經消失殆盡。“工人群體的客觀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性的工人階級已經存在”“它不是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范疇……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但是,在當代沿海的大工業生產中,無論是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還是與城市社會形成隔離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車間之間往返的生存狀態,工人群體間的人與人的相互關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工人階級的斗爭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新工人的斗爭卻還停留在維權階段,一種個人化目的階段。因此在汪暉這里,新工人只能成為新工人。
而在筆者看來正是由于新工人階級意識的產生才讓他們區別于“農民工”。自改革開放以后,工業化的進程在許多方面改變了中國大多數傳統農民的生活,讓他們離開一直以來賴以生存的土地去未知的城市務工。與傳統的“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土地的依賴性大大降低,他們基本上已是半個城市人。由于工業化、全球化這一社會變遷帶來的機遇,這一群體能夠發揮自身的能動性,主動積極地掌握學習的機會,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生存技能,主動地把控住他們在“市場”中的位置。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和集體應承擔的責任被轉嫁到個體身上,讓個體被迫以單個人的力量去解決系統問題”[4]。而恰是這一原因,這一群體擁有的經濟資本增多,他們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已經不同于他們父輩,他們開始主動地覺醒自身的階級主體意識。
三、“打工春晚”的后續——新工人文化的自覺
就“打工春晚”而言,在2012年首屆晚會普遍引起各方關注以后,其規模越辦越大,舞臺的擴大,經費也因此而增加,就連一些家喻戶曉的明星也都通過自己的方式給予“打工春晚”關注。但是與首屆晚會好評一邊倒的情況不同,更多觀眾開始質疑,“打工春晚”如何才能不變味?在經過3屆的探索后,2015年的“打工春晚”回歸它的“初衷”。這種有意識地引導文化發展甚至可以稱之為“文化的自覺”。更甚者這個新工人集體以他們微弱卻確實業已產生的階級主體意識來引導這種文化上的自覺。
新工人們自發組織成團體,創辦自己的博物館,抒寫自己的詩歌,創作自己的歌曲,他們用自己所能夠觸碰到的文學、文化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文化訴求,他們拒絕帶有歧視性的稱呼“農民工”,堅持稱自己為“新工人”,這是他們對自己所屬階層的一份歸屬感與認同感。他們不滿所謂主流媒體文化對農民工形象的遮蔽、丑化和貶低,[5]他們也不需要那些虛偽的同情與刻意的人文關懷。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關于社會的話語模式,在自己的能力范圍下,他們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踏實地工作生活,完善自身形象,以改變社會的偏見,來確確實實地創造出一個適合廣大勞動者生存的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1]湯達琦.從春晚三十年看“新工人”稱謂的變遷[J].美與時代(城市版),2015(11).
[2]汪暉.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J].開放時代(專題:公民社會VS人民社會),2014(6).
[3]盧暉臨,潘毅.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J].社會,2014(4).
[4][波蘭]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M].歐陽景根,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
[5]黃平.“中國故事”的講法—以2011年春晚為例[J].天涯,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