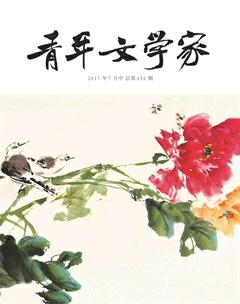淺析雍正《寧波府志》的文獻學價值
張沁
摘 要:本文通過對雍正年間修訂的《寧波府志》的梳理,分析該地方志對寧波本地文人的生平以及各方來客在寧波府期間從事的文學活動的記錄,將他們的個人創作、總結編修作品、石碑篆刻以及描寫寧波當地風物的作品盡數納入,分門別類,為研究文人們的創作生平以及寧波府文化底蘊提供參考資料。
關鍵詞:寧波府志;文獻價值;查漏補遺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2
雍正《寧波府志》(下簡稱《寧波府志》),為當時寧波知府曹秉仁等人所修,萬徑等人纂。筆者所用版本系據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刻本影印。
全書共三十六卷,首一卷。內容詳實豐富、門類清晰,具有極高的文獻參考價值。
一、人物志對文學家的創作生涯進行總結和補充
《寧波府志》以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共三卷篇幅以縣為單位羅列歷朝歷代人物,又別開名宦、名臣、忠節、孝義、文苑、特行、隱逸等卷列舉個中翹楚。筆者僅舉其中較為知名人物為例。
唐代虞世南。錄于卷二十一慈溪人物志。《寧波府志》中記敘其由陳入唐的仕途經歷,形容其“生平篤于孝友”,“容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議論持正,遇事敢言,剛直之性,老而彌篤”[1],多次直諫唐太宗,卒后得太宗稱贊“世南對朕忠心一體,拾遺補闕,無日暫忘”。方志有別于傳記,篇幅所限,然以寥寥數百字敘述虞世南生平,并描摹其人品性,已屬難得。
唐代賀知章。錄于卷二十鄞縣人物志。《府志》形容其為“性放曠,善談笑,賢達”,“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工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世傳以為寶”[1]。此節盡顯方志考證的特質。在普遍認知中,賀知章為今杭州蕭山人,而雍正《寧波府志》將其列入寧波府人物。考據理由如下:“按知章據唐書越州永興人,永興今蕭山縣,故舊通志列紹興隱逸傳,但鄞南鄉有山名響巖,地名高尚,傳為知章故里,相沿已久,又近代《廣輿記》等書,亦載寧人物中。當非無據,今仍之。”[1]雖難免有難免有攀附名人之嫌,但賀知章晚年自號四明狂客,應也不失考證之據。在研究賀知章其人、其作品之時,亦為一種參考。
宋代史浩。錄于卷二十鄞縣人物志。《府志》著重突出了他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成就,甚至詳細闡述了他的身后事,卻忽略了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大約其身份過于顯赫,以至于文學才能在有限篇幅內被選擇性省略了。
二、藝文志中對有關寧波府的文學活動的系統總結
編者于藝文志前自述編纂藝文志的初衷。言“志之有藝文也,蓋史家之遺,而有與史異者,史列諸書之目而已,志則郡中大營建之作,于夫學士大夫紀載舊聞敷陳,民瘼登臨山水之詩若文皆所不遺。蓋有足以備考稽資法戒者,固不容聽之煙云過眼也,寧自任闞諸虞……顧百年來散亡磨滅或僅存其目而是編所載反有出于舊志之外者,其亦是邦文獻所關,母寧過而存之也歟。”[1]大意是立志將史書、舊志之外關于寧波府的文獻盡數搜羅收錄其中,其初衷大約就可以“查漏補遺”四字概括。
1、藝文志上:目次
該部分以朝代劃分,囊括各類作品。
(1)私人著作
如宋周邦彥《清真集》。
(2)編注舊有著作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寧波府志》對王應麟作品的總結。上文已經提及王應麟被收錄在本書的名臣志中,足見編者較為認可的是王應麟作為官員的成就。但本書并未忽略王應麟作為一個考證大家的成就,列舉其多達二十余種,六百多卷的著作:“《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六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鑒地理考》一百卷、《通鑒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鑒答問》四卷、《困學記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解踐祥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四卷、《詞學指南》六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1]其中最出色的是王應麟私撰的《玉海》二百四卷。分天文、地理、官制等二十一門類,除卻類書作用,對目錄學亦是貢獻非凡。這樣豐富的著作或可解釋南宋遺民王應麟入元后二十年“空白”的人生。但在王應麟的諸多作品中,并未提及《三字經》,因而王應麟是否《三字經》作者,猶待考證。
(3)編纂的方志及類書等
如明代張時徹《寧波府志急就方書》。
(4)除文學外的其他類目書籍亦有記錄
如明代醫學家王綸的《學庸要旨》、《草本集要》、《名醫雜注》等著作。
其中大部分作品今尚存,小部分作品雖亡佚,然能存其目,亦能算得一種亡羊補牢吧。
2、藝文志中:雜文、藝文志下:詩詞
這部分收錄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寧波府籍的文人作品,而是將所有與寧波府有關的作品都保留下來。其中不乏蜚聲文壇者,諸如陸云、柳宗元、陸龜蒙、司馬光、范仲淹、陸游等人都有關于寧波府風土人情的作品被載入。
(1)王安石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中記載:“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寧波府志》藝文志中保留了王安石的三篇文章,四首詩作,應是慶歷六年至慶歷王安石任鄞縣知縣時所作。
據宋書,王安石在鄞縣任上的主要政績是興修水利。王安石在《鄞縣經游記》中就曾寫到他視察工程的經歷。“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1]
而從王安石自己的作品觀之,他似乎對自己擴辦學堂一事更有心得。
在《慈溪建學記》中王安石闡述了自己的教育觀。開篇他就肯定了政教的重要性,他認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而政教的目的在于為天下取士。“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后能者也。”[1]同時,王安石的教育觀是極其務實的。他揭露了天下尊孔,卻將學孔變得僵化的現狀——“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于天下……當此之時,學稍稍立于天下矣,猶曰縣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于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他指出教育應應時而變,單單尊崇孔子而不立學,實屬無用。另外,文中還表現了王安石的擇師觀。雖然他在前文中指出“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于位而去者,以為之師”,但在慈溪這種特殊情況下,王安石選擇了當地學者杜醇來擔任學堂的夫子。他在《請杜淳先生入縣學書》中寫道:“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馀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愿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1]王安石言辭懇切,請求杜醇先生來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重擔,足見其尊師重道。在杜醇先生去世之后,王安石還作《挽慈溪杜醇先生》(亦收錄于藝文志中)緬懷,此為后話。在《慈溪建學記》中王安石也解釋了選擇杜醇的原因:“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于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1]除卻杜醇本人的品德才學,王安石選擇杜醇還因為他是受本地的風俗浸潤的,他的思想和方式更適合本地的學生,也就回歸了王安石最初為國家儲備官員的想法——讓這些學生成為治理當地的官員。另一方面,王安石也發現了教育潛移默化的長遠作用。“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后至于善。”
時年王安石尚不到而立之年,已經具有這樣長遠的目光,與他未來成為頗有作為的政治家顯然是密不可分的。《慈溪建學記》是王安石在慈溪孔廟留下的碑文,不僅是一篇抒發作者政見和思想的優秀文章,能夠作為研究其文學成就與未來政治行為的參考,也見證了他在慈溪知縣任上對慈溪當地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2)蘇軾
《寧波方志》中收錄其文一篇(《宸奎閣碑》),詩兩首(《送馮判官之昌國》、《月湖十洲倡和詩》),蘇軾年譜中未見其曾于寧波府任職,應是知杭州期間所作。
(3)黃宗羲
相較于前兩位,黃宗羲與寧波府的淵源要更深一點。黃宗羲是紹興府余姚縣人氏,按現今的行政區劃來看屬于寧波大市范圍。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黃宗羲于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并在此期間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著作。其中,《四明山志》是他的作品中唯一一本具有方志性質的著作,也是圍繞四明山的唯一一本方志,足見黃宗羲對其熟悉程度之高。
黃宗羲有兩篇文章收錄于《寧波府志》藝文志中。《海市賦》寫的是黃宗羲在達蓬山游玩時巧遇海市盛景的所見所嘆,瞬息變化躍然紙上,是一篇出色的寫景文章。《四明山九題考》則是建立在作者對四明山非常熟悉的基礎上,文章以“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倡和》,分為九題,后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于此是,顧四明山非九題可得盡……”[1]總領,簡單敘述了作者對四明山的考證,“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于二百八十峰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體現他嚴謹考證的態度。本文應是《四明山志》完成后的心得總結。
另外,黃宗羲是天一閣第一位外姓入閣者,曾作《天一閣藏書記》,發出了“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的感嘆。
三、天一閣沿革
天一閣是我國最早的私人藏書樓,于古典文獻意義非凡。“天一閣遺存的典籍中,以明代地方志保存得最為完好。”[2]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天一閣,那么筆者所研究的雍正《寧波府志》的內容將會貧瘠許多。
《寧波府志》古跡卷中寫道:“明兵部侍郎范欽宅之東偏左,瞰月湖,為浙東藏書家第一。舊有張時徹、豐坊二記。康熙巳未元孫廷輔請于姚江黃宗羲,復為之記。”[1]
在范欽的個人條目中記載道:“……爵升兵部右侍郎,遂歸家居建祖祠,置祀產、恤親、族訓、宗學,聚書于天一閣,至書萬卷。”展現了天一閣在雛形時期的規模。
而其子孫后輩范光文、范光遇等人的條目中僅側重于政績,而并沒有著筆于他們代代相傳的私人藏書家身份。在古跡卷中提及的黃宗羲為天一閣做記一事,應發生于范光文首次破格帶外姓人(即黃宗羲)入閣時期,方志亦無記載。另張時徹、豐坊、黃宗羲三人所作之記并未收錄在藝文志中,不得不說是一大疏漏。故而雍正《寧波府志》在體現天一閣文化底蘊方面尚有欠缺,實為遺憾。
總體而言,雍正《寧波府志》內容詳實,門類清晰,對研究作家作品、創作背景以及文學活動等都有的很高的參考價值。雖有不足,也算是瑕不掩瑜。
參考文獻:
[1]上海書店出版社編輯部. 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卷[M]. 第一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2]陳寧雄 .天一閣對中國藏書文化的貢獻[J]. 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