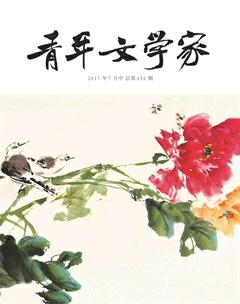淺析西歐中世紀早期社會結構的發展狀況
摘 要:自日耳曼各部落進入西歐以來,不僅給原有的羅馬社會造成沖擊,更帶來了蠻族的社會文化。隨著西歐早期的社會發展,至查理大帝時期,國家封建統治的確立,社會結構也逐漸穩定清晰。本文旨在通過三個描寫法蘭克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史料為節點,來探析自日耳曼人軍事民主制時期到克洛維建立墨洛溫王朝,再至查理大帝時期社會結構的發展狀況。
關鍵詞:西歐;中世紀;社會結構
作者簡介:李梓榕(1993-),女,漢族,山東淄博市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紀。
[中圖分類號]:K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1
公元5世紀末,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舊的強盛文明逐漸衰落,拉開了中世紀早期的序幕。各個蠻族的入侵不僅帶來了戰爭,更給6、7世紀的西歐造成了政治、經濟社會混亂的嚴重影響,但與此同時,隨墨洛溫統一法蘭克各部落,日耳曼與羅馬的漸次融合,在此后的500年中,新的“歐洲”文明漸漸形成,至查理大帝時期,隨著國家封建統治的確立,社會結構也逐漸穩定清晰。
一、日耳曼部族的早期軍事民主制時期
在塔西佗敘寫《日耳曼尼亞志》之前,日耳曼人早已渡過萊茵河,進入到被凱撒征服的高盧省,塔西佗則描寫了日耳曼人社會發展的較高階段。在日耳曼尼亞志的第七條中,塔西佗詳盡的描寫了此時的日耳曼人社會,此時的日耳曼部落中已經有了按照出身選舉通常是貴族出身的國王、擁有一定權利的酋帥或首領、權力大于軍事首領的祭司,祭司在生活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神圣地位,說明此時的日耳曼人還處在較為原始的軍事民主制階段。
此時,日耳曼人社會分化的過程已經開始。在平等的自由氏族成員中間出現了氏族顯貴和奴隸。在和平時期,日耳曼人按照他們自己的習俗,各人自愿將自己的牛群或谷物的一部分獻給貴族。俘虜通常都變為奴隸。此階段,部落中社會階層的劃分不是按照財富的多寡,而更看重出身的高低。
隨著與羅馬人日益頻繁的貿易交換和發展,內部階級分化也不斷增長。氏族貴族掌握很多地產和大量的牲畜, 并且利用奴隸勞動,在部落中得到越來越大的權力,掌握了氏族部落的領導權。最重要的是,每個部落中屬于領導地位的人在他們周圍聚集了由戰士組成的“扈從”作為突擊隊,他們跨越了親屬部族團體的界限,構成了持久的階級劃分的核心,并將原始社會中的強制性權力制度強化了。
二、羅馬與日耳曼社會因素的不斷融合時期
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曾經在日耳曼人日常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的軍陣就是按照家庭和血緣關系編排起來的,他們用這種將生死榮譽托付給最為可靠的人的方法來激勵士氣。而到了克洛維時期,氏族制已趨于解體。
在薩利克法典中,為避免血親復仇的矛盾激化,而確立的賠償金制度可以明顯地看出此時法蘭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國王和貴族是上層,法典中規定殺死一個伯爵應被罰款600先令;處于中層的是有人身自由的法蘭克人,他們也是法蘭克社會生產的主要承擔者,償命金是200先令;羅馬人的償命金為自由人的半數,只有100金幣,半自由人的地位更低,償命金是自由人的一半,他們的地位在自由人與奴隸之間。
在這個新的社會形態中,隸農在法律上的自由逐漸減弱,而從屬性越來越強;貴族的獨立性也不復存在。另一方面,法蘭克人原有的“自由”也因為農業生產方式被束縛在馬爾克共同體中,日耳曼人原有的親屬關系以及以軍事目的建立的扈從關系,被以土地為紐帶維系的從屬關系所取代。
三、查理大帝的社會穩定時期
建國之初,墨洛溫王朝的創建者克洛維按照“戰利品共同分配”和“公開贈送禮物”的傳統,把王國的土地分贈給他的親兵們,土地成了他們的世襲財產和私人領地,他們也因此成為最早的地主貴族。至查理·馬特時期,為了給王權建立強大的軍事支持,查理馬特進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實行采邑制,這種方式把無條件分配土地改為以服騎兵役為條件的“封授土地”,也因此塑造了封臣這個新的、以服兵役為基礎的貴族群體。
隨著法蘭克封建化的日益擴展,在騎士階級崛起的同時,教會貴族這一階層也逐漸成長穩固,成為法蘭克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早期,克洛維就把皈依基督教作為建立法蘭克王國,征服羅馬人的一項重要政治措施。751年查理·馬特的兒子丕平得到教皇的支持,建立了加洛林王朝,開始了政權與教權的最初聯盟。在查理大帝時期,其在位期間所實施的一系列教會政策,推動了法蘭克的進一步封建化。事實上,基督教會和基督教的教士在法蘭克實現封建化、完善封建制度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成為封建統治集團的重要機構和成員。至此,新的教俗貴族和世俗貴族共同構成法蘭克社會的統治階層。
四、結語
在日耳曼早期軍事民主制階段,社會階層主要分為部落首領、祭司、貴族、自由氏族成員和奴隸。隨著克洛維統一法蘭克各部,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度逐漸解體,法蘭克人與羅馬貴族等階層逐漸融合,社會形成了以法蘭克自由人,羅馬自由人,半自由人和奴隸為主的階層。至查理·馬特實行采邑制改革,騎士階層逐漸崛起,成為貴族和平民階層的中間力量。隨著基督教的不斷封建化,在查理大帝時期,分化出的教士貴族成為與世俗貴族并行的,新的統治集團的一員。隨著法蘭克國家封建統治的進一步確立,社會結構也逐漸穩定,“三位說”明確起來,而這三種階層,正是在法蘭克國家的不斷發展中逐漸成長,我們也都可以從早期日耳曼人的社會結構中追本溯源。
參考文獻:
[1]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M].郭方、劉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古羅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M].馬雍、傅正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3]王亞平.試析中世紀早期西歐采邑制形成的社會基礎[J].經濟社會史評論,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