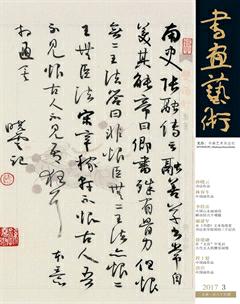徐渭另類書風及成因探析
曹雪鈺
摘要:徐渭書法作品類型多樣,風格各異。通過對徐渭思想形成、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及創(chuàng)作心態(tài)、創(chuàng)作方式的研究,分析導致其另類書法風格的原因。 關鍵詞:徐渭;書風;三教合一;刑具;平和
一
以嘉靖元年為上限,以李贄逝世為下限,王門講學活動最為活躍時期,前后大致歷時80年,恰好覆蓋了徐渭生活的時間段。徐渭在其《畸譜》中列出“師類”首先包括王畿,其后依次為蕭鳴鳳、季本、錢楩和唐順之。王畿、季本二人皆為王陽明高足,身后弟子眾多;蕭鳴鳳是徐渭的表姐夫,實際往來關系并不多;錢楩,與王畿和玉芝禪師交往密切,后來也出人季本門下;唐順之,因季本、王畿而結識徐渭,后在“本色”論中對徐渭有所啟發(fā)。
徐渭“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繼而又慕于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于禪”。經研究發(fā)現(xiàn),尚在而立之年的徐渭在思想體系上就已經是“三教臺一”了,他借助心學、禪宗、老莊的視窗看到個體存在和自然人性,從而更新“理欲”觀、“情理”觀、“義利”觀、“群己”觀。從嘉靖三十八年《十六夕詩草書軸》開始,頻見徐渭書法作品中落款為“天池道人”“天池居士”“天池山人”及“青藤道士”等,由此可看出禪宗及老莊思想對他的直接影響。另外,五位老師中四位都研習陽明心學,所以使得其思想及文學藝術作品中無不充斥著三教體系下狂放不羈的反叛精神和對自我肯定的真情流露。
萬歷元年除夕,剛剛結束7年牢獄生活的徐渭,在三月與友人游歷時創(chuàng)作了《天瓦庵等四首四體卷》。打開此卷,撲面而來的是黃庭堅書風,細看之下發(fā)現(xiàn)挺拔爽暢的點線舞動和黃庭堅長搶大戟般的開張結體相融合后,卻也形成了徐渭獨特的個人風貌。此卷從章法上來看,全卷安排較為緊密,字字侵讓;字勢左右擺動,幾乎每行都不同程度地偏離中軸線。結體上,徐渭在黃字的基礎上將字的欹側感加強,收緊中宮的同時拉長了撇捺,在字的相互呼應下相得益彰。徐渭之結字吸收黃山谷精妙后,參人己意,較之黃字變化更多,格局也相應恢宏許多。用筆上,若言黃山谷為沉著痛快,那么徐渭此卷則是痛快卻不見沉著,卷中線條多細勁,起筆收筆處皆多尖銳,感覺在撇捺及豎畫中輕佻而未留住筆。同時卷中撇捺及豎畫的拉長增加了靈動感,橫畫及捺畫的收筆也突出個性,多為水平方向快速拖出,很多時候的捺畫在快速拖出時因下一字的起筆而會帶出右下方走勢的弧度,如此特征是在徐渭諸多書作中最為明顯的一幅。而且運筆過程中又多提按,筆畫跳蕩明顯,這種用筆方式多顯出徐渭的癲狂狀態(tài),也明顯感受到他出獄后心情的釋放。“我與鼠爭食,盡日長苦饑”類似囚牢中的凄慘遭遇在此時充分地宣泄,似乎根本就不愿去理會作品創(chuàng)作中的線條與形式,只是其真性情的抒發(fā)。
最顯徐渭狂放風格的作品要數《代應制詠劍詞草書軸》《代應制詠墨詞草書軸》《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草書軸》這3軸。前兩件行草軸不管從作品形制上還是風格上都極為相似,整體布局在字距、行距上均繁密,以狂草的氣勢表現(xiàn)行草書的手法,顯示出其書法風格的高度一致性。兩軸最為吸引人之焦點處即是筆力雄渾奔放,不同墨色的線條曲折縈繞,結體因勢成型,全然不作字際、行際留白的安排,揮灑迅疾,但筆筆到位,一種狂風驟雨的氣勢躍然紙上。用筆中大量使用提按頓挫的動作,尤其是在刻意拉長的筆畫中,一筆之中的頓挫感十分明顯,很容易感受到筆力的存在,例如“斗”“旰”“年”和“冠”等字。并且筆畫中增加了線條的曲折起伏,這些動作的運動幅度較大,富有跳躍感,給整幅作品增添了靈動的氣息。在結字上,主要取扁勢,還有如“冶”“巧”等左右結構的字,左右間距拉大再加上“斗”“都”之類的豎畫被拉長,從而在極其茂密的章法中,看到了特有的律動感。總之,此二軸很好地表現(xiàn)出了徐渭真率恣意又頹放不羈的濃烈個人色彩,并且以獨特的章法形式、空間布局開創(chuàng)了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突破了傳統(tǒng)形式美的規(guī)范。正如袁宏道聽說:“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落不平之氣,字畫間宛然可見,意甚駭之!”自此,無人不被這種暴風驟雨,渾然整體又氣勢磅礴的恢弘大作所折服。
《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草書軸》也延續(xù)以上兩幅應制之作的整體風格,全幅章法茂密,搭配用墨的濃重和枯筆形成的飛白,造成強烈的節(jié)奏感,沖破漢字字形的局限,成為徐渭立軸書法的特色,同時也造就了徐渭狂放書風的一大特色。
二
然而在徐渭諸多恣意狂放的書法作品中,另有一些面貌迥異的作品存在,這些作品究竟有著什么樣的獨特之處,出現(xiàn)這些異處的原因又是哪些呢?
先來看一下徐渭為數不多的小楷作品《初進白鹿表小楷冊》,全文19行,共計289個字,按明奏表的形式呈現(xiàn),可大致從中窺出明臺閣體的影響。由于初入幕府,一貫個性張揚的徐渭倍感壓抑,給皇帝的奏表更是謹小慎敞,全篇章法工整,結字趨扁,字形和筆法中明顯可見鐘繇、二王之影響,也偶有筆畫初露倪瓚之端倪。對比徐渭其他書法作品,這個小楷冊雖感到拘謹,但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徐渭一生中難得一見的精彩之作。
拿徐渭10年后的《致禮部明公小楷札》與此相比,從理論上來說,10年后的作品無論是從結字上還是筆法上理應要比前者更精到,但是真正映人讀者眼簾的卻不免讓人稍感失望:首先,同為小楷書信類,《致禮部明公小楷札》從章法上來說,后半段明顯存在行距上下寬窄不一的現(xiàn)象,可以看出作者力求將每行字平行書寫,但是最后效果不佳;從單字上看,很多字欹側的情況比較嚴重,由一些筆畫也可看出作者盡力將字安排于臺理行距內,這更使得每個字的擺放都有呆板之感,整幅字的氣息也欠貫通。其次,《致禮部明公小楷札》的行距和字距都過于松散,筆畫稚拙,較前者稍感瘦弱,缺少很多作者個性狂放的一面,全文看來更像是出自文弱書生之手。此文是徐渭在獄中時寫給吏部侍郎諸大綬的感謝信,按照粱一成、李德仁及劉正成的說法都是寫于隆慶元年,所以本文認為此札應為徐渭初戴刑具時所寫。
徐渭獄中所作文章或書信中均有提到“余在繄”“時尚繄”“時予尚繄”等,而對于刑具使用則強調:“抱桔寄長吟”“所對著(共下面加手)桎絏諸械”“桎(共下面加手)之所”等。另外,《前破械賦》《后破械賦》分別寫到:“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鸛喙不啄,琴體乏弦。乃偕二友,木竇金紐,與之未三,脰及足手。”由此可知,徐渭提到的“二木一金”可能是脖預上重有三十多斤的桔或枷,和兩手又同時為鐵(共下面加手)所困,如此可知《致禮部明公小楷札》之所以呈現(xiàn)出諸多有違常態(tài)之處,皆是因為徐渭在獄中佩戴死囚刑具,而尚未習慣書寫所致。后至隆慶三年《奉答馮宗師書》中:“至(共下面加手)(兩手同械也)之所,涉筆為艱,遽不盡展。”即使仍舊艱難書寫,但兩種刑具重量的懸殊已經使得徐渭產生了“昨日何重,今日何輕”的感慨,自比化為蝴蝶的莊生在同時期和以后的作品書寫中已能較好地把握書寫技巧。
另外于獄中所作的行楷一類還包括《干字文行楷卷》,此卷與前兩者相比風格就鮮明許多。內容雖是為童蒙識字所用,但在除渭寫來卻如涓涓細流般娓娓道來,整體氣息平和,布白均勻,偶有行距緊密處卻也未顯出局促之感;結字較之前的扁方變?yōu)殚L方,疏朗的字體使得壓抑感消失,姿態(tài)變化較多,用筆也顯輕松、隨意,脫離了寫奏表和書信時的拘謹;線條流暢,但見捺畫和彎鉤折角處頓筆稍顯遲滯,在整體看來卻也無造作之感。文章開始處,作者尚為工整楷書,十行左右后便連貫筆畫成行楷之態(tài)勢,再到文章后三分之一,漸人行楷之佳境,結尾自作跋處已然為小行書。如此輕松暢達之行楷卷在筆者看來,概為兩手同械后期所作。
三
萬歷十七年年初,徐渭因醉酒而摔傷手臂,此年秋后又因病致雙耳失聰,孤苦伶仃的他早已沒有了早年龍性難馴的狂縱,唯有病痛與其做,半。“予嘗傷事廢餐,贏眩致跌,有臂骨脫突肩臼,昨冬涉夏,復病唧軟,必杖而后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賦,羨令威而不偕,橫榻哀吟”。而且“絕不飲食者十九日,頃方粥食,強起移步,扶杖可至中堂,欲過門而門限也”。但是即使是這樣的身體狀況,也不能阻止他書寫的欲望,“今試書奉別等五六字,便手戰(zhàn)不能,……其后草者則渭強筆,殊不似往日甚。”“一日自作小楷千余,腕幾脫,遂感昔日之勞”。自此,徐渭身體狀況用他在萬歷十八年時所寫的詩句來說是“可憐獨剩滄溟氣”。然而他在狀態(tài)稍好時仍醉心于書畫創(chuàng)作,《杜甫秋興八首詩行草冊》《歐陽修晝錦堂記行楷軸》及《煎茶七類卷》等幾件作品都是在這幾年中創(chuàng)作完成的,雖然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但是此時與世無爭的徐渭已真正步入了其書畫藝術的人書俱老期。就連平日里的書畫創(chuàng)作也凸顯他自娛自樂的輕松心態(tài),“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涂花卉……葫蘆依樣不勝揩,能如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裁”。懷著這種心態(tài)所作的書畫作品明顯已將中年的奇崛恣肆扔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恰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五月蓮花》一圖,是清雅淡薄的氣息,灑脫豐富的文人情趣。
《杜甫秋興八首詩行草冊》是徐渭71歲時抄錄杜甫55歲左右所作的《秋興八首》。徐渭對杜甫一直都抱有仲慕之情,“讀書臥龍山之巔,每于風雨晦暝時,輒呼杜甫……為錄其詩三首,見吾兩人之遇,異世同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杜甫秋興八首詩行草冊》從整體來說,氣息沒有中期作品的緊張厚重,反而多了很多舒緩的文人氣質,雖然結字依然欹側多變,點畫不羈。冊頁中結字大小參差,錯落有致,無法之法凸顯瀟灑適意。此作作為徐渭晚年的浪漫之作,讓讀者從心靈深處感受到了他的才華與心緒,也由此成為了晚年的代表作品之一。
《歐陽修晝錦堂記行楷軸》作于徐渭72歲時,長約6尺,全文共512個字,這樣一幅巨制與其行草書相比應算是異類之作,此書作采用有行無列之章法,工整嚴謹,結字略扁,筆法多參己意,而又依稀可見鐘王、倪瓚筆法,呈現(xiàn)出祥和沉靜、與世無爭而又姿媚溢出的整體面貌,這類書風卻是在徐渭早中期的作品中難覓蹤影的。因為徐渭晚年時與世無爭的心態(tài)正好符合小行楷一類的書寫心境,而且他當時體弱多病的身體狀況也是一個客觀制約條件。所以極有書寫欲望的徐渭這時期寫行楷的數量是多于之前任何階段的,而此階段的這些客觀條件也促使除渭留下了諸多區(qū)別于狂風驟雨、氣勢磅礴的行草書作品,讓我們看到了其晚年淡薄平和心態(tài)下的本色之作,而這些作品也將另類的徐渭展現(xiàn)給了人們。
在晚明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徐渭一生經歷了諸多曲折和磨難,這造就了他特立獨行的書法風格,在這其中的一些書風嬗變又與他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創(chuàng)作心態(tài)等的多重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他的幾種書風雖面貌各異,但真實反映出了徐渭因人生境遇不同而形成的特定心態(tài)及精神風貌。所以徐渭的書法是以天才為資,以性靈為宗,以橫放絕出、氣如風雨,或以偶想妙得、天趣盎然為勝,風格復雜多樣且不自我程式化,但始終不失真我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