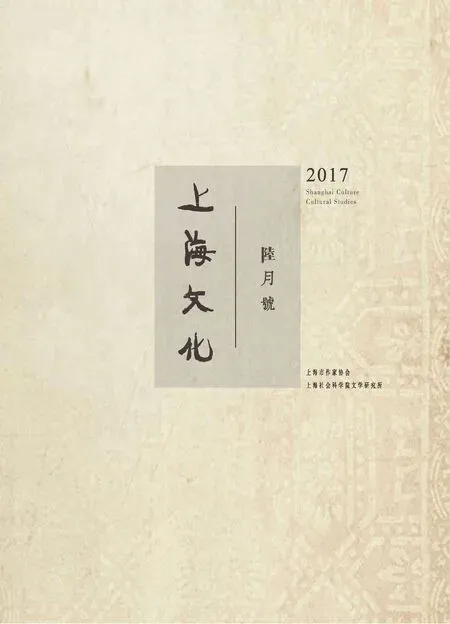筆墨與影像:上海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風格嬗變
——潘蘅生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研究
何振浩
筆墨與影像:上海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風格嬗變
——潘蘅生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研究
何振浩*
潘蘅生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家。他運用中國水墨和中國毛筆,結(jié)合西洋的明暗技法,借用影像效果來創(chuàng)作。其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別具一格,在中國現(xiàn)代連環(huán)畫藝術(shù)史上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本文介紹潘蘅生先生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和藝術(shù)特點,著重分析水墨語言結(jié)合影像效果的特殊技法及其反映的時代特點和審美傾向,指出以潘蘅生為代表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對后來的中國具象油畫的深遠影響。
連環(huán)畫 水墨 影像
潘蘅生,1949年生于上海,是中國著名的知青畫家,善畫連環(huán)畫和油畫。潘蘅生的父親潘德明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一位民國時期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當年騎自行車環(huán)游世界的壯舉,雖沒給后代留下萬貫錢財,卻留下了“丈夫壯志”的無價之寶,深深影響了潘蘅生。在潘蘅生小時候,離家不遠的嘉善路上,“福音堂”的斜對面有一家小書攤,花幾分錢可看一個下午。喜好繪畫的潘蘅生便立下雄心壯志:將來這小書攤上也會有一本我畫的小書。
1971年,他為北大荒作家鄭加真的長篇小說《江畔朝陽》畫了12幅插圖。從此,他在插畫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一發(fā)而不可收。從一個沒有上過藝術(shù)院校,甚至連少年宮興趣班都沒有參加過的純自學業(yè)余愛好者,畫成了專業(yè)美術(shù)創(chuàng)作者;從一個無名小輩畫成了著名藝術(shù)家。
1983年,已成為黑龍江省知名畫家的潘蘅生被調(diào)到省文化廳的戲劇工作室擔任美術(shù)編輯。這期間,他已成為為數(shù)不多的以水墨素描方式進行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畫家。他的水墨素描不僅造型嚴謹,而且人物神情生動、畫風扎實,別具一格。代表作是1984年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的連環(huán)畫《周游世界》,他用水墨畫的形式表現(xiàn)了50年前父親潘德明的那次震驚世界的環(huán)球之旅。專家認為,這252幅作品“造型嚴謹準確,表達流暢嫻熟,凝聚了畫家本人對旅行家父親的敬愛和懷念”。這部作品榮獲了“第六屆全國美展”銅獎和“第三屆全國連環(huán)畫評選”榮譽獎。
潘蘅生在繪畫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賦,油畫、水粉畫、素描、國畫皆擅長。寫實、抽象融會貫通;沒有進過專業(yè)美術(shù)院校,也沒有拜過師,卻憑著自己的努力和聰慧,不斷汲取古今中外名家大師的理念與技法,終于在藝術(shù)上有所成就。
人民體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連環(huán)畫《周游世界》是潘蘅生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的成名作,而幾年之后的《母親》,則被藝術(shù)家本人視為比《周游世界》更為出色的作品。這兩部代表了潘蘅生連環(huán)畫藝術(shù)最重要成就的作品體現(xiàn)了潘蘅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最大特點:影像真實性與筆墨手繪的藝術(shù)性的有機結(jié)合。在他的筆下,這種西洋水墨的特殊技法被運用得恰到好處,展現(xiàn)出他超強的寫實技巧與能力,以及高超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靈氣與活力。清晰準確完美的圖像敘事與豐富敏銳感性的藝術(shù)性相結(jié)合,這便是潘蘅生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的最大魅力,也引領(lǐng)著上海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風格的嬗變。把他的這種藝術(shù)特點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來關(guān)照,反映出中國藝術(shù)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發(fā)展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一種現(xiàn)實性和藝術(shù)性相結(jié)合的、順應當時時代潮流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興起,也是當時的集體審美方式轉(zhuǎn)變的體現(xiàn)。
一、20世紀70—80年代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的嬗變及其特殊歷史價值
新中國成立以后,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手法逐漸變得更加多樣化,傳統(tǒng)線描、傳統(tǒng)水墨、西洋素描、水彩水粉、黑白木刻等都得到了廣泛使用。連環(huán)畫的形象塑造上也開始大量借鑒西方的寫生手段,將人物和故事情境表現(xiàn)得更加充分與豐滿。連環(huán)畫這種繪畫藝術(shù)形式具有小中見大、形式多樣的特點(中外技法都可適用)。但是,連環(huán)畫由于兼帶很強的文學敘事性,必然需要以表現(xiàn)人物為主,且多帶有場景的補充。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要求下,擅長國畫的藝術(shù)家也需要具有更強的人物姿態(tài)表現(xiàn)能力,因此,在技法上出現(xiàn)了較為普遍的中西結(jié)合的線描或水墨表現(xiàn)方法。縱觀新中國成立前后的連環(huán)畫歷史,許多畫連環(huán)畫的高手,不論技法上用的是西洋的素描、水粉,還是中國的線描、國畫,都非常講究人物造型結(jié)構(gòu)比例的準確性與整體場景透視的合理性,可以說都是畫人畫景的熟手與高手。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文學腳本的豐富,各種世界名著和蘇聯(lián)文學作品有需求改編成連環(huán)畫作品;同時,在當時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運動高潮中,也需要一種有別與傳統(tǒng)國畫的新的現(xiàn)實主義美術(shù)樣式,來表現(xiàn)新中國大地上的各種新的運動和新的面貌。因此,運用西洋繪畫注重素描、結(jié)構(gòu)、透視的各種畫法以及經(jīng)過改良的國畫技法就被廣泛運用于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
潘蘅生畫中運用的就是一種具有影像效果和明暗關(guān)系的水墨連環(huán)畫技法。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偏向攝影或電影鏡頭感的、偏向西洋繪畫體系的連環(huán)畫畫法,有著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需求。首先,五四以后,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西方的文藝作品大量引進中國。在藝術(shù)上,也出現(xiàn)了第一批赴歐洲學習的藝術(shù)家,他們帶回了西洋的繪畫技巧、思想與藝術(shù)作品。這些前輩影響了后來的一大批藝術(shù)學子,特別是在上海,西洋畫法成為一種主流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方法。新中國成立以后,在連環(huán)畫出版市場上,很多作品的文學腳本本身就是西洋文學作品或是具有世界性交流意義的文藝作品,也自然需要運用西洋繪畫的表現(xiàn)技巧來創(chuàng)作作品。其次,“文革”后思想的逐步解放,人們想看到一些更新穎也更貼近現(xiàn)實的視覺藝術(shù)形式,而明暗對比是視覺藝術(shù)中最有沖擊力和感染力的對比方式,因此,講究明暗形體空間透視的西洋畫法的連環(huán)畫作品受到了讀者的普遍歡迎。再次,隨著大眾對當時僅有的幾種娛樂方式之一電影的迷戀,也使得這種帶有影像效果的西洋水墨技法繪制的連環(huán)畫受到讀者的喜愛和追捧。在看連環(huán)畫小人書時能獲得看電影一般的藝術(shù)享受,這在當時娛樂方式極少的群眾眼里也不失為一種美好的視覺享受。最后,作為藝術(shù)家本人,已經(jīng)擺脫了從前舊式連環(huán)畫作者為了賺錢拼命趕稿,大量程式化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而是要精心創(chuàng)作出獨具一格的、自己滿意而專家認可、讀者真正喜愛的連環(huán)畫作品。這樣的連環(huán)畫作品不光是為了大眾的一般消遣,更是一種視覺藝術(shù)的熏陶和精神的洗禮。
二、獨特的水墨技法
潘蘅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運用的是一種明暗關(guān)系的水墨連環(huán)畫技法,非常講究畫面整體的黑白對比與節(jié)奏感。在局部上要求形體關(guān)系的準確和人物動態(tài)的自然,還不能像其他連環(huán)畫技法那樣過多依賴模式化的造型和構(gòu)圖手段。在繪畫過程中要體現(xiàn)出更強的真實性,同時筆法上又不能畫得太死板太僵硬,而保持手繪過程中的生動和靈氣。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的動作、表情和整體的主次虛實關(guān)系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在這種運用西洋水墨技法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潘蘅生當然要依賴大量照片,但是他運用得很靈活,也獲得了許多利用照片資料創(chuàng)作作品的有益經(jīng)驗。首先,在他看來,沒有照片資料而完全靠想象,只能畫出很概念的形象,那對所表現(xiàn)的故事內(nèi)容來說就是簡單化的,不可能真正打動人。但是如果一張畫全部依賴照片,反而會不生動,沒有精彩的靈光乍現(xiàn)和創(chuàng)作的自由發(fā)揮。比如,一幅作品中需要十個不同的人物形象,手頭有六七張照片資料是最好的。剩下的人物形象便是在這種集體印象的揣摩體會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樣的創(chuàng)作效果最生動,又有基本的依據(jù)。有時候潘蘅生也經(jīng)常是幾張照片取長補短地參考,再加上自己的處理和想象,新穎的畫面就會應運而生。繪畫本身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當筆墨落紙的那一刻,會產(chǎn)生連繪畫者自己都無法想象的效果。畫面中的自由度也是藝術(shù)的重要部分,是藝術(shù)處理的很大的一塊空間。細看潘蘅生的許多作品,他特別善于把握人物的情緒和微妙的神態(tài),但是這種微妙絕不是依賴對素材照片的死磕摹寫,而是在這種他自創(chuàng)的西洋水墨技法中憑借扎實的寫實基本功,運用自己豐富的經(jīng)驗,并且結(jié)合和利用素材照片以及繪畫過程中的運筆和水漬的多種偶然性,細膩而傳神地拿捏到一個個精彩瞬間。

圖1 潘蘅生連環(huán)畫作品手繪稿,圖片由潘蘅生提供
當時大部分的連環(huán)畫在人物動態(tài)和神態(tài)表現(xiàn)方面,大多采用較為夸張的表現(xiàn)手法。而在潘蘅生的作品中,他對人物情緒的表達和劇情發(fā)展的控制有更高的要求,體現(xiàn)在具體作品中就是細膩和精準。在這樣的要求下創(chuàng)作的畫面恰恰使畫中的人物塑造顯得更為豐滿和真實,也更加具有藝術(shù)感染力。使讀者可以隨著畫面融入文學敘事中,并且感受到文本和畫面同時傳達的準確的情感與思想。對于這一點來說,在當時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很少有作品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潘蘅生之所以使用這種基于西洋繪畫寫實技法的水墨技法,是因為時代的背景和家庭原因。一方面,他父親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探險家、大旅行家,肯定多多少少有家庭言傳的影響和血脈性格的遺傳。另一方面,他雖然因為支邊的原因來到了東北,但是上海人的那種洋氣和向外探索的開放性眼光始終會對他的喜好和表現(xiàn)語言的選擇產(chǎn)生影響。
三、影像手法的時代特點及其魅力
影像在繪畫中的使用始于19世紀的歐洲,在當時的學院派繪畫及后來的印象派繪畫中都曾被利用。影像的介入拓展了人的視野,增加了很多表現(xiàn)對象的偶然性和瞬間性的視覺場面。同時也使畫面更有可能進入現(xiàn)實生活場景,去表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生活,表現(xiàn)當下發(fā)生的事件。可以說影像是最具現(xiàn)實意義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潘蘅生的父親潘德明在周游世界的過程中,就用隨身攜帶的相機記錄了一路上各個重要的歷史瞬間和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影像在旅行家手里是記錄歷史的最便捷最有力的工具。在潘蘅生眼里,利用影像來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也是一種最能還原歷史并且最能體現(xiàn)出他父親現(xiàn)代精神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
影像可以有全景,可以有特寫。影像往往在人們來不及用眼和腦記錄的時候,幫助復制眼前紛繁復雜的世界,同時也用片段化的方式呈現(xiàn)出多樣的視覺特征。因此,影像的魅力可以說是一種追求現(xiàn)代性的魅力,在當時看來是超越傳統(tǒng)的,帶著一種時尚感的新視覺形式。潘蘅生充分利用了影像的這種現(xiàn)代性,并且結(jié)合在他完美的水墨技巧中,使這種現(xiàn)代性的視覺模式又融合了藝術(shù)的多樣和豐富的效果,融入了一種內(nèi)心情感的細膩的表達。

圖2 潘蘅生連環(huán)畫作品手繪稿,圖片由潘蘅生提供
在《周游世界》中,潘蘅生使用了很多他父親旅行途中拍攝的照片。其中有與各國領(lǐng)導人和名人見面的重要時刻,也有許多沿途各地的風土人情。在具體表現(xiàn)中,他既要如實呈現(xiàn)那個歷史的瞬間,又要取恰當?shù)臉?gòu)圖角度來呈現(xiàn)畫面的藝術(shù)效果。這里有取舍與著重突出的藝術(shù)處理,也有在原有資料中融合相關(guān)內(nèi)容的組合處理。
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有電影蒙太奇的效果,因此,就如同剪輯一樣,需要在腳本中選取最能表現(xiàn)劇情的那一刻,并且用有限的畫面來講述故事情節(jié),表達情感。同時還需要使其后的內(nèi)容連貫。潘蘅生的連環(huán)畫作品很好地做到了前后畫面的統(tǒng)一連貫與畫面具體呈現(xiàn)的差異和節(jié)奏感。畫面構(gòu)圖有橫豎變換的搭配,甚至為表現(xiàn)特別的內(nèi)容更有畫中畫的特殊構(gòu)圖。潘蘅生自述在整體構(gòu)圖時他會把好多張畫稿一起貼在墻上,揣摩內(nèi)容的連貫性和構(gòu)圖的節(jié)奏起伏。在正稿的深入與調(diào)節(jié)中不斷完善這其中的整體韻味,以求觀眾和讀者在閱讀時保持視覺的新鮮和思維聯(lián)想的豐富和多樣。
四、筆墨與影像的完美結(jié)合
潘蘅生的連環(huán)畫作品善于運用影像般的畫面特征,看得出他也受到了經(jīng)典的蘇聯(lián)電影的影響。在那個時代,蘇聯(lián)電影可堪稱是那代人的精神美食。那代人對電影中的很多臺詞可以倒背如流,經(jīng)典的人物形象也必然深入人心。在潘蘅生的作品中有很多張采用了電影特寫式的畫面,而這樣的畫面勢必需要更為精準的人物表情的刻畫,也需要作品前后人物形象的統(tǒng)一。這對寫實功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在《母親》這套連環(huán)畫里,潘蘅生更是花了功夫,他也自認為比畫《周游世界》時精彩老道了許多。筆墨的控制更精準,細節(jié)與整體都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很多精彩的細節(jié)表現(xiàn)堪稱是畫面中的神筆。現(xiàn)實題材連環(huán)畫的真實性具有生活的真實、細節(jié)的真實和形象的真實,這類連環(huán)畫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上具有歷史典型性與生活真實性相結(jié)合的審美特征。歷史題材連環(huán)畫的真實性要求具有尊重歷史、還原歷史和強調(diào)歷史的真實,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上具有典型歷史真實性的審美特征。而畫家要有能力去把握生活真實性與歷史真實性,并且通過適當?shù)乃囆g(shù)加工和藝術(shù)虛構(gòu),最終形成藝術(shù)真實性,感染讀者和觀眾。
為了畫好關(guān)于父親的《周游世界》,為了塑造不同畫面中不同角度的父親形象,他甚至親自做了一個父親的雕塑小頭像。小頭像完全是他自己參考著父親的多張照片手捏出來的。只是在頭發(fā)的整體處理上讓他的搞雕塑的同事修補了一下。有了這個小道具,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帶來了很多便利。在沒有更多的父親照片的情況下,他可以在燈光下反復擺弄這個小雕塑,找到特別適合的角度。對著這樣的雕塑寫生,比起畫有限的照片來說,當然要好畫很多,可以畫得更為從容與細致。這也是他長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中積累的竅門之一。
在追求真實的歷史感與真切的人物形象的同時,潘蘅生也非常重視連環(huán)畫藝術(shù)的繪畫感和藝術(shù)語言的趣味與魅力,水墨語言在寫實要求之下的感性發(fā)揮便是他所追求的藝術(shù)趣味。
水墨在光的白卡紙上的運筆,一方面會有水跡的出現(xiàn)。水跡如果掌控不好,必然使畫面顯得很花很碎。但是一旦熟悉并且掌控得當,這樣的水跡在需要時就可保留,甚至在關(guān)鍵造型處起到塊面轉(zhuǎn)折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可肆意涂抹揮灑,得到一種畫面的自然流動的效果,大大增強藝術(shù)性和手繪的韻律感。甚至水漬還能表現(xiàn)出墨的不同的顆粒感,作品的材質(zhì)豐富性也就呈現(xiàn)出來,使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在一種物質(zhì)感中顯影般地呈現(xiàn),有種物質(zhì)材料和影像幻覺對比的魅力。畫出一種虛實相生且具有強烈節(jié)奏感和韻律感的效果,這樣的效果是純粹的照片所無法比擬的,也是連環(huán)畫之所以成為藝術(shù)的一個關(guān)鍵特點。
歌德在《文學風格論》中說過,“藝術(shù)家要使作品達到驚人高度的真實,作品本身必須是可靠、有力且豐滿的”。①歌德:《文學風格論》,王元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潘蘅生連環(huán)畫作品中精彩且細膩的寫實表現(xiàn),能最直接地再現(xiàn)歷史的本來面貌,把觀眾引入那種真實的氛圍之中,讓人有種身臨其境的逼真和親切感。同時,水墨效果的適度渲染,水漬與墨跡的保留和運用,既突出了繪畫藝術(shù)的趣味和魅力,又是對主題敘事情節(jié)的氣氛和情境的烘托,更加強化了那種真實性引發(fā)的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情節(jié)的沖突和對比。因此,潘蘅生連環(huán)畫藝術(shù)中筆墨和影像的完美結(jié)合把“真實性”這一創(chuàng)作內(nèi)容的審美特征用藝術(shù)化的方式相得益彰地呈現(xiàn)了出來。
新時期連環(huán)畫對西方繪畫體系的研究與借鑒,彌補了早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中濫用模式化語言、造型簡單、空間感差、人物性格特征表現(xiàn)貧乏的弱點。連環(huán)畫在造型上有了顯著的提升,畫家追求“明暗對比”和“細節(jié)刻畫”,可以更完整、更深入地塑造形象與表現(xiàn)體積感,這也是新時期連環(huán)畫造型樣式上一個突出的審美轉(zhuǎn)變。同時,對人物組合和場景描寫的多樣化表現(xiàn)也鍛煉了創(chuàng)作者的場景控制能力。因此,當年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培養(yǎng)了一大批善于掌控大場面的油畫創(chuàng)作人才。
每一種藝術(shù)方式都可能給下一個藝術(shù)的流行打好基礎(chǔ)做好鋪墊:歷史上巴比松畫派給印象派的興起做好了思想和技法上的鋪墊,而印象派的發(fā)生又給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井噴式的發(fā)展開啟了大門。
方寸之間的筆墨幻化出具有影像般的歷史真實,同時又在造型和藝術(shù)效果方面留給觀眾以視覺的震撼和感染力。比起“文革”時期由繪制官方宣傳畫培養(yǎng)起來的畫家,這樣的細膩生動活潑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方式無疑是當時的一股清流,帶來了思想和藝術(shù)上更多的可能性和吸引力。這種連環(huán)畫不僅為中國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給中國的油畫的發(fā)展尤其是寫實油畫的發(fā)展積蓄了能量,注入了活力。在技法和造型能力上都提高了要求。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大批寫實繪畫高手的涌現(xiàn)以及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的產(chǎn)生,其背后都不約而同地有著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可見,小小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鍛煉和培養(yǎng)了新時期像潘蘅生一樣的中國繪畫的中堅力量。
如今,連環(huán)畫已然進入了博物館,進入了歷史懷舊和收藏的領(lǐng)域,但是它曾經(jīng)的輝煌必然影響了中國的畫壇。每一個藝術(shù)樣式的流行一定有它的歷史價值和歷史意義,進入歷史的優(yōu)秀的連環(huán)畫作品,也可以給我們現(xiàn)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思路帶來啟示和思考,在技法上給我們借鑒和養(yǎng)料。潘蘅生的連環(huán)畫藝術(shù)就是這樣的藝術(shù)財富。
責任編輯:李艷麗
*何振浩,男,1975年生,浙江海寧人。上海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油畫專業(y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繪畫理論與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