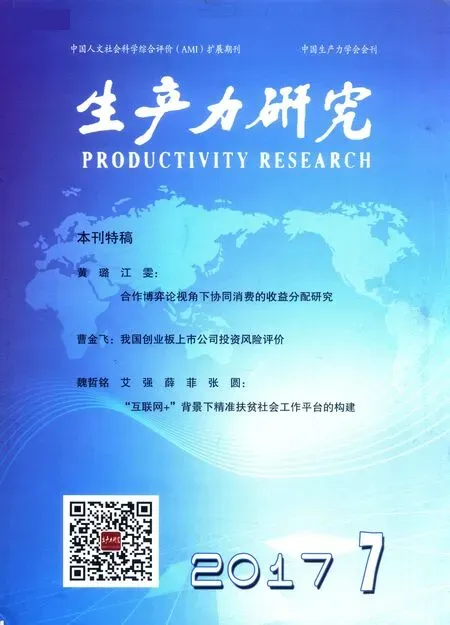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推進機制研究
喬 煜,李 琴
(蘭州理工大學 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推進機制研究
喬 煜,李 琴
(蘭州理工大學 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傳統的“輸血式”救濟型扶貧模式已不能發揮太大脫貧的效力,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扶貧模式向“造血式”的內源式扶貧轉換是西部民族地區扶貧工作的必然選擇。“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為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機制帶來了新機遇,西部民族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自身豐富的各種資源,重新審視政府在扶貧過程中的職能,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傳統,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推動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機制的構建,促進經濟、文化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
一、引言
隨著國家扶貧工作的推進,國家扶貧政策從剛開始的“輸血式”提供基本生存物質救助的救濟式扶貧,逐步向“造血式”的激勵貧困人口提高自身脫貧能力,增強自身創造能力,以人為中心的內源式扶貧方式轉換。
內源式發展模式是我國西部民族地區開展內源式扶貧機制的基礎和依靠。王維達教授認為,內源式發展不但要求要達到發展的目標,還要求不能異化發展,必須尊重和保護各國人民和各個民族的文化特征[1]。即內源式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其主要內涵是:發展是個人的解放,是人類的全面發展,是以自力更生為基礎,只能依靠社會內部力量來推動發展[2],它強調發展的內生性,人的積極主動性。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內源式發展必須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區的民族人文背景、歷史背景、生態環境基礎等方面,依靠西部民族地區的資源和少數民族群眾內部的力量,按照區域內人民群眾的需求制定發展計劃,并穩步向前發展。
內源式扶貧正是當前我國西部民族地區扶貧推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扶貧新方式。“一帶一路”戰略的施行為我國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工作的推進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一帶一路”的新機遇下,如何推進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的發展,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西部民族地區的扶貧現狀及致貧原因分析
(一)西部民族地區貧困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貧困治理的艱苦歷程中探索出分階段定目標的扶貧開發模式,扶貧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在一系列的扶貧開發活動后,明顯可以看出我國貧困分布發生了地域變性變化。“八五”時期(1990—1995年)全國農村的貧困特征是東部明顯改善、中部有所緩解、西部問題突出。西部地區的貧困問題得到了國家的重視,扶貧開發力度也逐漸增大。“九五”時期(1996—2000年),我國正處于扶貧開發的攻堅階段,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其惡劣的自然條件、薄弱的基礎設施和落后的社會發展等因素,貧困人口分布的地緣性特征明顯,貧困發生率逐步向中西部傾斜。西南大石山區、秦巴貧困山區、西北黃土高原區以及青藏高寒區等幾類地區是貧困人口分布的主要集中地。“十五”和“十一五”時期(2001—2010年)是我國扶貧開發的綜合發展階段,我國貧困的形勢和特征變化不斷。在貧困區域的分布上,貧困愈發向中西部地區集中,總體上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且這些地區的貧困是一種系統性的貧困,單一措施難以見效。“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2011—2020年)屬于集中連片扶貧開發階段,我國貧困的區域性分布愈發明顯,國家以“區域發展帶動扶貧開發,扶貧開發促進區域發展”為思想基礎,將新疆南疆三地州、西藏、四川藏區、滇桂黔石漠化區、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西邊境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14個區域劃為連片特困地區,將這些地區作為扶貧攻堅主戰場[3]。
從上述階段中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已成為我國扶貧開發的主戰場,而西部民族地區的貧困治理將是我國未來扶貧工作的中心和重心。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中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貧困人口總數量有5 575萬人,全國范圍內的貧困發生率為5.7%,而西部地區貧困發生率卻高達10.6%,將近全國貧困發生率的兩倍。2015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 966.2元,但根據按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顯示,西部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6 868.1元,不僅年增長速度緩慢,且明顯落后于全國及其他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見表1)[4]。

表1 全國居民按地區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單位:元
(二)西部民族地區致貧原因分析
1.地理位置偏僻且自然環境惡劣。我國西部地區處于我國邊疆地帶,西南地區河流縱橫,峽谷廣布,地貌以高原、山地和丘陵為主還有廣泛分布的喀斯特地貌、河谷地貌和盆地地貌等。地勢起伏大,海拔5 000 m~6 000 m的高峰眾多。氣候溫熱,年溫差小,雨量豐富,生物物種雖然資源豐富,但是或被破壞濫用或被開發利用,生態脆弱。且山林地區夏季時常暴發山洪、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地震也時常在我西部地區發生。西北地區地勢多見于高原、盆地和山地,且植被稀疏,山地、石質戈壁、荒漠、荒漠草地、高原草地面積廣闊,山麓綠洲較少,農業種植來相對落后于中部、東部等其他地區。西北的大多地區因其惡劣的環境,春季和冬季許多地方時常遭受沙塵暴的困擾,例如,臨近騰格爾沙漠的民勤縣土壤沙漠化嚴重,經常遭受沙塵暴侵襲。西部地區地形復雜、環境惡劣,交通不便,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導致其經濟發展緩慢,存在大量的貧困人口。雖然與西部地區接壤國家數量很多,但因國家政策的緣故缺乏與鄰國的互動交流。
2.少數民族在扶貧工作中缺乏積極主動性。我國西部邊疆地區生活著50多個少數民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匯聚在此,且每個民族的文化與風俗習慣各不相同。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不是從其內部自發產生的發展,而是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等外部力量的推助下,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發展經濟。正是由于內外發展的不協調,使得少數民族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在發展與自身民族文化、風俗的傳承的選擇中模棱兩可,最終造成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少數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技術與自然界的平衡關系被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打破,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自然進程因此中斷了。少數民族原有的、傳統的自然文化資源和社會發展水平不足以作為提升其生產力水平和資源利用能力的內生動力,最終導致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貧困狀況明顯[5]。且長期以來,國家對西部民族地區都是采取“輸血式”的救濟型扶貧模式,這種模式是一種單向的救濟模式,只需要國家單方的提供幫助,被救濟者則等待救援就可。這種單向模式使救助者產生了依賴,當地人民在扶貧過程中變得被動,喪失了積極參與脫貧致富的主動性,沒有積極的發揮自身能力去創造財富,主動改變自身貧困狀況。
3.國家開發政策的區域性差異。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一直把發展戰略的重心偏向東部沿海地區。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對外開放為我國基本國策后,我國的對外開放格局的逐漸形成,大致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創辦經濟特區,第二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第三步建立沿海經濟開放區;第四步開放內陸、沿江和沿邊城市。從對外開放的順序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先發展自然資源、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處于優勢的沿海地區,再逐步向處于劣勢的沿江和內陸地區遞進的發展模式,讓先富起來的沿海地區帶動內陸地區的發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是這種發展模式,使得西部地區的發展遠遠落后于我國其他地區,雖然近些年國家對西部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西部扶貧開發政策。但是由于長期的貧困積聚阻礙了西部地區自身的發展,加上西部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狀況等客觀因素,導致現階段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居多。可以看出東西部地區貧富差距已不是短時間內能跨越的,需要國家長期從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進行幫扶。
三、“一帶一路”戰略為西部民族地區扶貧推進帶來的發展機遇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途經我國新疆、甘肅、寧夏、西藏、青海、四川、廣西、云南、內蒙古等西部民族地區。這些省份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加之地理位置處于我國邊疆,自然環境惡劣,致使其交通不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雖然與我國西部地區接壤國家數量頗多,但因經濟水平、國家政策等原因,西部地區與鄰國的貿易交流并不通暢。內源式扶貧雖說要以人為自身的發展為中心,但絕對不是封閉的發展,它需要與外界的交流和互動,而“一帶一路”戰略的施行,為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1.“一帶一路”增強了我國西部地區與接壤鄰國的貿易、經濟、旅游、等往來。如,2015年的前5個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總額達到3 983.8億美元,占同期中國進出口額的25.8%[6]。“一帶一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為西部地區的人們提供了許多致富機遇,推進了西部民族地區的內源式發展。
2.“一帶一路”增加西部民族地區人民群眾就業機會。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西部邊疆地區的門戶,并與“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多個國家接壤,擁有三條開放的路線。一是向南連接印度、巴基斯坦、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二是向西通過亞歐大陸橋,連接中亞和歐洲;三是向北與俄羅斯、蒙古國接壤。這三條開放路線的開通把西部地區變成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增加邊疆地區與接壤鄰國的互動往來,尤其是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海洋運輸為主的對外貿易模式轉變為以陸路運輸為紐帶的模式,打破了我國長期以來的經貿模式,給西部民族地區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加強了我國內陸地區、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互動合作,將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資源要素會聚在此,并通過中西部大道直接對接國際市場。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往來中,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迅速增長,帶動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發展,增加了西部地區的就業機會,從而解決一部分西部地區失業群眾的就業問題。
3.“一帶一路”推動了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旅游業的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旅游要以當地民族文化為基礎,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在增強西部地區與沿線國家和國內的其地區的人文交流的同時,也幫助當地的人民群眾樹立了文化自信。民族文化旅游已成為西部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重點①根據相關網站數據顯示,2016年敦煌市全年累計接待旅游人數突破800萬人次,達801.52萬人次,同比增長21.37%。實現旅游收入78.36億元,同比增長22.89%。2016年西藏藏族自治區累計接待國內外游客2 315.94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14.8%;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2.19萬人次,同比增長10%,接待國內游客2283.75萬人次,同比增長14.9%。實現旅游外匯收入1.94億美元,同比增長10%;國內旅游收入318.8億元,同比增長17.6%。旅游總收入達到330.75億元,同比增長17.3%。2016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前三季度全疆共接待國內游客6 151.2萬人次,同比增長18.44%;國內旅游總消費908.32億元,同比增長20.03%;接待入境游客149.05萬人次,同比增長13.32%;入境旅游消費5.57億美元,同比增長21.09%。預計全年共接待海內外游客8 100萬人次、增長32.9%。海內外游客消費1 400億元人民幣、增長37%。,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正是吸引游客的亮點,游客為了體驗不同的風俗習慣,品嘗各式的民族風味小吃,領略壯闊的西北風光,紛紛到西部地區旅游。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當地的餐飲、住宿、手工藝等行業得到快速發展,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高,增加了當地居民的就業。同時,很多少數民族同胞的思想觀念隨之而改變,他們通過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內涵,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發家致富。因此,不會再有因民族文化與自身發展孰輕孰重而取舍困難的問題,從而緩解了西部民族地區的貧困狀況。
四、推進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機制創建的建議
經過幾十年的扶貧開發工作,西部地區的貧困雖已得到緩解,但傳統的扶貧方式不再能滿足現階段扶貧工作和貧困治理目標的需求,改進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扶貧開發的模式、創建扶貧新機制是我國當前扶貧工作的重心,內源式扶貧模式正是當前我國西部民族地區扶貧推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扶貧新方式。推進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新機制的創建應當做到:
(一)重新審視政府職能定位
政府在制定西部民族地區的扶貧政策過程中,應當明確政府制定的貧困幫扶政策,只是一種外在的動力[7]。政策只是幫助當地居民脫貧致富的輔助工具,不能決定貧困地區怎樣發展、往個方向發展,而是要根據西部民族地區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制定扶貧開發的發展目標。揚長避短,在發揮西部民族地區的長處的同時盡可能的改善西部民族地區的短板。此外,政府還應當幫助群眾自己了解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明白他們需要什么,能夠做什么,發揮他們的潛能,讓少數民族人民群眾主動參與到扶貧工作中來。要從他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出發制定幫扶方案,在扶貧工作進行的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全面發展。
(二)轉變貧困者的思想觀念
扶貧不僅是社會結構的改變,也是貧困人民思想狀況的轉變。西部民族地區的人民要想徹底擺脫貧困的首要之舉就是轉變自身關于貧困的傳統觀念,先從思想觀念上相信自身擁有戰勝貧困能力,再從實際行動中克服貧困。內源式扶貧就是要求以人自身的發展為中心,它要求貧困地區的人民應當意識到自己是扶貧工作中的主體,幫助他們深刻意識自己在扶貧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單純的救濟型扶貧是治標不治本的救濟方式,它只能在一定基礎和一定時間段上解決貧困的狀況,并不能從本質上根除貧困。一旦國家停止救助,將會有大批已經脫離貧困或即將脫離貧困的群眾重返貧困。因此,培養貧困群眾自身的致富能力尤其重要,擁有創造財富的能力,才能徹底擺脫貧困,走向富裕。西部民族地區的居民要想徹底擺脫貧困,就要認識到自身的能動作用,從思想上轉變對貧困的看法,相信自己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戰勝貧困,然后在國家政策幫扶的基礎上提升自身脫貧能力,通過自身努力消除貧困走向富裕。
(三)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傳統
每個社會和民族的發展類型和方式,都因本身的文化特性、思想和行動結構的不同形態,因此,文化是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內在源泉,豐富多姿的民族文化是西部民族地區最大特色。在推進內源式扶貧工作機制創建的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西部民族地區的民族特色,合理的將極具民族特色非風俗習慣、文化傳承運用到扶貧工作中來。首先應當讓西部民族地區群眾深刻意識民族風俗習慣是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一大優勢,教給當地民族同胞利用民族文化的技巧,充分發揚當地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在當地扶貧工作推進過程中的內生作用。政府在制定扶貧幫助政策實也應當尊重民族地區的文化傳統,因地制宜的制定扶貧方針和目標。發揮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積極性,讓他們積極主動參與到當地的扶貧事業中來。“一帶一路”的實施,也增加了邊疆地區與相鄰國家的文化互動,在多樣的文化互動過程中,形成了源于社會內部的發展動力,推動著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
(四)合理的利用扶貧專項資金
以往的扶貧資金主要通過各種補助以現金的方式分發給貧困群眾,但是資金在向下分發的過程中難免會因各種原因不斷減少,貧困群眾真正拿到手的補助十分有限。而且,單純的經濟上的補助并不能促進貧困者的致富積極性,還可能使其產生過度依賴,不利于扶貧工作的開展,所以需要轉變扶貧專項資金的發放方式,嚴格把控資金的流向。例如,西部有些地區采用扶貧貸款的方式對貧困者進行幫扶,在嚴格審查貧困者是否具備貸款資格后為其提供低利率長期限的貸款資金,鼓勵貧困者自主創業,發展勞動生產、畜牧養殖等產業。這樣不僅能增強貧困者的致富能力,幫助貧困者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當一個地區從事同一產業的農戶多了之后,可以在該地區形成某一特定產業的產業鏈,達到一定規模和知名度后,市場也會逐漸開闊,最終帶領當地群眾實現富裕。
(五)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區的文化與生態旅游資源
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資源是西部民族地區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寶藏。在生態旅游資源方面,西部民族地區不但幅員遼闊,而且資源豐富,氣候環境變化多樣且動植物種類繁多,自然景觀變幻多姿。據《中國風景名勝區事業發展公報》顯示,全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共225處,總面積約10.36萬平方公里。而西部地區現有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就有75個,是全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總數的33%,加上自然保護等其他旅游資源,還有尚未開發的旅游資源,可以說西部旅游資源相當豐富。在人文旅游資源方面,西部地區不僅是我國古代文明的發祥之地,而且是許多少數民族的宗教勝地,擁有神秘文化、雕繪藝術和傳統工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它們不但蘊含著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發展的見證,是人類文明的瑰寶[8]。而且,西部地區也是50多個少數民族發源和聚居的地區,50多個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動形成了西部地區最具特色、最具優勢的文化吸引力。富饒的自然生態資源為西部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旅游發展奠定了基礎,隨著歷史的變遷,多彩人文資源豐富了西部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之旅的內涵,西部地區的各級政府應當帶領當地群眾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加強當地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民族文化、民族節日、民族小吃吸引中外游客,帶動當地餐飲業、住宿業等服務行業的發展。
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和人文資源,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是幫助西部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重要途徑。這要求當地政府要制定適當的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政策,鄉級政府應該將上級政府的宏觀規劃融入到自己的建設中來,號召當地居民積極參與,聯合全鄉群眾的力量,統一的建設和發展當地的旅游業。在打造民族文化旅游景點的階段,可以雇傭當地的居民來參與基礎交通設施的建設,或者從事種植花草樹木、鋪地磚等零技術要求的勞動,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來源。之后帶領當地居民發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飲食和手工藝產業,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吸引游客,最終消除貧困,走向富裕。
五、結語
我國目前正處于集中連片扶貧開發階段,西部民族地區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將是我國扶貧工作的中心與重心,內源式發展扶貧模式也將會是未來西部民族地區扶貧工作應當重點發展的新模式。西部民族地區內源式扶貧機制的創建,不但需要政府轉變自身傳統的職能,在了解當地發展情況的基礎上制定正確且適合當地發展的扶助政策,還需要當地貧困群眾的主動參與和積極配合,還需要其他地區和其他人民對西部民族地區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尊重,更需要西部民族地區的人民合理的利用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
[1]王維達,1998.論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參與程序及其在中國的發展[J].中國行政管理(3):31-33.
[2]蔡小菊,向征,2010.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內源式發展模式的特殊內涵[J].大舞臺(11):243.
[3]劉牧.當代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戰略研究[D].吉林大學,2016:92-93.[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6.
[5]錢寧.文化建設與西部民族地區的內源發展[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1):39-40.
[6]新玉言,李克.崛起大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全剖析[M].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63.
[7]邱洪艷.論少數民族地區內源式發展——文化與少數民族發展[D].天津師范大學,2005:20-21.
[8]張小利,2007.西部地區旅游業發展的比較優勢悖論——基于東西部地區旅游收入效應的比較分析[J].財經科學(2):131-133.
(責任編輯:C 校對:R)
F124.7
A
1004-2768(2017)07-0107-05
2017-04-30
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義務與社會協同:社會權保障研究”(15XFX021);2016年甘肅省軟科學專項項目“甘肅省扶貧政策與農村低保制度融合對策研究”(1604ZCRA016)
喬煜(1975-),女,河南新野人,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法學基本理論與社會法學;李琴(1992-),女,四川眉山人,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