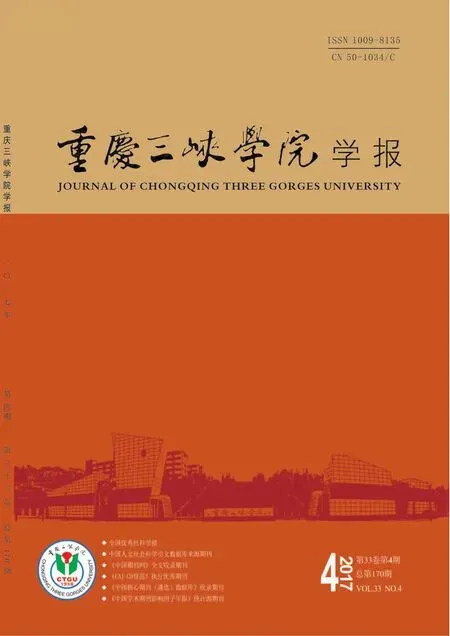易學對李白的主要影響
康懷遠
(重慶三峽學院,重慶 404020)
易學對李白的主要影響
康懷遠
(重慶三峽學院,重慶 404020)
易學對李白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若以“主要”而論,我認為應當包括“功成身退”的自我保護、“不事權貴”的傲岸性格和崇尚“白賁”的美學追求。
李白;周易;“功成身退”;“不事權貴”;“白賁”
“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其道就在于含蓄而廣大、深邃而精密,李白接受《周易》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涉及他的思想、詩風,也涉及他的生活道路和創作方法①關于易學對李白思想、詩風、生活道路和創作方法的影響筆者將專文論述,此文不贅。近年來筆者對李白與《周易》的研究論文主要有:(1)《李白明月意識的易學解讀》,發表于《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5期;(2)《李白讀易初證》,發表于《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6年1期;(3)《李白的易學人生觀》,發表于《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4期;(4)《易解李白芻議》,發表于《中國李白研究》2016年集(黃山書社2016年版)。,但若以“主要”而論,我認為應當包括“功成身退”的自我保護、“不事權貴”的傲岸性格和崇尚“白賁”的美學追求。借用法國作家法朗士在《樂園之花》中的話,如果把他所說的的“書”換成《周易》,那么易道恰好似“魔靈的手指”,撥動了李白的“腦纖維的琴弦和靈魂的音板,而激發出來的聲音”與詩人的心靈相關。
一、《周易》“利用安身”與李白“功成身退”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系辭下》)既是《周易》重要的哲學思想,也是《周易》回歸現實世界、關注現實生活的重要命題。《周易》宣稱“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辭上》),對人的身體的極盡推崇確乎成為西方實用主義者謂之“人類靈魂的最佳圖畫”[1]35及“浩瀚宇宙里所有結構中最美妙的”[2]252先聲。身體在《周易》中的絕頂地位不可小覷:“君子安其身而后動”(《系辭下》),“身安而家國可保”(同上),“君子以反身修德”(“蹇”卦,象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系辭下》),“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復”卦,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卦,卦辭),“藏器于身”(《系辭下》),“言出乎身”(《系辭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在李白的詩文中,身體的分量同樣不可等閑視之,并與功成相聯系,在人生存亡、安危、福禍、得失、取舍、屈伸和進退的選擇中表現出鮮明的個性風格,主要表現為:一是以立功為不朽,仰慕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等建功成名的人;二是時時抒發求功成而不得的惆悵和慨嘆:“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三是設想著功成后隱身而去歸山藏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并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行路難》其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風》其十八)。用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話來說就是:“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范蠡、張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而這恰與《周易》“利用安身”的哲學思想不無關聯。
考查“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句,原是《易傳》引用孔子的話來闡述《易經·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明從爾思”之義的。《周易》的核心功能是“利用安身”四個字,它講利,講趨吉避兇,但絕不主張為求安身而逢迎喪德,充當小聰明的角色。第一,“利用安身”的前提是“精義入神”;第二,“精義入神”方可有所作為;第三,“崇德”的物質利益是“安身”的生存或生活基礎。這就告訴我們,在義與利、身與德的選擇中,中國文化肯定人對物質利益正當追求的同時,強調人在滿足物質利益過程中把“義”與“德”的實現作為最高理想或最終目標,即“安身”是為了進一步修德進業。這是一種東方智慧,一種中國式的人生大智慧。“精義入神”作為一種高境界的哲學精神,其要義就將天理、地理、人理、物理諸理融合而成宇宙之理、萬物之理、人生之理。《周易》以樸素直觀、辯證的思維傳達出實用獲利和靜心養身的人生哲理。老子借以發揮為“功成身退”或“功遂身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嬌,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第九章)。
從《周易》“利用安身”到《老子》“功成身退”,人生的哲理就完全生活化、實際化了,人生的小宇宙與天地日月、萬千世界的大宇宙默契連通,使得中國式的根身文化在有修養的文化人身上一脈相傳,李白則為佼佼者:“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駕去溫泉后寄楊山人》),“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贈張相鎬二首》),“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功成拂衣去,歸于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贈韋秘書子春》)等詩句,不是詩人無由實現功成的牢騷與無奈,也不是仕途不遇的調皮與戲謔,而是出于自我保護的清醒與優選。
李白讀易,把“利用安身”結合為“功成身退”的智慧選擇,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高揚著生命的悲憫情調。李白生活的時代,且不說他年輕時熱烈擁抱的大唐社會天寶前后開始朝著下山的路走去,也不說他長安被讒賜金放還所負載的痛苦與悲憤,更不說他面對家國破敗、朝綱紊亂、生靈涂炭、豺狼冠纓的黑暗現實的呼天愴地,單就同代輔國之臣慘遭迫害的殘酷與血腥、不平與憤懣,都可能溝通了自己對人生追求的幾分保留與理智及其對生命目的的預測與判斷,因為“不考慮手段就表示不嚴肅對待目的”[1]282。《周易》以“占事知來”“遂知來物”(《周易·系辭》)的簡易之理所提供的手段,使李白保持了自我保護的警覺:“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同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
眾說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或理想主義詩人,其實,除此而外,李白也是很現實的詩人,很講實用的詩人[3]。詹锳先生說,“因為從李白的創作經歷看,他還是一個布衣詩人。詩仙李白終究不是‘仙人’,他也是人間的泛眾,是民間苦難過濾了的普通之人”(摘自楊振喜撰文回憶詹锳先生語)。實現生命的目的關鍵要看實效,一如杜威所言:“尋求認識上的確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動結果中求得安全。”[4]109《周易》倡導“變動以利言”(《系辭下》),在“乾”卦之初九講“潛龍勿用”,原因就是“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乾”卦,文言)。一切以實效為標準,合目的的實效行動就有大用,“吉兇者,貞勝者也”(《系辭下》),“爻也者,效此者也”(《系辭下》),“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同上),“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卦,象曰)等等,無一不是明言目的實效性的。李白從“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到“仰天大笑出門”(《南陵別兒童入京》)入長安,“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事君”目的是非常明確的,以至于飽受坎坷、屢遭挫折而“一朝復一朝,發白心不改”(《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因為他“長相思,在長安”(《長相思》),這是一種有耐心的執著,實用的目的浸透著李白的苦心經營。當然,苦心經營所付出的代價是他始料未及的,但那孜孜以求、“自強不息”(乾卦,象曰)的文化品格卻給后世留下了很寶貴的精神遺產。幾多清醒與優選,幾多保留與理智,造就了詩人特立獨行的人格形象。
二、《周易》“高尚其事”與李白“不事權貴”
《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說:“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辭釋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意思是,君子之德應當以“不事王侯”即不屈于王侯為高尚,其志向可以作為人們效法的榜樣。張岱年先生稱之為“保持人格的獨立”,“是最古的關于人格尊嚴的思想”[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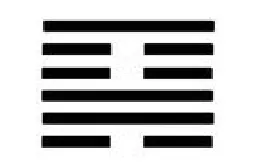
圖1 周易·蠱卦
關于《周易·蠱卦》的“蠱”,《序卦》曰:“蠱,事也”;《左傳?昭公元年》曰:“皿蟲為蠱,谷之飛者為蠱”;《雜卦》曰:“蠱則飭”。根據以上說法,一般認為蠱卦巽(風)下艮(山)上,以山下大風象征救弊治亂,整飭秩序,故而“元亨”。但是,要得亨通,一要“干父之蠱”,治理因鐵腕撥亂(父為陽為剛)所造成的歷史亂象;二要“干母之蠱”,治理因寬仁過度(母為陰為柔)所遺留的死角黑洞;三要糾正歷史弊端,即使產生失誤也要堅持;四要糾偏務盡,不留遺憾;五要贏得眾人的贊譽擁護;六要功成身退,超然物外,保持高潔志向。這就是六爻①“初六:干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九二:干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干父小有晦,無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干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爻辭的大概意思。而最關鍵的必須做到“君子以振民育德”(象曰),培育民眾美德,糾正時弊。蘇軾的解釋是:“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事,則后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為‘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為,下莫逆而上無為,則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偷,而衰亂之萌起矣”(《東坡易傳》第十八卦蠱)。東坡從社會政事的角度看蠱卦,是合乎易道的。至于上九,誠如余敦康所說,它(上九)“處于蠱之終極,此時整治蠱事已大功告成,可以抱一種超然的態度,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逍遙物外,潔身自守。這種高尚的志向合乎隨時進退之義,是值得人們效法的”[5]。
中國文化中的“功成身退”的思想淵源,不能不說與易道有關。李白生活的時代,他確乎無法擺脫“行路難,多歧路”“青蠅點玉”,“白雪寡調”“世人欲殺”的厄運,應當說他選擇“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而“五岳尋仙”不失為理智的高尚之志。“北闕青云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只是他功未成而身先退,諸多遺憾和不平總要撩撥起后世仰慕者的心弦。李白的尊嚴,就這樣一代又一代不斷地提升著。
所謂的人格尊嚴,乃是人之為人的內在潛質善的價值觀念和德性規范,在肯定自我中具有使他人敬重的品格。如儒家的“貴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殺身成仁”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浩然之氣”和“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的英勇精神,道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天人品性以及知止②老子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九章)、“知足”①老子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貪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又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崇儉②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六十七章)、棄智③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十八章)“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絕圣棄智,民利百倍”;(十九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五十八章)“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三章)、去欲④老子說:“無知無欲”;(三章)“虛其心,實其腹。”(三章)等生命追求。李白于儒、道當是兼而有之,在接受易道“不事王侯”的文化精神過程中表現出獨特的個性風格。
“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的李白,認為自己是“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巢父、許由,堯時隱士,是中國古代最為典型的“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的兩位頗有骨氣的高人。史載許由面對堯讓天下的誘惑不為所動,洗耳穎水以示拒絕,巢父聽了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而“牽犢上流飲之”只怕“污吾犢口”(《史記·伯夷列傳》和《史記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李白以巢由自許,正是他“不事王侯”操守人格尊嚴的自我宣達。
縱觀李白的人生和行事,詩人確有一種巢由情結,研讀《送岑徵君歸鳴皋山》(下文簡稱《送》)和《鳴皋歌送岑徵君》(下文簡稱《歌》)兩首詩即可看出。徴君,朝廷徵聘而不就的高士,從詩題“徴君”二字看出這位岑勛(郁賢皓考證,其人似與岑參為從兄弟)同樣屬于“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之人。《歌》詩自題曰:“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泠池作。”可知兩詩當同為“天寶三載(七四四)去朝以后游梁宋時所作”[6]845。
《送》詩借送岑徵君歸隱鳴皋山這件事,力贊被送者的聲望和才能堪比謝安,傷嘆其不為世所容而隱淪為客,但作為貴道之人能夠保全自然本性,韜光潛輝,探玄精深,觀察造化,游于無形,令人欽佩。詩人在征引嚴子陵不事光武帝歷史典故中,盡情傾吐自己平交帝王、不慕權貴的人格尊嚴,并對棄才妒能的社會現實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歌》詩屬騷體,詩人先寫岑徵君思歸鳴皋山而因積雪、河凍、山險受阻的煩悶心緒,繼寫以詩、酒、音樂為岑徵君餞行并想象其別后的隱居生活,再寫詩人的心緒繚亂、孤寂愁苦,最后寫詩人由激憤于懷而生棄世隱居之想,痛斥小人爭權奪利、賢者失所,朝廷真偽混淆、美丑顛倒,悲憤之情與屈原《離騷》和賈誼《吊屈原賦》異曲同心、靈犀相通。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十八評曰:“太白《鳴皋歌》雖本乎《騷》,而精彩絕出,自是太白手筆。”[6]854
聯系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骨氣和“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贈辛判官》)的傲氣以及“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疏媒勞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遭遇,他是把“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故實糅合為“不屈己,不干人”的人格追求,在“功成”與“身退”的艱難選擇中著實要去面對功未成而身欲退的痛苦與折磨。這種痛苦與折磨幾乎與詩人終生相伴如影之隨形。嚴酷的現實、坎坷的經歷、世態的炎涼、社會的危機、環境的險惡,整個地造就了李白“高尚其事”“不事權貴”的孤傲氣質和獨立人格形象[7]。
后世稱“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宋戴埴《鼠璞》上),腰長傲骨雖然不足憑信,“不能屈身”,卻也契合李白生性。
唐李肇《唐國史補》載:“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后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8]163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亦載:“李白名播海內,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9]644
《舊唐書·文苑列傳》又載:“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于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余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10]
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白》還載:“白浮游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狀不書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里,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長笑而去。”[11]93-94
以上四種帶有小說家的演繹,把“力士脫靴”和“貴妃研磨”戲劇般地寫進文壇掌故,也不是空穴來風,夸張是夸張了,然而倒也不離李白的生性之真,可視為“傲骨”說潤色性的描述。唐人任華說:“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醉。……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這應該是可信的。
除此之外,宋趙令畤《侯鯖錄》卷六記載:“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釣鰲客者,心胸廣大、抱負遠大、志氣宏大的非凡之人,后蜀何光遠《鑒誡錄·釣巨鰲》、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狂譎》已有載說①后蜀何光遠《鑒誡錄·釣巨鰲》:“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 張佑遂修刺謁之,詩題銜‘釣鰲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于言下挫之。及見佑,不候,從容及問曰:‘秀才既解釣鰲,以何物為竿?’佑對曰:‘用長虹為竿。’又問曰:‘以何物為鉤。’曰:‘以初月為鉤。’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為餌釣,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李白自稱釣鰲客者盡管查無實據,后世還是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何也?因為符合李白的個性氣質和行事做派,自然當之無愧。
《周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它以天地大理、陰陽之變、剛柔有致的深邃思維和智慧“推天道以明人事”,揭示出人在宏大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辭下》)。《周易》每卦六爻,上下各兩爻分別代表天地之道,中間兩爻代表人道。對人道的確立,開啟了中國文化人格尊嚴的先河。儒道兩家無不從中汲取精華,把人格尊嚴提升到理論化、系統化的高度。李白不事權貴,集儒道(當然還有其他如縱橫家、法家、兵家、農家等)于一身,融《周易》于靈魂,其“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生軌跡,用詩、酒、劍、仙、俠貫串起來,為中國詩壇增添了幾多亮麗的風景。
如詩,李白說:“屈原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功名富貴如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文章千古事,“立言”向被士人推崇為與“立功”“立德”的三不朽之一。他頌揚屈原辭賦,實為借杯澆壘,旨在表白在詩的王國里是不容有“功名富貴”的一席之地的,與其“不事權貴”人格尊嚴極其合拍。難怪郭沫若稱道:“那是詩與酒的聯合戰線,打敗了神仙丹液和富貴功名的凱歌。”(《李白與杜甫》)
如酒,“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杜甫《酒中八仙歌》),“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酒神所揮發的氣概在李白身上產生了沖決千古、驚天動地的力量。“酒膽海樣大,詩才天比高”(四川江油李白紀念館臧克家贊李白聯),此語道破李白作詩、愛酒的真諦。他愛酒不愧天地,“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飲美酒,登高臺,快哉“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因為在他看來,“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月下獨酌》)。酒興掃卻虛名,強化了李白的孤傲,扶正了李白的自尊。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狂譎》:“王嚴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
如劍,“百兵之君”的劍,與李白有不解之緣。《新唐書》本傳記載,李白“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其人生志向就是“欲將書劍許明時”(《別匡山》),足見劍寄托著詩人“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和抱負。他說:“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贈崔侍郎》),“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希望有朝一日,“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臨江王節士歌》),“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塞下曲六首(其一)》),能夠效命疆場,實現自我。在他的詩作中,“學劍”(《結客少年場行》:“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仗劍”(《上安州裴長史書》:“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佩劍”(《襄陽舊游贈馬少府巨》:“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撫劍”(《贈張相鎬三首(其二)》:“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彈劍”(《行路難(其二)》:“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裙王門不稱情”)、“拂劍”(《贈何七判官昌浩》:“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勛”)、“冠劍”(《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嚴陵》:“冠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橫劍”(《留別廣陵諸公》:“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脫劍”(《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拔劍”(《送羽林陶將軍》:“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出龍泉”)等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劍似乎可以威逼一切,凌厲之慨何其了得!
如仙,李白有“謫仙人”“酒仙”“詩仙”“醉圣”“仙風道骨”的稱號,仙、圣二字,活脫脫地展現了他飄逸于世、獨立不群、超越凡塵的精神風貌。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從李白的游仙詩中感悟出詩人“郁郁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的“怨”來,甚確。“高舉遠引”正是“不事王侯”的注腳。
如俠,李白足以當之。《新唐書》本傳說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魏顥說他“少任俠,曾手刃數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說他“袖中匕首劍,懷有茂陵書”(《贈李十二》),劉全白說他“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俊邁,往往興會屬詞……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范傳正說他“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宏大,聲聞于天”(《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這些都是李白任俠的真實記錄。至于詠俠一類詩的數量和質量可謂唐代之翹楚。
詩、酒、劍、仙、俠,是李白生命精神的重要元素,連同儒家的大丈夫志氣和浩然正氣及其道家宗法自然的無為秉性和不慕權勢的歸真質性,是他有尊嚴地生活在大唐社會的人格寄托和自尊化身。面對權貴,詩人不低眉、不折腰、不迎奉,其骨氣、骨格、骨性,在儒、道、詩、酒、劍、仙、俠的七位一體中熠熠生輝,令世人永銘不忘。儒之氣、道之心、詩之靈、酒之興、劍之鋒、仙之逸、俠之勇,在李白把它們凝聚于身的時候,便與“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易學思想最終玉成了自尊的李白,富有個性的李白,狂放傲然的李白,至大至剛的李白。如果套用清人龔自珍“莊騷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最錄李白集》)的話,那就是“儒、道、詩、酒、劍、仙、俠實七,不可以融,融之以為骨,也自白始也。”
三、《周易》“白賁”之白與李白之白
“六經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理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歷代作家和作品的沾溉更是舉足輕重、不可小覷。南朝劉勰所謂“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文心雕龍》),程頤所謂“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程氏易傳·易序》),就是從本質上肯定了《周易》的美學價值及其審美判斷。誠如宗白華先生指出:“《易經》是儒家經典,包含了寶貴的美學思想。《易經》的許多卦,也富有美學的啟發,對后來藝術發展的思想很有影響。”[12]458
《古風五十九首·其一》是李白的創作宣言。在這個宣言里,他深沉哀嘆西周以來雅正之聲日遠日衰、渺茫難覓,深情痛惜戰國之際所造成的詩壇荒蕪、荊榛叢生,深摯禮贊悲傷幽怨的屈原在汨羅江邊那震撼千古、激人肺腑的吟唱;在這個宣言里,他時而回眸大漢帝國時代揚雄、司馬相如沖擊頹波、激揚文典的開流之功,時而疾首梁、陳、隋代憲章淪喪、文風綺麗的頹靡之氣,時而心系三曹七子的建安風骨卻也無不流露悵然惋惜的遺憾之情。詩人表示,“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他要在大唐盛世,高舉復古風雅的大旗,讓文華與質樸妙合統一、相得益彰,如同繁星在明凈的秋夜閃爍,并決心效法孔子,像刪《詩經》、著《春秋》那樣,直到獲嘉瑞仁獸麒麟而罷筆,再現詩壇的風清骨正。才逸氣高、舍我其誰的自信和豪邁溢于言表。
其實,就文、質而言,《周易·賁卦》便是最可寶貴的濫觴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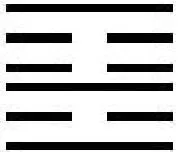
圖2 周易·賁卦
賁卦(如圖 2)由噬嗑卦發展而來,《序卦》說:“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說文解字》釋:“賁,飾也,從貝卉聲。”東漢鄭玄注:“變也,文飾之貌。”賁本為貝殼的光澤,引申為修飾、裝飾。說明此卦是專門探討文飾的。賁卦卦辭說:“亨。小利有攸往。”卦象為上艮下離;離為火,艮為山,象征山下有火。東晉王廙注:“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峰峻嶺,嶠崄參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火焰映照山崗,光彩艷麗,美輪美奐。卦辭意為事物要有必要的文飾,可以亨通,文飾之后,以顯其美。宋程頤注:“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進也。”(《伊川易傳》)意即此。賁卦彖辭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這樣的卦爻結構,形象地意味著賁卦剛爻與柔爻、文華與質樸相互交飾的緊密關系。賁卦彖辭又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天文、文明、人文、文化均有一“文”字,足見賁卦對文飾之美的重視。
再行觀察,離、艮相疊而成的賁卦,離之文明,艮之止,告訴我們,璀璨如火如光如日的文明,不是無限的、無所止的,而是必須約束的受限制的,即所止。唐李鼎祚引鄭玄注:“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卦互體坎艮,艮止于上,坎險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周易集注》)必要的文飾是亨,但文飾僅小利,它是不可勝質的。中國文化所遵循的文質觀,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它追求無過無不及,主張過猶不及,講文飾而止于禮義、而止于至善。有文必有質,有質必有文,質是文的內在本質,文是質的外在形式,無本質的形式是干癟的空殼,無形式的本質是缺乏美感的存在。一方面強調“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語),另一方面反對“文過飾非”,不為假象遮掩本質。只有二者密切結合,內外融通,須臾不離,才是中國式的文質觀。賁道之大旨,于此可見。誠如宋程頤所說:“物有飾而后能亨,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有實而加以飾,則可以亨矣。”(《伊川易傳》)
如果仔細閱讀賁卦的爻辭,我們就會更清楚《周易》對文、質關系的美妙描述。賁卦由下而上,依次為初九爻:“賁其趾,舍車而徒”,是說先文飾腳趾,以步代車,不炫耀乘車的榮光,實乃素樸無華;六二爻:“賁其須”,此爻屬陰,女性,是說文飾頭發取悅上位者(也有把須解釋為男性的胡須,那就是文飾胡須),比附文不離質;九三爻:“賁如,濡如,永貞吉”,是說文飾得色彩艷麗、潤澤光亮,似有濃妝極盛、達于頂點之意,象征文飾過度,文勝于質;六四爻:“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是說一旦文飾過度、文勝于質,就應當知止,因為此爻離火之外,示意艮止開始,意即由文飾過度、文勝于質向由文返質、崇質返素回歸,并回歸得圓潤自然,如同素妝白馬一般;六五爻:“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說用堆積很多的一束束素帛來文飾草木雜生的園林,極言此為質樸之處而非華美之所;上九爻:“白賁,無咎,”是說文飾的最佳目標是白,是不文,是無飾之飾,是飾極返素歸樸,呈現出自然之美的無色(雜卦:賁,無色也),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繪事后素”(《論語·八佾》)的最高境界了,與老子所謂復歸于無極、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實為同一機樞。換句話,像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辯若訥的天道一樣,賁卦的主題即大賁若白。三國王弼說:“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無咎也。”(《周易注》)足見本色之美、內在之美才是《周易》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超越外在華美的素美、真美、大美、完美、自然之美。劉勰說過:“衣錦衣繡,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返本”,“白賁占于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文心雕龍》)白賁之白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地位足見其高。
剖析《周易·賁卦》,我們可以梳理出文飾的全過程:飾趾飾須(素樸之美)→飾如濡如(華麗之美)→白賁無咎(無飾之美)。這是一條經由素樸到華麗再回歸平淡無飾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路線,形象有趣地闡發了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變化歷程——或許是先祖圣哲質實無華的生活經驗,或許是先祖圣哲審美理想的理性預設,或許是先祖圣哲對中國之美學的智慧前瞻,卻產生了和產生著影響中國文學和中國文論的巨大正能量。
李白于讀易中,吸收和容納了《周易·賁卦》大賁若白的美學思想,不僅以白為名,而且以白字入詩,奮筆抒寫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詩篇。他宗法易道,歸趣自然,在中國詩壇的黃金時代創造了光耀千古的燦爛與輝煌[13]。
引起我們注意的,還有所謂白賁之志。賁卦上九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這一句,是對上九爻辭“白賁,無咎”的解釋。為什么無咎?由卦象得知,上九剛居柔位,又得到六五以柔承之,而處賁之極,賁道盡去其華麗而歸于樸素,文飾以白為主,有崇尚自然純美之象,故其無所咎害。然則與志何干?王弼的注釋比較圓通:“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無咎也。以白為飾,而無憂患,得志者也。”(《周易注》)
《孔子家語·好生》記載:“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馀,不受飾故也。’”孔子一生,其文學主張是“思無邪”,美學主張是“繪事后素”,既推崇中和之美,又推崇自然之美。所謂正色者,是指“白當正白,黑當正黑”“丹漆不文,白玉不雕”的不飾不雕,即王弼所說的“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無咎也。以白為飾,而無憂患,得志者也。”
由此而及李白,他以自然為宗,力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創作風格;高揚“垂衣貴清真”“文質相炳煥”的審美標幟,其“刪述”之志大得益于《周易·賁卦》的美學指向。楊振綱《詩品解》在“自然”品下引《皋蘭課業本原解》認為“凡詩文無論平奇濃淡,總以自然為貴”,“如太白逸才曠世,不假思議,固矣。”李白的自然詩風與眾不同處就是不假思議,即不假人力,不著粉黛,達到了主(體)客(體)合拍,從容法度,信筆拈來,運神遣意,妙手回春的境界。這是白賁之美的美學效應。
白賁之美,自然、素樸、質實、純粹,李白以白字出之。他近千首詩作,“白”字句出現的頻率為463次,散見于近400多首詩歌。杜甫1 400多首詩歌,“白”字句出現的頻率為493次[14]122-123,以平均值比較,李白顯然高于杜甫。“白”字句在李白詩中高頻率的出現,是非常有趣的美學現象。他的筆下,云白、水白、草白、露白、石白、波白、浪白、月白、筆白……至于“白日”“白發”“白骨”“白馬”“白猿”“白犢”“白鹿”“白雞”“白雁”“白虎”“白龜”“白黿”“白鷴”“白龍”“白鳩”“白鼠”“白鴉”“白鵝”“白鶴”“白酒”“白虹”“白駒”“白玉”“白璧”等等,應接不暇、俯拾即是、難以勝舉。
并且,李白之白,深深地烙印著他清白爽朗、光明俊潔的品格特性。他的名、字、號,他詠月歌月舞月邀月望月賞月的詩句,他那個名叫“月圓”的妹妹、名叫“玻璃”兒子,一切的一切,怎一個白字了得?在李白的世界里,黑白對立,兩極分明,其尚白的美學觀中,無疑浸透著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清白”。李白自喻白玉、白壁,痛斥讒言他的小人是青蠅、惡臭,彰顯了詩人晶瑩透明的人格。長安被逐、坐系獄中、流放夜郎,更慘更重的打擊,使他“終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一朝復一朝,發白心不改”,“白發對綠酒,強歌心已摧”,“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北闕青云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這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李白,詩品和人品絕妙地一致!
[1] 約翰·杜威.確定性的尋求[M].傅統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查德·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M].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 康懷遠.李白讀《易》初證——易解李白芻議(之一)[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6(1):46-51.
[4] 余敦康.周易現代解讀[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5] 張岱年.中國古代關于人格尊嚴的思想[N].光明日報,1999-07-02.
[6] 郁賢皓.李太白全集校注:第3卷[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7] 歐陽玉澄.再論李白萬州詩《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兼議萬州應加強對碼頭文化的認識與發掘[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4(1):14-17.
[8] 李肇.唐國史補[M]//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 段成式.酉陽雜俎[M]//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11] 辛文房.唐才子傳[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2] 林同華.宗白華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3] 康懷遠.簡述《周易》德論凝練的民族之德[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1):74-79.
[14] 李浩.唐詩的美學闡釋[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張新玲)
The Study of Change’s Influence on Li Bai
KANG Huaiyua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The study of change had great impact on Li Bai. There are three main influences among all the changes: self protection attitude reflected in “retiring after the success”; straight personality of “not to serve the rich and the power”; and the aesthetic preference of “the beauty of grey”.
Li Bai; Zhou Yi; retiring after the success; not to serve the rich and the power; the beauty of grey
I206
A
1009-8135(2017)04-0058-09
2017-05-11
康懷遠(1946—),陜西岐山人,中國李白研究學會理事,重慶三峽學院教授,主要研究唐代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