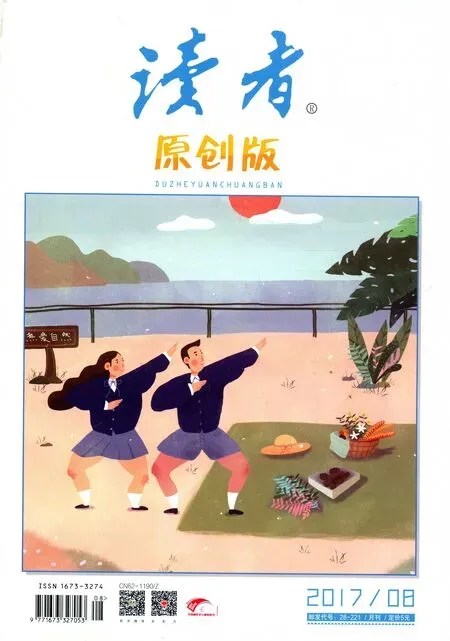上海鄰居
文|銅豌豆
上海鄰居
文|銅豌豆

樓上的上海老兩口中,我更喜歡老太太。
她瘦且白皙,下巴微微內收,一頭銀發,時常在外衣上套一件馬甲,一排紐扣工整而靜默,帶搭扣的黑布鞋一塵不染。她下樓時會扶樓梯扶手,腳步輕盈,沒什么動靜。我常與她在樓道里遇見,她總是不吝對一個中學生報以微笑,并適時奉上問候,“上學去啊”“回來啦”“吃飯沒有”。
支援三線建設到西北多年,老太太的口音辨識度依然極高,濃重的上海腔,黏膩婉轉,好像永遠也不會憤怒,像糖鍋里拔絲,螺螄殼里挑肉。說話大抵也能成為慢工細活,時而是快要起勢的歌唱,時而是即將收尾的吟詠。我家住一樓,是她出入的必經之地,常能聽見她與人打招呼或有片刻的閑聊,那個聲音恰到好處,聽得見但又不鉆耳朵,進退有度。
老太太手巧,每年端午都會送來兩個肉粽,軟糯醇香,每一粒米都沾著肉味兒。她幾乎每年都重復著同樣的話:“這邊買不到大的粽葉,要是在我們老家,能包更大的粽子。就是個心意,你們嘗嘗。”有一年端午,我們都不在家,老太太直接把粽子掛在門把手上,但家人都知道那是她掛上去的。這邊的人,沒有包肉粽的習慣,更做不出那么鮮美的味道。
看上去,老頭兒是在另一個極端—一年四季穿深色中山裝,舊得不像樣子,戴一頂藍色有檐兒的帽子,草綠色解放鞋,略微駝背,衣服褲子都很松垮,皮膚黝黑,一雙眼睛大而圓,像是隨時要提問。
老頭兒的細致,在纖毫之間。走在路上,他總是低著頭,看見煤球便撿起來,摘下帽子盛著端回家,這令我常常把他與上海人區分開—那樣一個光鮮洋氣的國際大都市里來的人,怎么會撿煤球呢?又怎么會把煤球放在帽子里呢?但是他一張口,的確是濃重的上海腔。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我邊踢著一個螺絲釘邊走路,老頭兒在背后叫住我,大約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只是不停地喊“哎哎哎”。我回頭看他,他說:“這個螺絲釘不好踢的,有用的。”少年的倔脾氣上來,自然不甘心,直接回道:“這東西又不是你的!”老頭兒上前撿起螺絲釘,繼續喃喃地說:“我撿起來就是我的。”
老頭兒不知是何時退休的,早年承接些修自行車的活兒,常常滿手油污。他走路仿佛抬不起腿,鞋底老是拖在地上,人也因此顯得沒精神。從那以后,他與我更不怎么打招呼了,只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我主動開口,他會有回應。但那是極為僵硬的禮節,狹路相逢時對視,他的目光里也有不情愿。那個瞬間,雙方都會為已經打過招呼或終于擦肩而過而慶幸。
就這樣淡淡地做了幾年鄰居。高三那年秋季的一個雨天,放學回家時我發現鑰匙落在教室了,父母也不在,只好在樓道里等。但很不巧的是,老頭兒也在樓道里擺弄一輛自行車,不知道是誰家的。那是一輛“三槍”牌自行車,他不一會兒就修好了,起身拍拍座位,大聲讀出了后座上的英文字母:“BSA。”他背著手轉了一圈,搖搖頭,又兀自說了一句:“Three gun。”天哪,這么洋氣的發音是出自這個老頭兒之口嗎?我向樓道里四下張望,企圖找出另一個人。
我表面平靜,內心開始暗流涌動—他從哪里來?他以前做過什么?他又為什么成為現在這樣?正暗自思忖,老太太系著圍裙、扶著樓梯扶手走到拐角處,對著老頭兒說:“吃飯了。”見我也在,照例親切地問我:“吃了嗎?”我說:“沒吃。”老太太說:“怎么在樓道里站著?”“沒帶鑰匙,等爸媽呢。”“那上來一起吃吧。”“不了不了,他們很快就會回來。”這時,老頭兒說話了:“走吧,先到家里坐坐也好。”
這個家與老太太一樣爽利、整潔,想必是她的杰作。正想著,一雙黑且粗壯的手把一杯茶放在我面前,抬頭時,老頭兒已換了雪白的襯衫,幾乎要發出刺眼的光。老太太招呼我們吃飯,我的確餓了,便一屁股坐在飯桌前。白米飯,三四樣菜,用小碟子盛著,印象比較深的是紅燒扒皮魚,不多的幾條,做得精致,味道很好。老頭兒捧著碗,時而看看我,時而低頭吃飯,依然不怎么說話。老太太十分熱情地招呼,一會兒夾條魚放我碗里,一會兒詢問我上學的情況。我倒是沒有客氣,先于他們好幾分鐘吃完了飯。當我望向對面的老頭兒,他的飯碗四周竟然沒有一根魚刺。他抬頭看我的時候,依然像要提問。
有一次,我正在午睡,外面傳來連續而輕微的敲門聲,我不耐煩地開了門,老頭兒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開腔:“你的鑰匙還插在門上。”說完,趿拉著老式解放鞋,弓著背轉身離開。
這個不可捉摸的老頭兒,盡管他以那樣沉默的方式把魚都留給我吃,盡管他雪白的襯衫一度光芒刺眼,盡管他提醒我收好就快丟掉的鑰匙,但因為煤球、螺絲釘以及老舊的中山裝、解放鞋,還是無法令我感到親近。特別是那次,我在院子門口與人打架,寡不敵眾落荒而逃時,恰好在不遠處的一個角落,撞見那像要提問又不置可否的眼神。老頭兒無疑窺見了我全部的秘密,這令我羞憤難當,卻也無言以對。我報以一個惡狠狠的眼神,轉身離開。那一刻,我真的不想再見到老頭兒,甚至連同那個講究而白皙的老太太都不想再見到。
此后的生活并無二致,他依然在院子里低頭走路,我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飛奔,儼然兩套生活體系。高考結束后,我們的生活終于不再有交集。每年放假回家,我幾乎沒有印象是否再見過他,也不怎么能想起這個樓上的鄰居。只是1998年的暑假,經歷過武漢那次驚心動魄的大洪災回到家里,一個傍晚,終于在單元門前遇到老兩口,老太太依然熱情地問候:“回來啦,好像瘦了。”老頭兒依然一言不發。簡單的寒暄后,老兩口準備上樓時,老頭兒轉身輕輕地說了一句:“水好大的吧,小心。”
那天以后,我再沒見過老兩口。
在這個沒吃到粽子的端午,對送來肉粽的上海鄰居會有懷念,但想來也不遺憾。許多話大概不必說出口,許多事且撒手放過。頭頂總是有反復流經的云,是白云就看看,是黑云就去收衣服。至于那個既令人感動又有意疏遠的老頭兒,他神秘莫測,似乎要提問的眼神里仍然有我曾經的羞憤。在驕縱又卑微、自信又恐慌、怯懦又囂張、純真又世故的今天,在我寫下這篇文章的一刻,這些往事已然成為面對未來的底氣,就像老頭兒從地下撿起的螺絲釘,“撿起來就是我的”。
圖 | 孫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