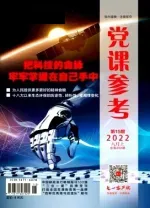大革命前后中共對武裝斗爭的認識與實踐
邵建斌
領導參考
大革命前后中共對武裝斗爭的認識與實踐
邵建斌
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跌入谷底,中國共產黨此時拿起槍桿子,創建了自己的軍隊,開始武裝斗爭,開啟了二十余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但是,摸索出這樣一條道路并不容易,其過程異常曲折、代價十分慘重。大革命前后,中共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實踐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逐漸變化的過程呢?
建黨初期:“宣傳、組織、訓練,究竟是比軍事運動十百倍重要的事”
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組織工人上。一大即認為“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凡有一個以上產業部門的地方,均應組織工會”。雖然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提出如下主張:“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但實際上,“因為黨員少,組織農民和軍隊的問題成了懸案,決定集中我們的全部精力組織工廠工人”“鑒于我們的黨至今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所以代表大會決定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二大時,中共提出:“中國工人要聯合在各種工人階級組織之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力量。”與一大可謂一脈相承。考察三大和四大形成的各項決議案中,雖然也偶有武裝工農的提法,但與后來每每將軍事問題的報告作為重頭戲截然不同。1924年5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上海地方、漢口地方、湘區(含安源)、京區和山東地方向大會的報告中,均未涉及軍事問題。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為數不多的力量,大都投入到了工農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中去了。以相對較少的力量來組織如此眾多的工人組織,本就不敷使用,如果再去組織軍事行動,其中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軍事工作,此時不僅在決議中得不到體現,在實際工作中也是力不從心。

不僅如此,對過于注重軍事工作的做法,中共還持批判的態度。對于“除了軍事運動就無所謂革命,換言之,革命就是‘流血’的軍事行動”這種認識,中共斬釘截鐵地指出:“實在,這是錯誤了。”并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刊文批評國民黨:國民運動的領袖人物“歷來單偏重于軍事活動一方面,或者是一個大錯誤”。他們“只見著革命的活動就是組織軍隊,再沒有別的方法了”。“軍事活動,的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得更真切,就是一個軍隊要真能擔當革命的任務,除非是個真正的革命軍。”相比之下,“我們卻極堅信: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主義的宣傳普及全國,比天天與軍事領袖周旋結合,更為重要”。惲代英對此有簡單明了的說法:“宣傳、組織、訓練,究竟是比軍事運動十百倍重要的事。”
北伐戰爭時期:“軍事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
隨著形勢的發展,武裝斗爭對于政黨和革命的重要性逐漸顯露,建立軍隊、從事軍事活動也愈發地迫切起來。第一次讓中共震驚的是黃埔軍校的學生軍。這支軍隊東征陳炯明,“三年打不破的陳軍,今日竟一敗至此”。戰局的發展完全超出了預料。除了東征以外,在南征軍閥鄧本殷、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中,學生軍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五卅運動也讓中共認識到政黨領導革命,光靠組織和宣傳似乎還不夠,武裝斗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亟起而組織武力”,有“平民之軍隊”,才能有“平民之政權”,“然后可以雪恥,可以立國,可以求得四萬萬人夢想中之自由與獨立”。
在現實的刺激面前,中共逐漸轉變認識。周恩來、瞿秋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早在1924年11月,周恩來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選調優秀共產黨員到各部門任職,還代表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在黃埔軍校的中共黨組織,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不僅如此,周恩來主持的廣東區委還直接領導了一支革命武裝——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在新的形勢下,周恩來雖仍認為工人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但同時也認為“兵士預備武裝起來與英帝國主義決一雌雄”同樣重要。工農運動顯然不是唯一選擇了。五卅運動一年后,瞿秋白回顧成敗得失時總結道:“中國民族現在一切對內對外的要求”“都必須要人民自己的積極的甚至于武裝的斗爭,革命軍隊的戰爭,撲滅一切反革命的軍閥——然后才能達到目的”“只有這種斗爭,從抗稅抵貨的運動,一直到武裝暴動和革命戰爭,才能算是五卅運動的真正繼續,才能保證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最后勝利”。在這里,武裝斗爭顯然已躍居更為重要和關鍵的地位。
中共中央在1925年四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并在10月通過《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決議案》,《決議案》認為應“擴大工人自衛軍的組織,不但在鐵路上礦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廠里也要進行這種工作,要組織青年工人的武裝十人隊百人隊等,因此中央委員會之下必須設立軍事委員會”。12月12日,中共中央將“軍事運動委員會”改為“軍事部”,這是中共第一個專門從事軍事工作的組織。1926年7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建黨以來的第一份《軍事運動議決案》,指出:“軍事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軍事工作負責同志,應與當地黨的書記發生密切關系,向書記報告工作情形,并和書記商量自己工作。”從此,軍事工作成為黨各項工作中的一部分,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愈發重要。
這里有個問題需要說明:在這一階段,中共雖認識到武裝力量的重要,也在一些論述中對此加以強調,但是并沒有突出武裝力量的階級性質,沒有突出無產階級的獨立領導。
不過,即便此時沒有突出強調軍隊的無產階級屬性,也不能否認:中共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已明顯進了一步。
大革命失敗后:“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下令強占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量地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共產黨在一夜之間由合法變為非法,由地上轉入地下。面對局勢的驟然巨變,下一步怎么走?
其實早在1927年年初,毛澤東在實地考察了湘潭等五縣的農民運動之后,認為批評農民運動“過分”的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因為被拿來佐證農民運動過分的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況且“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認識到所謂“過火”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積極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質。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武裝斗爭。在這樣的邏輯下,武裝斗爭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也是唯一選擇。
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的策略,并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反之,“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實際的結論。早在1927年6月份,毛澤東就提出要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7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談及形勢,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武裝斗爭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已是十分重要且關乎全局的成敗了。
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黨政府宣布“分共”,繼南京政府后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在如此嚴重的刺激之下,中共中央徹底拋棄了對國民黨的幻想,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指出:“農會政權的斗爭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裝才能保障其勝利。”《通告》還提出了農民武裝上山的問題。這是對中國革命客觀實際更深一步的認識。
真正將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付諸實踐的是南昌起義。1927年7月下旬,周恩來等就在“策劃如何繼續革命的方法”,他“覺得與其受人宰割,不如先發制人”“因而贊成在南昌由葉挺部首先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形成反武漢反南京的中心”。隨即,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成立。7月31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嚴,將近半夜2點鐘的時候,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率領北伐軍三萬余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城內外響起了一片激烈的槍聲”。“到天亮時止,全部結束了戰斗,殲滅了敵人一萬多人,武裝起義宣告勝利結束。”南昌起義的意義無需贅言。由此開始,中共開始獨立掌握自己的武裝。
8月7日召開的緊急會議則更進了一步。毛澤東在會上說:“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的發言切中了要害,指出了以往革命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在武裝斗爭上存在的不足,并用“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樣形象、生動而又鏗鏘有力的語言,突出了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強調“槍桿子里出政權”,并非毫無前提條件。其前提之一是發動群眾。沒有群眾的充分發動,所謂的槍桿子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前提之二便是“黨指揮槍”。毛澤東曾經說:“我們說槍桿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沒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便沒有這個保證。主持八七會議的李維漢后來說:“毛澤東同志的發言,是在黨領導革命的根本性問題上,不但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而且提出了對爾后具有重要意義的指針。”這是十分中肯的評價。八七會議以后,武裝起義如星火燎原一般,在湘、鄂、贛、粵、陜、甘、豫等地次第展開。從此,中共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革命道路。
無論如何曲折和反復,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武裝斗爭,而是在這條路上繼續探索,并最終經由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締造了一個嶄新的中國。
(摘編自《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