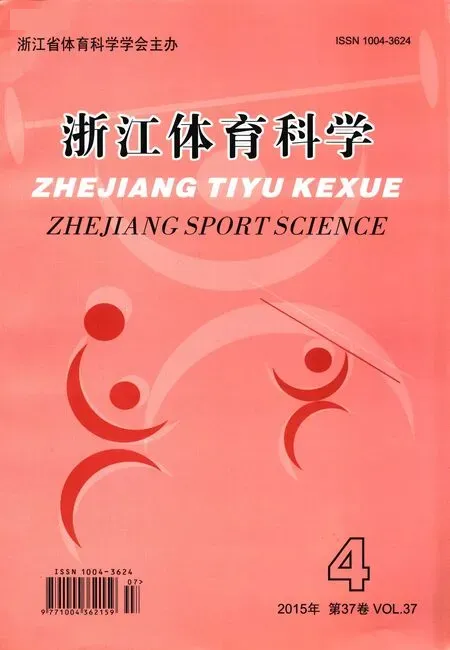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訓練對高脂血癥小鼠脂質代謝的影響
朱淦芳
(浙江中醫藥大學,浙江 杭州 310053)
?
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訓練對高脂血癥小鼠脂質代謝的影響
朱淦芳
(浙江中醫藥大學,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目的:研究不同的游泳持續時間對改善高脂血癥的效果,尋找最適宜的運動強度和持續時間,達到最好的降脂目的。方法:將80只昆明種雄性小鼠隨機分為正常對照組(C)、高脂對照組(H)、洛伐他汀組(L )及不同強度的游泳運動組(S1、S2、S3),通過建立高脂血癥小鼠模型,對高脂小鼠進行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訓練進行干預以及洛伐他汀治療,6周后,檢測血清及肝臟總膽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C)等含量變化,分析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訓練對脂質代謝的影響。結果:經過6周的游泳訓練后,高脂小鼠的TC、TG水平明顯下降,HDL-C水平明顯提高;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訓練中,20~40min/d游泳組綜合降脂能力最好。 結論:當以游泳訓練對高脂血癥小鼠進行干預時,中等強度的游泳訓練干預效果更為顯著。
關鍵詞:高脂血癥;小鼠;游泳;持續時間
0前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習慣特別是飲食習慣的改變,高脂血癥的發病率呈明顯增高的趨勢,由于血脂水平過高引起一些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疾病,如動脈粥樣硬化、冠心病、胰腺炎等的發病率也逐年上升。 高脂血癥的主要誘因之一就在于脂質在血管內皮沉積引起動脈粥樣硬化、冠心病、腦血管病和周圍血管病, 故治療高脂血癥對于預防其他相關誘發疾病具有重要的意義。
高脂血癥運動干預的機制,主要是通過骨骼肌做功、耗氧、耗能對整個機體產生的應激,使得各器官調整、適應而產生相應代謝變化的過程[1]。迄今為止,在開展深入研究的同時,我國研究人員進行了大量的高脂血癥運動干預的臨床治療效果的觀察實驗,從實驗結果來看,不同形式的運動干預可以降低TC、TG、LDL-C水平,升高HDL-C[2]。對高脂血癥患者血脂狀況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3-4]。然而,縱觀國內外文獻,不難發現有關不同的運動持續時間對改善血脂的研究并不多見。基于此,本課題針對不同的游泳持續時間對于高脂血癥小鼠降脂質代謝的影響開展研究,為運動干預降血脂尋求更為適宜的運動方案。
1實驗材料
1.1實驗動物
從浙江中醫藥大學動物實驗中心選取4周齡昆明種雄性小鼠80只,體重范圍介于18~22g。
1.2高脂飼料
為了能夠順利建成高脂血癥動物模型,本研究采取高脂飼料進行喂養。高脂飼料配方為基礎飼料79%、膽固醇1%、蛋黃粉10%、豬油10%,浙江省醫學科學院提供。
1.3實驗主要器材
塑料游泳池(100×60×50cm3),水深超過小鼠體長2倍,水溫32±1℃。電子天平(型號:T200,G&G);恒溫水浴箱(型號:DK-S24,上海森信實驗儀器有限公司);旋渦混勻器(型號:XW-80A,上海精科實業有限公司);低速低溫離心機(型號:ID25-2,北京醫用離心機廠);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型號:UV2400,徐州華納精密儀器有限公司),全波長酶標儀(型號:varioskam flash)等。
1.4主要試劑
TC、TG、HDL-C檢測試劑盒(溫州東甌津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羥甲基纖維素鈉(上海試四赫維化工有限公司)等。洛伐他汀:由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惠贈。用蒸餾水制備1%的羥甲基纖維素鈉溶液100mL,待溶解后加入30mg洛伐他汀粉末,配制成0.3mg/mL洛伐他汀混懸液。氯化鈉、苦味酸等其他試劑均購自杭州華東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實驗方法
2.1動物分組
80只雄性小鼠分籠飼養,每個鼠籠10只,自由飲食,適應性喂養3天,由國家標準嚙齒類動物常規飼料喂養。動物飼養環境24℃±2℃,濕度40%~60%,自然晝夜節律。并將其分別分為正常組(C組,n=20),高脂對照組(H組,n=20),洛伐他丁治療組(L組,n=10),大強度游泳運動組(S1,n=10),中強度游泳運動組(S2,n=10),小強度游泳運動組(S3,n=10)(詳見表1)。

表1 實驗動物分組及運動干預方案
*注:游泳組(S1、S2、S3),高脂對照組(Hyperlipidemia, H),正常組(Control, C)每天0.2mL生理鹽水灌胃;洛伐他汀組(Lovastatin, L )不進行運動,每天灌注20mg/kg劑量的混懸液
2.2高脂模型的建立
C組小鼠20只喂飼普通飼料,其余各組小鼠為模型組喂飼高脂飼料,6g/只/d,自由飲水。14 d后,選取兩組小鼠各10只,禁食18h,摘眼球取全血于1.5mL EP管中,4℃,4 000 r/min 離心10min,提取上清液,用試劑盒(酶偶聯比色法)測定血清TC、TG、HDL-C。模型組血清血脂的TC、TG測得的濃度與正常對照組相比顯著性升高(P<0.05)、HDL-C濃度顯著性降低(P<0.05);模型組肝臟的TC、TG測得的濃度與正常對照組相比顯著性升高(P<0.05),說明高脂血癥模型建立成功。
2.3運動干預實驗
分別對S1、S2和S3組進行游泳運動干預,具體干預時間及方案見表1。
2.4各項指標的測定
2.4.1體重和身長。每周一次測定小鼠體重和身長,并定期觀察食欲、行為、糞便、毛發及動物死亡情況,分別作記錄并比對。
2.4.2血清各項指標。分離血清:6周后,最后一次休息以后,所有小鼠禁食18h,眼球取血處死,并將血液以3 000 r/min,離心15min后提取得到血清,放置冰箱4℃保存。
血清在冰箱中放置過夜后,測定各項指標:TC、TG、HDL-C的測定均采用酶聯比色法,按照試劑盒說明的方法進行操作,以UV2400紫外分光光度計比色測定。
2.4.3肝臟各項指標。小鼠處死后,立即將其進行解剖,取出肝臟,稱取總肝重。用肉眼觀察肝臟病變,在相同部位取肝臟精確稱取0.1g在冰水中制成20%的勻漿,4℃,4 000 r/min,離心10min,提取上清液。放置冰箱4℃保存。
肝勻漿上清液在冰箱中放置過夜后,用酶聯比色法測定肝臟的TC、TG的含量,按照試劑盒說明的方法進行,以UV2400紫外分光光度計比色測定。肝指數用公式進行計算,肝指數=肝臟質量/小鼠體重。
2.5數據處理
根據生物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8.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方差分析,實驗結果均數±標準差(Mean±SD)表示,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3實驗結果
3.1體重和身長
高脂飼料造模后,給予運動干預6周,測定各組小鼠的體重和身長,體重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高脂運動組在游泳運動干預6周后,體重均有明顯的下降,與運動前都有較顯著性差異。就減輕體重方面而言,S1、S2和S3各組小鼠的效果要明顯優于L組。在不運動的情況下,H組和C組的小鼠體重均有略微增加。而表中的數據也可以顯示出,S2組對于體重的減少效果最為明顯。故運動對于體重的減輕非常有益處。高脂飼料對小鼠的身長影響和普通飼料相比并無顯著性差異,而且運動干預前后對小鼠身長的影響也不明顯。

表2 實驗后小鼠體重、身長變化結果
注:與正常對照組比較*P<0.05,**P<0.01
3.2血清各項指標的檢測
高脂小鼠模型在運動干預6周以后,各組小鼠檢測血清脂質的水平,并通過與C組的比較,分析判斷干預效果見表3。

表3 游泳干預后各組小鼠血清TC、TG、HDL-C的變化結果
注:分別為與C組比較,*P<0.05,**P<0.01;分別為與H組比較,●P<0.05,●●P<0.01;表4同
從表3可以看出,S2組的血清TC,TG,HDL-C水平分別與C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而與H組的血清TC、TG、HDL-C水平有非常顯著性差異。S1組血清TC和HDL-C水平分別與C組相比有極顯著性差異;TG有顯著性差異;而與H組的血清TC水平相比有顯著性差異;TG、HDL-C水平無差異。S3組血清TC、TG、HDL-C水平分別與C組相比有非常顯著性差異;TC水平與H組的血清TC水平相比有顯著性差異;TG、HDL-C水平無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的運動持續時間,對于調節血脂水平的差異比較大,20~40min/d的持續游泳時間,對于改善血脂效果更為明顯。且L組和S2組的數值比較接近,說明S2組的效果與洛伐他汀治療的效果相似,在以后的預防和治療中適當的運動可以代替藥物治療,減少副作用。
3.3肝臟脂質各項指標的檢測
高脂小鼠模型在運動干預6周以后,各組小鼠檢測肝臟脂質的水平,并通過與C組的比較,分析判斷干預效果見表4。

表4 游泳干預后各組小鼠肝臟TC、TG、肝指數的變化結果
從表4可以看出,S2組TC、TG水平分別與C組的水平相比有顯著性差異;與H組相比有非常顯著性差異。S1組血清與C組相比TC水平有非常顯著性差異;TG水平有顯著性差異;而與H組的血清水平相比有顯著性差異。S3組血清TC、TG水平分別與C組相比有非常顯著性差異;TC水平與H組的血清TC水平相比有非常顯著性差異;TG水平無差異。說明運動可以有效改善肝臟的脂質水平,而且改善較為明顯。總體來說,對于降低肝臟TC、TG水平,以中等強度為代表的S2組運動干預效果較好,接近于洛伐他汀藥物治療。
4討論
4.1高脂模型的建立
肥胖和高脂血癥除了遺傳因素外,主要是由于脂肪攝入過多,體力活動不足,長期能量過剩所致。研究表明,攝入富含脂肪的食物,動物飽腹感差,且僅需不到 2% 的能量就能轉化成機體脂肪[5]。因此,人們常用高脂飼料來制作高脂動物模型以進行科學研究。本研究用于建立高脂模型的動物,在血清脂蛋白構成上以及肝臟膽固醇和脂蛋白代謝酶的調節方面,盡可能與人類相近[6]。決定采用小鼠作為建模對象。因為小鼠容易繁殖和飼養,建模所需的成本會比較低;建模的模型形成時間較短,利于實驗的順利進行。
4.2不同持續時間的游泳對小鼠體重的影響
對有氧運動的強度和時間安排,美國運動醫學會1996年提出:人體健身運動的適宜強度是本人最大強度的 60%,適宜時間是每天 30~ 60min[7]。采用不同的運動設計方案,經過6周的運動,平均體重下降最多的運動組小鼠是S2組,下降3.5g,S1組小鼠平均體重下降2.9g,平均體重下降最少的S3組,下降1.90g。L組小鼠平均體重下降0.8g,效果并不明顯。通過分析數據可以發現,適宜持續時間的運動對于體重的減輕有明顯的效果。
4.3不同游泳持續時間對小鼠血清脂質的影響
持續使用高脂飼料飼養小鼠后,小鼠的TC、TG水平都比正常組的小鼠明顯要高,低于高脂模型組;而HDL-C則顯著低于正常組小鼠而高于高脂模型組。實驗結果分析得到:降低血清脂質效果最好的S2組的小鼠降低TG的能力甚至優于L組,而降低TC的能力也與L組接近,只是升高HDL-C的能力略有不足,低于C組。因為C組所采用的陽性藥物是洛伐他汀粉末,在臨床上使用的調制藥物中屬于他汀類。而他汀類具有競爭性抑制細胞內膽固醇合成早期過程中限速酶的活性,繼而上調細胞表面LDL受體,加速血漿LDL的分解代謝,此外還可以抑制VLDL的合成。因此他汀類藥物能顯著性降低TC,LDL-C和apoB,也降低TG水平和輕度升高HDL-C。本實驗也顯現出了洛伐他汀藥物主要降低膽固醇這方面的能力.。而有氧運動對于其他方面的調脂能力與此類藥物相比相差不是很大。而運動組中各個持續時間相比較,20-40min/d的游泳運動訓練對于調節血脂的綜合能力比較高,由此可見,中等強度的游泳運動對于高脂血癥的小鼠代謝具有調控優勢。
4.4不同游泳持續時間對小鼠肝臟脂質的影響
通過觀察高脂組和普通組小鼠肝臟顏色比較發現:普通組小鼠的肝臟為暗紅色,而高脂組小鼠的肝臟則為明顯的淡紅色,略泛黃色,并帶有較多脂肪。而各小鼠通過游泳干預或藥物治療后,肝臟的顏色較未運動都有所改善,為鮮紅色。20~40min/d的游泳時間對于肝臟TC、TG的降低相對比較好。研究表明:規律運動可影響B族清道夫I型受體( SR- BI) 基因表達,提高血漿脂蛋白脂酶、膽固醇脂酰轉移酶的活性, 降低肝脂肪酶的活性, 進而改變脂質代謝,達到防治高膽固醇血癥的目的[8]。因此,對于脂肪肝患者來說,有規律的運動非常有利于肝臟的降脂,便于針對性地治療。
5結論
參考文獻
[1]陳肇憲.游泳訓練高脂血癥對小鼠脂質代謝的變化[J].中國組織過程研究與臨床康復,2008,12(50):9925-9928.
[2]趙煥,連曉清,嚴建軍,等.不同時間段運動與高脂血癥的關系[J].江蘇醫藥,2013,39(11):1277-1279.
[3]肖秀玉.高脂血癥病人配合運動的療效觀察[J].福建醫藥雜志,2001,23(5):120-121.
[4]張勇,紀志敏,齊文華.不同運動時間的健美操鍛煉對中年女性血脂及體質量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4,24(8):5108-5109.
[5]Defronzora,Ferraninie. Insulin Resistance:A Mulifaceted Syndrome Responsible for NIDDM,Obesity Hypertension,Dyslipidemia and Athero sclerosis Card iovascular D isease[J].Diabetes Care,1991,14:173-194.
[6]劉雪梅,吳符火.幾類高脂血癥動物模型的比較[J].中西醫結合學報,2004(2):132-134.
[7]何振強.有氧運動與控制飲食對肥胖者和高脂血癥患者的療效觀察[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2,22(5):34-36.
The Effect on Different Durations of Swimming Training
to Lipid Metabolism of Mice with Hyperglycemia
ZHU Gan-fang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study is done to seek the most appropriate exercis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to lower lipid by studying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uration of swimm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pid metabolism. Methods: Dividing 80 male Kunming mice into 4 groups randomly: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C), the high fat control group (H), the Lovastatin group (L) and the swimm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exercise intensities (S1, S2, S3). Through modeling the mice with hyperglycemia, intervening the hyperlipidemia mice’s swimming training with different durations and treating them with Lovastatin, after six weeks, tested content variation including the serum and liver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s (TG) and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C)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urations of swimming training on the lipid metabolism. Results: After six weeks’ swimming training, the hyperlipidemia mice’s levels of TC, TG apparently decline while the level of HDL-C apparently improves. In swimming training of different durations, the best group with ability of comprehensive lipid-lowering is 20-40 min/d swimming group. Conclusion: When intervented the hyperlipidemia mice by swimming training, the most apparent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the swimming training with moderate strength.
Key words:hypermedia; mice; swimming; durations
中圖分類號:G804.7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