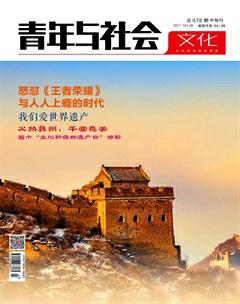根本就沒有什么網癮網癮是時代的眼淚
大盜賊霍老爺
在我小時候,是臺球廳最火爆的時候。家旁邊曾經有一家臺球廳,其中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經常去打臺球,每天都去,雷打不動。記得有一次停電了,就聽見樓下砰砰地敲臺球廳的門,看臺球廳的是個老頭,已經睡下了,隔著門問是誰?
是那個少年的聲音,他說:我是誰誰,我來打臺球。
“沒電,沒電你打什么?”老頭被驚了覺,很生氣。
“點蠟也行。”少年固執地說。
“我這沒蠟。”
敲門聲音停了,就聽見那少年一溜小跑跑了。
老頭剛躺下,又是砰砰砰地拍門。
“我買來蠟了。”還是那孩子。老頭被叫的沒辦法了,只好把門打開。我隔著窗戶往下看,看見他把蠟燭點著,把蠟油滴在臺球桌上。
老頭一巴掌把蠟燭給他打地上,“別把案子給我燒了。”他就默默撿起來,很認真地焊在墻邊的鐵架子上。然后把錢給老頭,開始擺球,自己跟自己打。有一次,這孩子被他爸逮到在臺球廳玩,把他拽到當街往死里打,他就默默地挨打,也不躲。但是沒過幾天,還是過來打臺球。
聽老頭說,這孩子以前挺聽話的,不知道為啥迷上了臺球。
時代病
如果按照楊永信,陶宏開這些教授和那些把孩子送進“網癮戒除中心”家長的看法,那個孩子無疑是有“臺球癮”的。有些人把“這癮那癮”放在嘴邊,卻忽略了一個問題?網癮或者其他癮為什么存在。
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公共娛樂匱乏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以前,幾乎所有的縣城都有一個體育場,一個電影院,一個劇院,這是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給國民的僅有的文娛福利。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這些場所也推向市場,這個“1+1+1”在市場中幾乎都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危機。
我記得在小學的時候,六一兒童節還有一場兒童劇,后來漸漸的連這個都沒有了。體育場的草坪開始還有維護,后來就已經成了菜地,下雨的時候,就在泥里踢球。電影院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暑假寒假經常推出套票,15塊錢,可以看一暑假的電影,平均一場連5毛錢都沒有。我當時買了幾個暑假的套票,有幸在十來歲的年紀就在大銀幕領略了邵氏的動作片和三級片還有一些美國老電影,得以對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有了初步的批判學習,我的父母如果知道看的是這個,一定不會給甘心花錢買票。
而這15塊錢,全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的家長樂意掏,那個電影院最終也維持不下去了。
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的國產電影,有一個特點,幾乎都是文藝片,電影工作者拍電影根本不是給群眾看的,都是給外國評委評獎用的,我當然不是指責電影工作者,實際上就是拍了,也沒人會去看。
一直到2000年后,報紙上還在寫電影院的經營艱難,坐標是武漢,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可想而知,實際上,很多地方的電影院也只是一個站牌名,根本已經不存在了。直到近年,電影市場才重新火爆。
同樣娛樂匱乏影響的不僅僅只是孩子, 90年代一些迪廳開業的時候,涌入迪廳的大多是成年人,我記得家鄉第一所保齡球館營業,我記得很多父母也經常去打上幾個小時。
少年宮
文化生活匱乏,校外教育也匱乏。“少年宮”原來是蘇式教育的標配,但在文革中,正規學校教育都沒法開展,校外教育也成了革命活動的另一種形式。改革開放后,雖然提出了發展校外教育的方針,但實際上,一切向錢看的大背景下,對于大多數地區,很多學校老師的工資都要拖欠,校外教育更無法保證,是長期被忽視的,根本沒有錢投入到少年宮上來。
少年宮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是個好像有,但并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公共文體沒有,校外教育也沒有,但娛樂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對孩子而言,在這個年齡,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極度渴求的。
這種渴求的欲望怎么釋放呢?錄像廳、臺球廳、電子游戲室,就成了很多少年的去處。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因為這是孩子們少有的娛樂,長期壓抑的娛樂欲望得不到釋放,任何形式的娛樂都會導致沉迷。
這是早在網絡游戲和網吧出現以前就存在的社會現實,如果說網絡成癮的話,那么這些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稱為電影成癮,臺球癮,電子游戲癮呢?
在很多家長看來是的。電子游戲一直被稱為“電子海洛因”,錄像廳和臺球廳是壞孩子去的地方,實際上,雖然錄像廳也經常放星爺的電影,但同樣也經常放些三級片,在這里混跡的少年確實很容易學壞。
不過,這是市場的自然選擇,有市場需求就有供給。在正常的文化娛樂需求無法滿足的情況下,年輕人一遇到游戲的光影聲色,徹底淪陷的必定不在少數。而其實很多三線城市由于管理不嚴格,無論錄像廳也好,臺球廳也好,以及電子游戲室,網吧都是一片烏煙瘴氣,也難怪很多家長把去這些場所視為學壞。
中國三十年的發展非常迅猛,迅猛到很多家長對涌現的新鮮事物一無所知。家長們依據的是過去的生活經驗,今天,如果家長看到孩子看電影大概不會覺得看周星馳電影有什么不好,但是在我們小的時候,有些家長看見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經常斥之為瞎胡鬧。他們無法理解這種東西也可以稱之為電影。
時至今日,沒有多少家長會把看電影打臺球視為洪水猛獸,但在當時,卻為很多人所不容。因為人的觀念一直在更新,守舊的人也會迅速被邊緣化,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但每一粒沙子,都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他們或許無法阻止時代,但他們可以阻止自己的孩子。
在這種恐懼之下,家長們先是封堵錄像,后是封堵臺球,再封堵電子游戲,后封堵網吧。每一個新鮮事物出現,都有一個從被抗拒到被接受的過程, 就像大清的國民看到火車,第一反應是這玩意兒破壞風水,如今再怎么科普轉基因,還是有人堅持要吃非轉基因大豆油。對“網癮”的妖魔化,本質上是一種對被現代化拋棄的恐懼。
觀念的沖突與倫理的大衣
有個朋友的父親是個政府官員,原來他因為玩微信還跟父親有過爭吵,誰知道轉眼連政府總理也提倡使用微信,中央政府還有微信訂閱號,這個父親被迫也得去學習,一用結果挺好,于是每天發給這個朋友幾篇文章讓他學習,這里面有心靈雞湯,也有網絡謠言,他現在頭疼的是怎么讓父親戒掉微信的“網癮”。
有個姑娘過年回家,她媽看她整天抱著手機看,怎么看也看不順眼,讓她不玩手機,不行就看會兒電視,在她看來,看電視要比玩手機好得多,看電視相比較玩手機而言,不那么“玩物喪志”一點,而在前幾年,她還對女兒看電視深惡痛絕。
所以你看,哪里有什么網癮,只有新舊觀念的沖突。
在中國,新舊兩種觀念的碰撞通常要穿上一層倫理的外衣。
“孝”是中國的最高倫理,“孝順”“聽話”一直是對培養孩子的要求,同樣的事情,大人做可以,孩子做就不行。
老子管教兒子,天經地義。很多家長自己也沉迷于麻將打牌,但是管教起孩子卻振振有詞,“我是為你好。”“為你好”的背后是中國的另一個傳統,教育的功利化。中國人注重教育,是極度重視教育的產出的,是有非常現實的功利目的的。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似重視教育,但背后是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若是不能求取功名,則讀書反而是羞恥的,作為窮秀才的范進是不被看重的,連窮秀才都不是的孔乙己是為人嘲笑侮辱的對象。
教育是無數普通家庭的攀爬階層臺階的希望,是他們不容有失的中國夢,望子成龍的結果必然是對孩子更嚴格的控制。
這也是一些家長的邏輯,孩子最好把所有時間來攻讀課本,“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任何和孩子爭奪時間的東西都要被禁止或者限制。
網癮的根本是文化、娛樂、教育
我在學生時代,每到周末就去新華書店去蹭書看,什么書都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完了餓著肚子回家。如果按照楊教授的說法,我有“書癮”,但人們常常把讀書神圣化,而把打臺球玩游戲污名化。其實都是娛樂,只是娛樂的方式不同,并沒有本質不同。
但新華書店也漸漸維系不下去,書越來越少,我當時一直有種負罪感,覺得書店是被我這樣的人看黃的。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這是中國多數城市的常態,我的負疚才減輕一些。
但要感謝新華書店,我現在還能寫幾個字,要歸功于那時候看過的幾十個架子的書。
在新華書店閱讀那些書籍時候,很多長輩苦口婆心地跟我說,看書挺好,但要把功夫用在正經書上,少看點閑書。
正經書就是課本,在他們看來,除了課本,歷史文學軍事社科,只要是課本上不收錄的,幾乎都是閑書。在這些人眼里,我大概是有“閑書”癮的。
看書尚且如此,上網、玩游戲被視為洪水猛獸就更可以理解了。一切有害于孩子考上大學或者好大學的娛樂都是另一種程度的“網癮”,這些應該包括但不限于電影、電視劇、踢足球、打籃球,諸如此類,只看家長心情和你的成績。
因為,在家長眼里只有上大學一條路,這道理原也不錯,教育確實是最容易的一條路。
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適合讀書這條路,而中國的教育資源也過于緊缺。拿中國電競傳奇@Sky李曉峰 舉例,照楊教授的看法,sky無疑是個網癮少年,因為打游戲被父親打,成績不好,在他玩游戲的時候,中國電競這個行業的前景也同樣不明朗,他最初也只是愛玩游戲,應該也沒有想過他的未來是作為人皇sky被人銘記。如果按照父親給他的人生規劃,他應該考大學,或者當個縣城的醫生,而且可能是個很糟糕的醫生,在他跟父親做手術的過程中,他還因為暈血昏過去了。
按照這樣的規劃,他的天賦無疑是被浪費了。而他作為電競選手的人生軌跡要比他走大多數人走的道路要輝煌許多。
實際上,老子管教兒子并不是天經地義,尤其對于中國這個飛速發展的國家,老一代人曾經的人生經驗,可能馬上就過時了,是不足以指導下一代的。
網癮是時代的眼淚。如果孩子有多樣的文化娛樂產品選擇,他當然不會沉迷。
“網癮”的根本原因是娛樂文化生活的匱乏,網癮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對現代化的恐懼,而網癮的進一步妖魔化是因為中國教育功利化和父權制的傳統,相信,只要這種狀態不改變,未來還會有手機癮,或者VR癮,或者什么什么癮。
網癮需要拯救嗎?恐怕需要被拯救的是中國的文化、娛樂、教育,對家長來說,還有岌岌可危的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