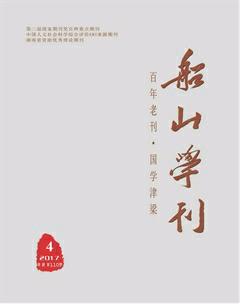船山與變法
摘 要:譚嗣同是晚清戊戌變法的主導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紀末期研究與宣傳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變法作為晚清青年知識分子與士大夫面對西方文明沖擊所進行的政治改革運動,歷來被認為是中國近現代史與哲學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環。而除了西學之外,譚嗣同在推動戊戌變法的時候,實際上是以船山思想作為其變法維新思想的主要傳統哲學基礎與精神動力。在譚嗣同的維新變法思想、哲學與精神氣質中,船山思想作為中國傳統儒家哲學的代表與西學、佛學一道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王船山;譚嗣同;《仁學》;戊戌變法
甲午戰爭后,譚嗣同寫道:
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于唐虞三代之盛,幾為士論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揚之太過,后身使四國,始嘆斯言不誣。夫閱歷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護前,不自諱過,復何難寤之有?即嗣同少時,何嘗不隨波逐流,彈抵西學,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久之漸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狀吾過。①
郭筠仙即郭嵩燾,是第一代湖湘士大夫集團中倡導洋務運動的干將、中國最早的外交家。其后半生基本上在思想上的爭議與政治上的無人問津中度過,他在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去世,享年73歲。而三年后,其心心念念的洋務運動也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宣告終結。可以說,甲午的戰敗,讓清王朝的原先仍舊隱而未顯的危亡成為亟在眼前的現實,也使得一些人意識到了郭嵩燾早年的遠見卓識。而今天,我們似乎很難想象其后在戊戌變法中戮力維新的譚嗣同,早年也和大部分人一樣攻擊過他的這位湖南同鄉與前輩。
但從船山思想研究傳承的角度上說,將郭嵩燾與譚嗣同認作船山學術研究上的前后輩倒也并無不可。譚嗣同少年時曾就學于當時的湖南瀏陽名士歐陽中鵠②,歐陽中鵠與首建船山祠的郭嵩燾是同輩人,同時也是船山學的忠實擁躉。在譚嗣同看來:以其師歐陽中鵠為首,外加王闿運、鄧輔綸,這三人是當時精研船山學的湖南士人中的翹楚。而鄧輔綸、王闿運又分別是船山書院的第二任與第三任山長。對此,譚嗣同有詩贊曰:
薑齋微意瓣③探,王鄧翩翩靳共驂。④
可以說,譚嗣同就是在曾國藩、郭嵩燾等晚清第一代湖湘士大夫集團所掀起的研讀船山學術之風潮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湖湘士人中的代表人物。而譚嗣同也從不諱言自己對于王船山的推崇及其所受到的船山思想之影響。譚氏云:
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幾絕。國朝衡陽王子,膺五百之運,發斯道之光,出其緒余,猶當空絕千古。⑤
又云:
為學專主《船山遺書》,輔以廣覽博取。⑥
一、直面憂懼:船山思想對于譚嗣同人格精神的塑造
但與郭嵩燾與曾國藩等傳統士大夫從具體現實層面出發,比較關注船山史論的思想研究進路不同。⑦船山思想對于譚嗣同的影響,首先在拋開思想藩籬、直面憂懼的精神氣魄上。譚嗣同云:
前命肆力《四書訓義》,伏讀一過,不敢自謂有得也。然于“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始知內省不疚之后,大有功力,非一省即已。雖然,功力果安在?以意逆之,殆《中庸》之云乎?夫欲不憂懼,必先省無可憂懼,所謂無疚也。無可憂懼,仍不能不憂懼,則亦憂懼之而已矣。故以無可憂懼治憂懼,不如以憂懼治憂懼。若曰無可憂而憂,無可懼而懼,是則可憂也,是則可懼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焉斯可矣,奚為其恐懼乎?⑧
而在譚嗣同講的這一“大有功力”的“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段落中,王船山到底說了什么呢?船山曰:
夫心有所期得,而不保其無失也,則憂;勢有所難安,而患且相及也,則懼。此二者生于心,則欲有所為而不果,欲有所守而不固,外無以貞天下之動,而內使其心儳然如不終日。君子則萬事之條理秩然而不迷,不憂也;萬變之情形毅乎有以相治,不懼也;故立于民物之上,而不與流俗同其得失也。
司馬牛者,但知冥行不恤患難者之為小人,而疑不憂不懼之且與彼同情也,則曰:不憂不懼,忘身而不知險阻已耳,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子何易言不憂不懼哉!夫于可憂而不憂,于可懼而不懼,此亦何足論者!乃若君子,則于事幾之難,物情之變,深計而得所自命矣。君子曰,人之所可憂可懼者,于己有疚而宜得兇危者也。若處己也不疚于己,接物也不疚于人,則當變故至前,省之省之,而果有以自信矣。于此而猶有憂懼焉,夫何憂乎?無亦唯是得失之情,系乎利害而憂乎?夫何懼乎?無亦禍福之至,系乎死生而懼乎?而此豈足憂足懼乎!舍此而更有何可憂何可懼乎!有望道不見之深情,則盡之在我,而不于當世問從違毀譽,以求其兩全;有匹夫勝予之慮,則感之在我,而不與天下爭成敗利鈍,以期于幸免。夫然,故怡然自得而俟命于素位之中,挺然自持而立命于存亡之外,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斯!……如司馬牛憂兄弟之亡,豈是內省有疚使然?無疚而憂懼,是庸人為利害所搖一大病。故內省不疚后,還有不憂不懼一大學問。⑨
從上文來看,與傳統上將《論語》這一章中的“內省不疚”理解為“不憂不懼”的邏輯前提不同(譬如朱熹對這一章的解釋就是如此。朱子曰:“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⑩船山認為,孔子在此對司馬牛的教導并不是說疚就是憂懼的前提,只是因為心中有愧,所以才會憂慮恐懼,因此若心中無愧就沒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指出:內省無疚只是解決欲為君子的內在障礙。憂懼本身并不是純然內在的,人心對于外在事物的“期得相及”才是憂懼的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憂懼具有不可避免的外在性因素。因此,所謂“無疚”只是以內省來調整自身而直面這不可避免的外在之“憂懼”的心靈狀態,從“無疚”出發,我發現我所謂憂懼者不過是“得失利害”“生死禍福”“毀譽成敗”這些“有命”之事。因此,“不憂不懼”實際上是指不需要“憂懼”而非“忘憂忘懼”“無憂無懼”。在船山看來,這并非輕易可得之事。雖人可“不疚”,但若強行就依此而言“無憂無懼”,這顯然是一種自欺欺人了,反而會被外在的“憂懼”而搖動心靈。唯有內省不疚,直面自身對于外在的“憂懼”,方有可能真正不憂不懼。這也是為什么譚嗣同在前述引文中將船山此意比于《中庸》“戒慎恐懼”一語的因果所在。
若我們了解了上述思想背景,就會發現,譚嗣同所推崇的船山這一直面憂懼方能不憂不懼的說法,本質上就是一種學必征實、實事求是的人生態度,也體現了船山的實學傾向對于譚嗣同思想的深刻影響。從歷史上看,也許正是因為受到船山的這種直面恐懼憂慮的世界觀之影響。甲午戰敗后,譚嗣同從不避諱其對于西方文明強盛及其對明治維新之后使用西方制度的日本的恐懼,并對其自身早年盲目排外表示追悔。譚嗣同云:
即以炮論之,最大之克虜伯、阿模士莊能擊五六十里,而開花可洞鐵尺許者可使萬人同死于一炮。雖斷無萬人駢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是以推,彼不過發數萬炮,而我四百兆之黃種可以無噍類,猶謂氣與精誠足以敵之乎?B11
以今人的角度來看,上述譚嗣同對于克虜伯火炮威力的形容甚至已經不能用夸張來形容。而亦由此可見,其對于甲午后時局之悲觀程度也已至極,以至于認為可以阻止日本席卷中國的辦法唯有仰賴西方顧慮其在華的商業利益或能出面牽制。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譚嗣同能直面如此震恐之時局,因此與力主洋務但同時還極力要求扶持名教并在西方文明面前強調中華文化之優越性的湖湘前輩士大夫不同,他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是非常激烈而徹底的,而這顯然也構成了其要求全然徹底之變法的根本思想動機,這同時構成了近世第二代湖湘士大夫具有極大革命性的精神氣質。或云:
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于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夏耶?……中國不自變法,以求列于公法,使外人代為變之,則養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之民胥為白種之奴役,即胥化為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驅之海隅及窮谷寒瘠之區,任其凍餓。B12
從上述引文來看,譚嗣同面對當時之時局,顯然憂慮已極,認為若再不變法,華夏文明將淪為蝦夷、黑奴之屬,徹底為西方所奴役,而同時他又對其之士大夫面對西方依然“不知懼乎”的自欺欺人之心態痛心疾首。就此而言,譚嗣同或可謂后世魯迅所講的“直面慘淡人生之真的猛士”。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譚嗣同將上文船山“何憂何懼”之詮釋理解為“故以無可憂懼治憂懼,不如以憂懼治憂懼”,顯然也與其時自身的心靈體悟有關。所以正是在直面此種時勢與自身憂懼的前提下,他的變法才是徹底而絕對無所畏懼的。
恰如目睹明亡而隱居深山發奮著書的王船山一樣,譚嗣同在此實是將自身的負面情感化作了逆勢前進的思想與實踐之推動力。所以,他會如此激進,從思想邏輯上說,乃是其直面當時局勢的憂慮震恐所致,直面憂懼則無疚的心態所致,這也正對應了前文中船山所言之“以期于幸免”的心靈體驗。就此言,我們可以說,正是以船山思想氣質作為精神之基,才造就了譚嗣同在十九世紀末最為激進的革命者之形象——因為憂懼已極、所以方能不憂不懼而沖決一切之網羅束縛。而其“沖決網羅”之說,也正是體現其學術宗旨的哲學著作《仁學》一書的核心要義,同樣也可以看作是譚嗣同激進變法思想的理論依據。
二、隱見而已:船山實學世界觀對譚嗣同仁學思想的影響
單從《仁學》這本書的思想內容來看,譚嗣同的哲學立場基本是力圖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論與概念系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能夠涵蓋與接續當時西方自然科學并同時為其變法理論提供哲學依據的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仁”。所以,他在此書開頭的界說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
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也。B13
以“通”解仁算不得譚嗣同的創建,乃是宋明道學傳統中的常見的說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在這里使用了當時西方物理學中流行的“以太”(Ether 或Aether)概念來詮釋其所謂“仁”之“通”義。所謂“以太”,從詞源上看最初是一個古希臘哲學概念,原指上部大氣層。20世紀初,以太這一具有絕對力學性質的假設性概念隨著愛因斯坦提出的狹義相對論而終結。B14從這個意義上說,譚嗣同對于“仁”的界說,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說是基本沿襲了當時西方物理學對于傳遞力與電磁波之“以太”的定義,并進一步推展到其認為的所有與“傳遞”(通)有關的領域。并且與當時西方物理學對于“以太”作為基礎物質無有生滅的定義一樣,譚嗣同也如此定義其所謂之“仁”,或曰:
不生不滅,仁之體。B15
但與此同時,其所謂的這個不生不滅的作為世界的本質之仁之體的思想根源,除了來自于當時物理學的以太詮釋之外,又別有一出自船山易學的中國傳統哲學之思想淵源。譚嗣同云:
不生不滅有征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并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 本為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 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B16
從上述引文來看,譚嗣同首先以近代自然科學中的化學與天體物理學的世界觀來解釋他所理解的物質——盡管在現象上會聚散生滅但從根本上說乃是不生不滅的世界觀,就此言,譚嗣同基本秉持著近代科學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物質不滅之世界觀。同時,他又將當時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以太”作為“聲光電”等運動傳播的媒介這一認識,當作“以太”的根本屬性。這一無時不刻都必須存在的屬性(要不然任何信息、力都無法傳播),被他看作是世界運動變化的根本性質,也即“日新”,并以此將之與船山的易學思想混在一起,進而以后者的理論與概念對前者加以匡正與詮釋。譚嗣同云:
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則合兩電,兩則有正有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發焉。……期可謂仁之端也已!”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說必加精,明而益微。至“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無妄”之所以無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匕鬯而再則泥也,罔不由于動。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兇悔吝,貞夫動也。謂地不動,昧于歷算者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靜之與剛動異也。B17
這段引文的核心要義,實際上在于譚嗣同將西方唯物主義世界觀中的物質運動(自動)的觀點與傳統易學與儒家思想中的“天行健”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盛德”的思想結合起來,用以詮釋“仁”的概念與仁學宇宙觀。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中國傳統思想落腳點則是在船山易學中。換言之,他借用船山的易學思想,從宇宙論的角度將上述近代自然科學的世界觀納入到儒家傳統形而上學的思想框架之內,以最終完成其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哲學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譚嗣同的《仁學》可謂近現代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本融匯中西、別開生面的革命性著作。就此言,船山思想在譚嗣同這一本接續西學承接中學的哲學著作中乃是作為中國學術的代表而出現的。從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說,在借鑒船山以變法方面,譚嗣同對于船山思想的認識也比既往的湖湘士大夫要深入得多。譬如此間,譚嗣同在前述引文中所借用的關于“一卦十二爻,半隱半見”的說法,其實是船山在以“乾坤并建”為核心的易學宇宙論系統的形上邏輯架構之下所提出的對于《周易》卦爻的認識方法。此乃船山對宋明理學之易學傳統的革命性顛覆及其宇宙論的核心要義之所在,是中國哲學傳統上的革命性創建之一。具體言之,船山的“并建乾坤”之說,主要是基于《系辭》“乾坤其《易》之門”的說法。船山云:
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蕩之謂。《周易》之書,乾、坤并建以為首,易之體也;六十二卦錯綜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B18
首先,從上述“乾坤并建”的說法來看,在這一命題中,船山主要是說:《乾》《坤》兩卦要成各自之撰的必要條件是互相不能離開對方的。正如要定下某條規則與界限,就必須有界內與界外、合規與違規的正反兩面情況一樣,《乾》《坤》之撰如不能互相交互和合于對方,便不能真正地使其自身確立起來。因此,這也就意味著:當《乾》卦之撰顯,其德必隱隱地指向仍處于遮蔽狀態的《坤》卦,反之亦然。《乾》《坤》二象之顯隱變化是以《乾》《坤》在本體層面的永恒實體性作為擔保的。這也是船山所理解的“乾坤,其《易》之門耶”的意思,只有在此基礎上,六十二卦方能隨時或顯、形質各異地立于時空維度之中。因為在本質上說,其余六十二卦不過是合乾坤之陰陽十二爻在六個爻位上不同的排列組合而已。所以,以十二爻為鏡面對稱的話,一卦之顯(如《復》卦)必意味著其下隱藏著與其鏡面對稱的另一卦之隱(如與《復》卦鏡面對稱的就是《姤》卦)。船山云:
夫陽奇陰偶,相積而六。陽合于陰,陰體乃成;陰合于陽,陽體乃成。有體乃有撰。陽亦六也,陰亦六也。陰陽各六,而見于撰者半,居為德者半。合德、撰而陰陽之數十二,故《易》有十二,而位定于六者,撰可見,德不可見也。陰六陽六,陰陽十二,往來用半而不窮。其相雜者,極于《既濟》《未濟》;其相勝者,極于《復》《姤》《夬》《剝》;而其俱見于撰以為至純者,莫盛于《乾》《坤》。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B19
基于這種以《乾》《坤》兩卦十二爻相合作為基準的鏡面對稱作為《周易》其余六十二爻的參照之理論,船山給出了其在認識論上著名的顯隱原則,此即譚嗣同講的“一卦十二爻,半隱半見”的說法,對此,船山之說的原文是:
還歸其故曰“復”。一陽初生于積陰之下,而謂之復者,陰陽之撰各六,其位亦十有二,半隱半見,見者為明,而非忽有,隱者為幽,而非竟無,天道人事,無不皆然,體之充實,所謂誠也。十二位之陰陽,隱見各半,其發用者,皆其見而明者也。時所偶值,情所偶動,事所偶起,天運之循環,事物之往來,人心之應感,當其際而發見。B20
依照“乾坤并建”的原則,船山認為,卦爻的變化所導致的卦象改變,從本質上說只是一卦顯現而另一卦隱去的關系,并不存在一卦消滅于另一卦誕生的情況。從畫卦規則的形上角度來看,在《周易》中的每一卦有六爻而每一個爻位則有陰陽兩種情況,因此,卦爻變化在本質上說不過是其爻位上的十二陰陽爻之顯隱轉換。能被觀察到的爻是此卦的當下顯現出來與既成之狀態或卦象,而未被觀察到的則是依照這十二爻原則可能繼而顯現的卦象或已經顯現過的卦象。所以,在形上層面,陰陽十二爻本身實際可說是永恒不變的,此所謂天道之“誠”,而在形下層面,因為具體的實、情、事的變化,其則顯現為某一具體陰陽相合的六爻卦象并且昭示了隱藏其下的另半面卦象。就此而言,卦象的顯隱變化現象背后所依據的是出于本體層面的《乾》《坤》兩卦十二爻之永恒不變的實體性,此即船山易學之“乾坤并建”。
進而,從易學上的乾坤并建原則出發,船山構造了其“氣一元”與“氣化屈伸”的實體宇宙論學說。這也體現在船山對于譚嗣同在上文中所引用的張橫渠的“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的詮釋之中。船山云:
明有所以為明,幽有所以為幽;其在幽者,耳目見聞之力窮,而非理氣之本無也。老、莊之徒,于所不能見聞而決言之曰無,陋甚矣。《易》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大備而錯綜以成變化為體,故《乾》非無陰,陰處于幽也;《坤》非無陽,陽處于幽也;《剝》《復》之陽非少,《夬》《姤》之陰非微,幽以為缊,明以為表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坤》合于太和而富有日新之無所缺也。若周子之言無極者,言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不可名之為極,而實有太極,亦以明夫無所謂無,而人見為無者皆有也。屈伸者,非理氣之生滅也;自明而之幽為屈,自幽而之明為伸;運于兩間者恒伸,而成乎形色者有屈。B21
從船山的上述說法來看,由《周易》的“乾坤并建”原則出發,因為六陰六陽乃是永恒不變的,因此可以得出,道學宇宙論中的氣之屈伸從本質上說并非“理氣生滅”而是氣之幽明現隱的變化。這意味著,具體現實的事物的顯現是氣伸展的表現,而同樣其在現實中的消逝則可以說是其屈的結果(成乎形色者有屈)。所以,同易學上的“乾坤并建”對應,在船山的“氣一元”之宇宙論中,“陰陽二氣”乃是永恒而無有生滅的基礎性實體,換言之,“氣”作為船山宇宙論的核心概念的不生不滅的。
而這一點顯然被譚嗣同敏銳地意識到了,并以之用來涵攝當時由西方傳來的物理學中的“以太”概念。我們可以看到,“以太”與船山的“屈伸顯隱之氣”從概念定義上說是十分相似的,并且都是具有宇宙本源性質的形上學范疇。船山云:
陰陽之實,情才各異,故其致用,功效亦殊。若其以動靜、屈伸、聚散分陰陽為言者,又此陰陽二氣合而因時以效動,則陽之靜屈而散,亦謂之陰,陰之動伸而聚,亦謂之陽,假陰陽之象以名之爾,非氣本無陰陽,因動靜屈伸聚散而始有也。故直言氣有陰陽,以明太虛之中雖無形之可執,而溫肅、生殺、清濁之體性俱有于一氣之中,同為固有之實也。B22
上述引文中的“屈散動靜”與譚嗣同所理解的化學上的物質化合分散,宇宙學上星系誕生消亡之邏輯其實十分類似。所以,前文中譚嗣同所謂的“仁體”,其在思想淵源上不僅有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以太”概念,而且還有船山的“陰陽二氣之實”與“乾坤并建”思想。譚嗣同在《仁學》中創造性地結合這兩種中西思想當中完全異質的理論進路,并以此構造其自身以“仁”為核心的哲學系統。而搞清楚了譚嗣同《仁學》在哲學上的思想淵源與立論核心,我們才能追問下面這個問題:為什么在譚嗣同看來,依船山的“陰陽二氣之實”與西學之“以太”而構造起來的“仁體”有著“沖決網羅”的作用呢?
筆者認為,乃是因為從譚嗣同《仁學》中的詮釋來看,不論是船山的“陰陽二氣之實”“十二爻”還是“以太”,這些哲學概念都有如下共同特征:
其一,具有客觀性與實在性。
其二,在本體層面上說是不生不滅的,同時,除了交互性(運動性)外,其不再附帶任何先定的經驗性之屬性。
其三,其在人類現象經驗層面上可以因為時間、空間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千變萬化,但這其中的變化都是經驗的、而非先驗的或先定的。同時這些在人類現象經驗層面上的變化對其在本體層面的不生不滅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而根據譚嗣同自己的說法,《仁學》中的“沖決網羅”之說,其核心要義在于打破任何既成、先定的思想上的束縛。所以,他在《仁學》自敘中云: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故沖決網羅者,即是未嘗沖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為一,凡誦吾書,皆可于斯二語領之矣。B23
而由上述引文,參照其對于“以太”與“仁”以及“船山陰陽二實”的界定來看,他顯然認為任何先定目的與永恒屬性,都不應該存在于本體層面,如果它們存在,那么就將成為現象層面的網羅(阻礙)。換言之,除了客觀性、實在性與變易交互性(通)之外,譚嗣同的“仁體”別無其他。因此,不論是上承自橫渠的船山之乾坤十二爻顯隱認識原則,還是當時以“以太”為核心西方自然科學的世界觀,都強調在這個具有客觀實在性的世界的本體層面除了永恒與變易(交互、運動)之外,就不存在其他任何固定不變的先定之性了。
換言之,《仁學》本身的“沖決網羅”之說也最終會在時間之中失去價值而被沖決。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正因為網羅(價值、本質)的所具有的這種時間性與現象屬性(這意味著其一定是可朽易逝的),所以網羅才是有可能被沖決的,因為這并非本體層面的問題;反之,也正因為其可被沖決,也就表明這些網羅(價值、本質)本身不具有本體層面那種具有恒常性的價值。
譚嗣同用這樣一種看起來是循環論證的邏輯,表達了其哲學對于一切固有價值與思想的批判。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其在上述引文中所言之“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故沖決網羅者,即是未嘗沖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為一,凡誦吾書,皆可于斯二語領之矣”的思想內涵。
從西方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角度上說,這種在形上本體層面消滅先定本質、價值與目的之思想進路,顯然是自康德與牛頓以來,西方思想在自然界中取消了上帝作為造物主之地位的哲學結論有關。而從船山思想的角度來看,乾坤十二爻顯隱認識原則以及“陰陽二氣之實”的宇宙論思想,所批判的乃是以程朱理學為代表將“天理”作為先定本質、價值與目的的宋明道學之世界觀,而這一世界觀也是直至清末依然存在的,它是自兩漢以來古典中國社會綱常名教系統的形上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譚嗣同的哲學,在形式上盡管依然使用中國哲學的傳統范疇為核心(譬如“仁”),但其理論實質是使用西方哲學史上的認識論革命與近代自然科學之成果,并借助中國哲學的傳統資源,對程朱理學進行的批判。而船山思想在這一批判中起到了理論橋梁與紐帶的作用。換言之,船山之學使得譚嗣同可能在與程朱理學相同的一套中國話語系統中,使用西方的思想資源完成對于傳統道學以及綱常名教系統的批判,進而為其在政治上的變法改革,并使用西方制度與意識形態改造大清王朝打下哲學基礎。譚嗣同借用了船山思想中的道學批判的理論骨架,同時填充進了當時近代化的西方哲學與自然科學思想,這構成了其以西學變法維新的哲學基礎。
三、道不離器、知先于行:船山知行觀對于譚嗣同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
因為在本體層面并不存在先定的價值,所以譚嗣同認為,一切的價值屬性與原則(道),都是具體時空境遇下的結果(器)。譚嗣同曰:
陳伯嚴之言曰:“國亡久矣,士大夫猶冥然無知,動即引八股家言:天不變道亦不變。不知道尚安在,遑言變不變耶?”竊疑今人所謂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虛而已矣。故衡陽王子有“道不離器”之說,曰“無其器則無其道,無弓矢則無射之道,無車馬則無御之道,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則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實用,果非空漠無物之中有所謂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變之弊法,又經二千年之喪亂,為夷狄盜賊所羼雜者耳。于此猶自命為夏,詆人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變法者,器既變矣,道之且無者不能終無,道之可有者自須亟有也。B24
譚嗣同認為,現實情況決定抽象的價值屬性與原則。因此他用船山的“道不離器”“無其器則無其道”的原則表明,在當前的現實之下,被詆毀為“禽獸”的洋人才是先進的華夏,而自命為“華夏”的中國在當時的歐洲面前,其實已落后為“禽獸”。所謂“故不變法,即偏安割據亦萬萬無望;即令不乏揭竿斬木之輩,終必被洋人之槍炮一擊而空”,這就是晚清與前代器變之不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從“人心風俗,政治法度”上所進行的道變(變法)就是亟有之命題。但實際上,譚嗣同在這里是選擇性地使用了船山關于“道器”關系的說法,因為在這個問題上船山實際上是這樣說的:
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茍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人或昧與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無器也。
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弦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
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B25
從船山關于這個問題的原文來看,“道不離器”的說法實際上是說圣人制器而明道的意思,盡管其中有道隨器變的內涵,但從圣人制作的層面來說,道本身只是通過器來表達,道不離器固然是事實,但器不離道也是一樣。道器兩者是隨著時代一同變異進化的,并且圣人是因時而通過器來展現其道的。但其間恰恰存在一個譚嗣同所反對的圣人先定原則,因為在船山這里,其道器邏輯其實是說,弓箭是射箭之道的邏輯前提,車馬是駕車之道的邏輯前提,抽象的價值屬性與原則的產生必須依賴于現實具體之物的制作,但制作本身乃是依賴于圣人這一主體的,圣人是為了明道方才制器。從這個意義上說,也不能完全說船山的想法是器在道先或道在器先。若從這個意義上看,譚嗣同的變法思想實際誤用了船山的這一道器說。在筆者看來,若依船山的原則,譚嗣同所提倡的對于“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的變法,從當時晚清的現實來說是不存在具體的現實物質依托(器)的,因此戊戌變法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從船山哲學的層面上說是注定要失敗的。
譚嗣同的這種有意無意地對于船山思想的誤解實際上意味著:其變法思想盡管借助船山道學批判思想作為框架,并且與船山一樣反對程朱理學所倡導的那種永恒不變的先驗原則,但其中填充的具體內容卻是西方近代的革命思想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在解釋變法根據的時候,他盡管使用了船山的“道不離器、器不離道”方法,但其中的認識原則卻是“依道制器”或者“貴知賤行”的邏輯,這里面的視角是機械的而非辯證的。
因此,譚嗣同的哲學從根本上存在著方法論與世界觀上的雙重標準問題,即世界觀是物質性的與科學性的,但方法論卻是某種唯意志論的而非實踐的。這也是他將西學與船山強行扭合在一起產生的不諧之處的關鍵所在。
小結
相對于第一代湖湘士大夫的曾國藩、郭嵩燾等人,船山對譚嗣同的影響要更為近現代化。所謂近現代化也就是說,如果在曾國藩、郭嵩燾那里的船山之學還是以一種傳統中國學術之面貌出現的話,那么到了譚嗣同這里,船山就轉換了一套令人驚訝的近代化的思想面貌并掀起了一場明末所不曾有過的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就此而言,船山之學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的指導思想之一。也許是甲午戰敗后的大清王朝在時局上與甲申年之后的大明王朝有太多相似之處,因此,經由譚嗣同的解讀,兩百年前的船山思想在精神氣質、實學世界觀、宇宙論與變化日新的歷史觀上都非常契合于十九世紀末的大清王朝對于變革的要求,并表現出了后世所謂“啟蒙”的思想特質。而不論譚嗣同對船山思想的解讀是出于什么政治與思想目的,有一點我們都必須承認,那就是在船山思想的啟蒙性詮釋上,他是先行者。
【 注 釋 】
①②④⑤⑥⑧B11B12B13B15B16B17B23B24 譚嗣同:《譚嗣同集》,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242、1、83、83、152、152、237、239、313、313、328—329、341、312、174—179頁。
③筆者案:瓣即歐陽中鵠的號,取“瓣香薑齋”,敬仰薑齋(船山的號)之義。參閱,高田淳:《清末的王船山》,《船山學刊》1984年第2期。
⑦陳焱:《晚清以來百年王船山哲學與思想研究述評》,《船山學刊》2012年第4期。
⑨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七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88—689頁。
⑩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4頁。
B14馮一兵、李春密:《以太觀的歷史演變及啟示》,《物理通報》2010年第三期。
B18B19B20B25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1、1054、225、1028頁。
B21B2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272—273、80頁。
(編校:夏劍欽 余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