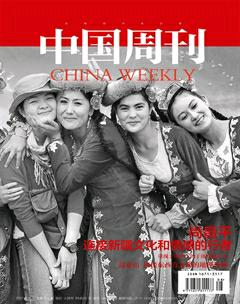以心相抵深深處
娟子
雖然生活在新疆,但我們的視野和行走都十分有限,對于許多地方、許多人群都未必能夠真正抵達,而正是那些地域和人群,有著令你難以想像的魔力,總是會借助著一種力量在你面前呈現出奇妙的光亮。
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到刀郎和刀郎老藝人,是在2004年冬天烏魯木齊下第一場雪之時,那是一次以文會友的隆重相聚,主題正是與刀郎有關的內容。深夜席散,當我們喝光了從南疆帶來的數桶穆塞萊斯,醺醺然走在這個城市初雪的街道,內心總覺得在燃著火焰。因為我們能夠聽到最原生態的音樂,喝到最原生態的美酒,可以說在那一晚已經遠離了城市的俗囿,墜入了曠野的狂放。
此后,那些身穿白布衣、盤腿席地的刀郎老藝人總會浮現在我的眼前,盡管那一晚我們在刀郎狂歌之中紛紛起舞,盡管我們把胸前的嘉賓鮮花都敬獻給老人們,盡管我們舞累之后就坐在老人們的腳邊繼續聆聽,但我們總是覺得,無法走進刀郎的世界,他們的內心。
每每打開尚昌平《刀郎》一書,我就會回想起初雪之際的那一幕,面對刀郎和刀郎音樂,我們許多人都有一種親近的渴望,卻又始終無法釋懷的焦灼。所幸,借助昌平在幾千年來刀郎之路上的巡行步履,我們得以更深入地親近這一古老綠洲之上的狂野樂舞。
《刀郎》一書中對于刀郎文化的淵源與延伸、傳承與表現都有著縝密的論述和詳實的敘述,這自然有賴于昌平對西域文化的思考,以及她在新疆地域上的數載奔波,以此才能夠厚積薄發,凝聚和升華出這一主題厚重大氣又生動鮮活的靈魂。
她在文中自述:“刀郎樂舞的本質是什么,一直懸系在我的心頭不得釋然,尤其是在我所經之處,無論耄耋老人,還是青春少年,無不推誠相與;或即景聯辭,或席地鼓琴,更令人感愧交并。”“村民在空曠的場地上迎風起舞,琴弦上跳出的音符像一顆顆長了尾巴的沙礫,在空中隨風旋轉,抽打在我的身上、臉上,那是一種帶著彈性的擊打,直至全身麻木,直至擊碎大腦中的一個問號——什么是刀郎?!”
什么是刀郎?對于每一個關注新疆地域和傳統文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有著無限內涵的問題。正如昌平在《刀郎》一書中的廣征博引,求證探述所得出的結論,刀郎涵蓋著民俗、社會、文化現象與民族精神氣質,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象征,存在于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
整本書中,令我偏愛的是昌平對于數位刀郎老人的考察和描述,從他們的身世、家庭和社會生活中,都可以透映出這樣一個簡單的主題——刀郎,就是一種生活態度。在刀郎人的生活中,喜作歌,樂作舞,悲作歌,怨作舞,所有的生活情緒都歸結進刀郎,所有的語言和感情都凝聚成刀郎。
在昌平走近的刀郎藝人中,卡龍琴樂師阿不吉力·肉孜,60歲那年為求得別家院內可做樂器的上好桑木,曾經三叩其門,最后以自己的毛驢交換終得實現所愿,用這株桑木做成了三件樂器,被譽為“一木三琴”;庫爾班·吐爾地·艾捷克這個艾捷克樂師,被人們在姓氏后面附以樂器名稱而尊崇,他在琴體的頂端嵌上了金屬制作的國徽圖案,是他改變了刀郎人口傳心授的傳藝方式,用文字方式協助恢復了幾近失散的刀郎木卡姆曲詞;因為生活困頓有過多次結婚史的吾斯曼·艾山,不懂得稼穡之艱,令他魂不守舍地只有一把從未給他帶來名利的刀郎熱瓦甫;還有兩位90歲高齡的刀郎老藝人沙得爾·沙依提和木沙·尼牙孜,他們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著對于刀郎的熱愛:“一個人一生可能會討幾個老婆,但他鐘愛的琴只能有一把”;而被稱為“刀郎雙星”的孿生兄弟艾山·牙牙和玉素因·牙牙,對生活的理解和表現雖然不同,卻對刀郎有著同樣濃烈的激情……這些老藝人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并不艱澀,簡單的可以歸結為一點——刀郎,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音符。
無論富足還是貧困,刀郎正是一種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我相信昌平所走近,也是我們所渴望親近的,對于她或者我們而言,并不能夠了解足夠深,抵達足夠遠,但只要能夠與這些老藝人相處,即便短暫,也會從他們生活中透映的光亮來達成自我的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