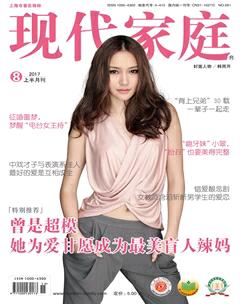過于精明,近乎猥瑣
許云倩
美國情景喜劇《老爸老媽浪漫史》中有一個情節,巴尼因為從小被父親拋棄,那些需要使用工具的活他一點都不會。家里的一個小零件掉了,他拿出100美金讓大樓管理員幫他擰個小螺絲,令他的朋友對他側目。我邊看邊想,這些活我從小都會。削個榫頭裝在墻上,再敲個釘子上去;電線插頭松了重新裝上之類的事,小時候常干。也是因為從小父親不在身邊,揉面做饅頭,登高換燈泡,繡花鉤絨線,啥都會些。成家后,自然分工,“動刀動槍”的活干得少了,偶爾為之,也還湊合。也許我還是傳統觀念:家,就應該是合作社,是互助組,是讓我們蕩起雙槳。
由“釘子”,我想到了蘇青說的那句名言:“連墻上的一顆釘子,都是我用自己的勞力換來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女性爭取平權也好幾十年了,但恐怕也未必喜歡完全顛倒過來。最近聽朋友說他表姐的感情故事,令我感嘆不已。女方男方都是離異,男方帶一兒子,女方攜一女兒。男方有三套房子,結果卻在女方家同居。他說是三套房子都給兒子了。女方的閨女去海外留學了,兩人世界倒也沒人打擾。女方比較大氣,日常開銷自然都是她來負擔,男方心安理得享受美好的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過節的時候,女方的父母到女兒家作客,女兒覺得菜準備得不夠,讓男朋友到周邊的大型超市去買些海鮮。男朋友出去兜了一圈,回來說,今天海鮮都賣完了。這下真把女方給惹惱了,她不信邪,從來還沒聽到過大型超市有海鮮賣完這一說,她親自去跑了一趟,拎了一袋海鮮回來,把男朋友趕跑了。之前她總覺得兩人感情還不錯,男人小氣些尚可容忍,但真到了這個份上,那就是有害了,還是遠離為好。
我的感慨在于,這個故事,太像另外一個故事了,連數字也一模一樣。幾年前,一個喪偶的女子找了我們都認識的同為喪偶的一個先生。那位先生在我們眼里一直是個文弱書生,其實也沒多深的了解。后來的信息都是從女方這邊來的,兩個人交往順利,很快結婚了。女方沒有子嗣,有一套自己住著的房子。男方有一子和三套房子。這就是我所說的數字相同:房產比例。然后結果也是類同,男的入住女方的房子。他有很好的理由:一套房子是給兒子的,絕對不能染指;一套在郊區,生活不方便;還有一套是在市區又是他之前住著的房子,還是不能用來結婚,因為有他去世妻子的骨灰盒。聽起來奇葩卻似乎很有道理。用骨灰盒來當作捍衛房產的神器也算是很有創新精神了。只要當事雙方能夠接受,旁人也難以置評。自然,婚后生活中,男人的種種摳門也不會比之前的精算更為令人稱奇了。我只想問:嫁給這樣的男人真的比獨身更好嗎?
還有一位前輩老先生,在老太太過世后,找到一位紅顏知己。倒不是人們想象的老少配,對方跟他年齡相差不大,是鶴發紅顏。老太太是從別的城市過來的,老先生給她在隔壁租了一間房子,租金自付。白天,他們在老太太屋里共話詩書;夜晚,老先生回自己屋子異床異夢。就這樣,他們以一種既非同居也非結婚的形式近距離生活。老先生既得到了精神世界的充實豐滿,又堅守捍衛了自己物質世界的堡壘,老而不昏,令人佩服。
不知什么時候,上海的某些男人變得這樣的精怪了。自己擁有的什么也不脫手,只想占盡別人的便宜。半路夫妻因為家庭是重新嫁接組合的,有些保留和戒備也可理解,但一味地守護自己的家園和財產,毫無羞恥感地生活在女人的羽翼之下,也真是讓人羨慕他們的理直氣壯。
我母親每年體檢都承蒙她同事及其丈夫的陪伴和關照。那位老伯總是細心為兩位老太太帶路拿包,在她倆驗血后又及時送來早餐。母親告訴我,他倆其實是一對再婚夫婦,但是他們兩人及他們各自的子女都相處和睦,外人看來與原生家庭無異。其實這也沒什么特別的訣竅,就是大家多為對方著想,別總是打自己的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