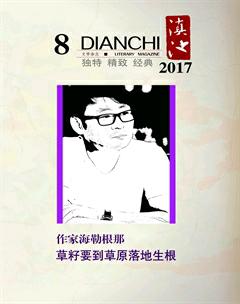草籽要到草原落地生根(創作談)
海勒根那
作為一個短篇小說的制造者,單就工齡來說我也勉強稱得上“資深”老工匠了。
二十多年前,二十歲的我在《草原》上發表第一篇小說《狗娘養的狐》時,責編谷豐登先生在編者按中寫道:……一個毛頭小子竟然能寫出如此雄渾大氣的作品,為此我們編輯部特意給作者的所在單位打了電話,核實了情況,證明小說確是出自他手……最后老先生為內蒙古文壇發現了我這個“毛頭小子”表達了激動,并對我寄予了殷殷厚望。時隔多年,今天的我應《滇池》之約寫下這篇創作談時,一種時過境遷的滄桑感浮掠心頭,當年那個誤打誤撞闖進文學的“愣頭青”已然辜負了谷先生的期望,僅聊以安慰的是,我對于文學的虔誠癡心未改,二十幾年來還在馬拉松式的跑道上踽踽而行,無論烈日炎炎或暴風驟雨。
若要梳理一番自己的創作,就要先梳理一下自己這半生的生活,因為這些小說故事都源于我的三個半故鄉——內蒙古蒙漢雜居的科爾沁、大東北城鄉、游牧的呼倫貝爾,和使鹿鄂溫克、狩獵鄂倫春人棲息的大興安嶺,前三個是我真正生活過的地方,而后者只是我為探知蒙古祖地時常主動接近那里,權作半個心靈家園。
那個遙遠的科爾沁哲里木盟,曾經是清代著名的孝莊皇后、大將軍曾格林沁的故土,清末民初,大量漢民涌入,王公放墾,匪盜橫生,張作霖等軍閥一度把昔日的豐美草原當做了軍備糧倉,民族英雄嘎達梅林奮起保衛蒙古人的家園,最終戰死沙場……小時候我就是聽著這些科爾沁的故事懵懵懂懂長大。等我記事時,家鄉已是荒沙漫漫的沙坨子和一望無際的苞米地。而我的村莊除了為數不多的老人還偶爾操持蒙語,基本都成了平卷舌不分的遼寧口音的漢人。村莊的生產隊長不是姓王就是姓張,在農村土地包產到戶之前天天用大喇叭呼喊著社員下地種田。《苞米,苞米》的故事在那時的鄉村里俯拾即是,翻著死魚眼睛的崽子都是地主富農家的孩子。有一天公社傳來為他們平反的消息,所有貧下中農都哭了:“憑什么給他們平反,不吃(恥)人類的臭狗屎們,以后我們還怎么活?”可是不久,讓“臭狗屎們”歡天喜地的事情接踵而至,以至于屬于貧農的優越感徹底沒有了,再不能隨隨便便把他們綁起來游街,讓他們撅腚在田間給廣大社員解悶,直到許多年之后,他們又翻身做了“地主富農”,而貧農依舊還是貧農。當然,這個村莊與中國更多的鄉村一樣,有悲有喜,有聲有色,我寫的很多鄉村故事都源于這里。
可少年的我命運多舛,五歲喪父,十歲時母親撒手人寰,我不得不隨同兩個早已出嫁的姐姐遷徙到科爾沁腹地,那里的村莊與我出生的漢地一樣遍野黃沙,可不同的是,村民不僅嚼著沙子種地,還在沙地里尋找草根放牧牛羊,而且他們的話語滴里嘟嚕,這些語言我似曾相識——在父母親的嘴里聽說過,卻一句不懂。他們以牛奶制品和炒米、蕎面為主食,滿街飄蕩著牲畜的膻味和釘馬掌發出的叮叮當當。牧業生產隊里,春天的人們在忙著劁牛騸馬,幾個皮匠正將熟好的牛皮制成牛馬具掛滿墻壁。夜晚,全村人擁擠到一個破落昏暗的黃泥土屋里聽瞎眼睛老頭彈著胡琴說唱烏力古爾(古書)……這一切使我感到陌生而新奇。那順烏力塔的姐夫把我領到小學校面見校長,校長用蒙語問了我 1+2等于幾,我知道等于 3可我聽不懂他的語言,校長瞪了瞪眼睛:“意樂根家系(漢人家伙)!”姐夫解釋說:“比歇比歇,嗯巴蒙古倫渾(不是不是,這也是蒙古族)。”校長大手一擺,姐夫只好又領我回來,趕上一輛馬車送我到漢地去讀書。從此我便年年像候鳥那樣在科爾沁農、牧區兩地飛來飛去:到出生地附近的公社小學讀書,寒暑假再回那個叫“駱駝昌”的蒙古村落。這個異鄉村落給我的不僅僅是養育,我感恩它在于——它在我少年的時候便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讓我驚奇地認識到,世界上的村莊并非一樣:說著完全不同語言的人,他們的習俗千差萬別,情感表達大相徑庭,而生活卻同樣豐富多彩。我后來寫的很多科爾沁蒙地小說——《到哪兒去,黑馬》《羊圈里的弟弟》《駱駝香脂》等都是出自那里。
十八歲后,初中畢業的我不想安分守己在村莊務農,一天早上背起行囊告別養我長大的姐姐去東北打工,我身無分文只有一身臭力氣,就憑著一雙黃膠鞋走過了許多東北城鎮,做過很多苦力和最底層的工種。一次最強的勞動是,我和兩個工友兩小時卸下 50噸火車皮的水泥,回去還要騎行十公里的自行車,結果路遇瓢潑大雨,筋疲力盡渾身熱汗的我被冷雨淋透,一時感冒高燒,不知怎么爬回的居住地……這個包羅萬象的大東北被我視為第二故鄉,它教會了最底線的生存法則: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當然也有淳樸憨
直和行俠仗義。辛勞之余,我聽到不同的工友講的不同的民間故事,主角多為土匪、盜賊、妓女,和淘金者,那些“人為財死”、“底層宿命”、“男盜女娼”、“快意恩仇”照亮的是蕪雜人性和人生百態。而我更被那些東北硬漢的精神所吸引,后來寫下了《賭客》《血灑巴河寨》《十七顆彈片》《天狗種月亮》等一批東北小說,并以此起家開始了寫作生涯。
轉眼二十五歲。那年我突發奇想,為了改變一文不名的境遇一路向北來到了呼倫貝爾,“草籽還是要到草原落葉生根”——如我所愿,海拉爾這個游牧業包圍的小城著實養人,我在一家店鋪里租了兩節柜臺做起小買賣,沒想到生意順風順水,只短短幾年便使命運扭轉。這里最接近蒙古祖地,出城就是遼闊的草原和條條大河,牛羊成群,蒙古包簇簇,而游牧人自由自在于馬背上馳騁……一種血脈的尋根,一種民族情感的蘇醒,一種文化認同的溯源,讓我深深沉醉在這片沃土高原。這使我想起了貧瘠的科爾沁,我那黃沙遍野的故鄉何曾不是這般“風吹草地顯牛羊”的模樣,可曾幾何時,它被異化了、荒蕪了、丟失了……而我自己就像科爾沁故鄉一樣,是被蒙古母親丟失的孩子……我滿含熱淚寫下詩句:
第一次聽到長調
聽到九曲回腸的蒙古民歌
我就知道我的血液屬于這浩蕩奔淌的河流
而我的心靈屬于這奪人魂魄的音韻
語言也隔離不了血脈呀
丟失多年的兒子
總能一眼認出母親
第一次聽見你的呼喚啊
我低下頭來無聲地哭了
……
在呼倫貝爾,二十載時光如一日,我不再勤奮地寫作小說,而是如醉如癡地去往草原深處,飲酒作詩,采風牧羊,我就像一匹撒歡的野馬四處奔跑,心靈從未如此釋放,如此寬闊。然而,呼倫貝爾也絕非世外桃源,洪流之下無凈土,當它豐厚無比的地下礦藏被人類發現,它的安詳與寧靜的神話也終將被打破……而一個比牧草還弱小的詩人能為它做些什么呢?只有眼睜睜看著它被工業的屠刀切割,被挖礦的巨鏟蹂躪……而我只能用一支軟弱無力的筆去書寫草原最后的寓言,祈愿長生天睜開慧眼,不要再將呼倫貝爾變成另一個科爾沁……我寫作《尋找巴根那》,寫作《伯父特木熱的墓地》,寫作《騎手嘎達斯》,都是源自內心的眼淚。
呼倫貝爾境內的另一片寶藏便是大興安嶺,卻在十幾年前終于被開發殆盡,政府開始號召放下油鋸封山育林。可是原始山林并非原住民砍伐光的,野生動物也并非他們捕獵沒的,這個道理人人皆知卻沒處可講……使鹿鄂溫克人下山了,狩獵鄂倫春人交出了獵槍改為農民。一切都歸罪于時代的變遷,又一個獨特群體需要改變原有的生產生活,與農耕民族大一統了……
如今的使鹿人和狩獵人后代沒幾個會講自己的語言,一張嘴就是東北方言捎帶臟話,民族傳統和獨有文化蕩然無存。《把我送到樹上去》的別佳,在真實生活中沒“操”字不張口,可他面對現實的苦悶與無奈又能向誰傾訴?還有《鹿哨》里的丘克,《父親狩獵歸來》里的父親,《六叉犄角公鹿》里的吉若(我的其他幾篇森林小說主人公),他們都本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卻被現實的重拳打敗了……
以上就是我的三個半故鄉,我的三個半母親。是她們用多姿多彩的現實世界賦予了我波瀾蕩漾的生活,和無盡的文學滋養。作為一個小說制造者,我能做到的只是盡我所能,在這大海中掬幾瓢水制成拙作。如果說這些故事還能讓讀者耐下性子讀完的話,那還要感謝我的師傅。每一個工匠都有自己的師傅,寫作者也不例外。為此我把幾個頂頂重要的名字寫下來,以示敬意,他們是: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胡安·魯爾福、巴別爾;大名鼎鼎無人不知的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夫卡,還有中國的余華,以及名不見經傳的東北作家劉國民。
責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