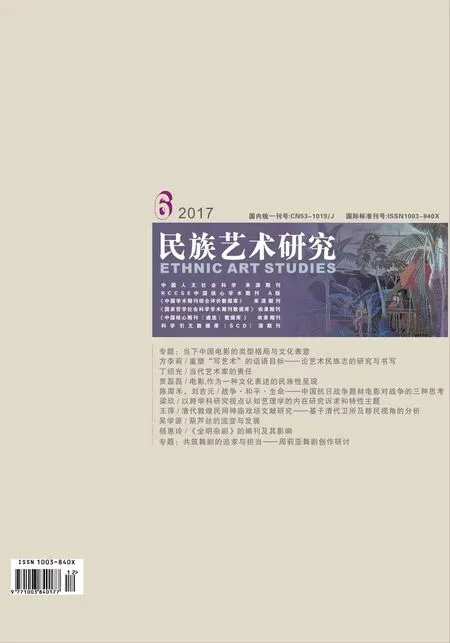跨類(lèi)型、超類(lèi)型與反類(lèi)型:當(dāng)下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的類(lèi)型發(fā)展態(tài)勢(shì)
楊林玉
跨類(lèi)型、超類(lèi)型與反類(lèi)型:當(dāng)下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的類(lèi)型發(fā)展態(tài)勢(shì)
楊林玉
在一個(gè)年輕觀眾占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的時(shí)代,“青春”作為一種類(lèi)型思維被廣泛采納,幾乎所有類(lèi)型電影都試圖在各自的框架內(nèi)與“青春”對(duì)話。作為類(lèi)型的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尚處在形成之中,它廣泛借鑒其他類(lèi)型的表現(xiàn)手法,試圖勾連觀眾以往的類(lèi)型觀影經(jīng)驗(yàn),努力溢出“青春”的拘囿,進(jìn)入主流文化的界域。得益于年輕觀眾對(duì)類(lèi)型創(chuàng)新的包容度較強(qiáng),青春片成為跨類(lèi)型實(shí)驗(yàn)的演練場(chǎng),近年來(lái)國(guó)產(chǎn)青春亞類(lèi)型十分活躍,這類(lèi)影片尚未形成類(lèi)型成規(guī),還有長(zhǎng)足的類(lèi)型發(fā)展空間。相比美國(guó)青春片經(jīng)歷了半個(gè)世紀(jì)的發(fā)展,已走過(guò)了效仿其他類(lèi)型以及自我復(fù)制的歷程,轉(zhuǎn)而向有深度的超類(lèi)型青春片邁進(jìn),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在迅速走過(guò)了短平快的發(fā)展階段后,也開(kāi)始嘗試深度模式,出現(xiàn)了一批較有代表性的、具有超類(lèi)型與反類(lèi)型特質(zhì)的青春片。
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跨類(lèi)型;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元青春
青春電影是一種含義豐富的所指,可以包容許多差異性大的電影類(lèi)別。從大的方面說(shuō),電影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以青年人的審美趣味為絕對(duì)主導(dǎo)的文化,根據(jù)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研究中心與藝恩咨詢合作的調(diào)查,“從讀大學(xué)到畢業(yè)工作10年的青年是目前觀影的主流群體”[1]。幾乎當(dāng)下所有的電影都在潛意識(shí)中預(yù)設(shè)了青年觀影者作為主體受眾,也在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尋求向年輕人的思維方式、價(jià)值觀靠攏。2016年中國(guó)電影觀眾的平均年齡已低至21.6歲[2],觀影群體低齡化深深影響了電影的創(chuàng)作取向。隨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暴發(fā)式增長(zhǎng),告別了物質(zhì)匱乏的青春個(gè)體似乎“能夠?yàn)樗麨椋ㄒ坏膯?wèn)題是我們想要什么”[3](P157)。近年來(lái)出現(xiàn)了一股書(shū)寫(xiě)青春、消費(fèi)青春的熱潮,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青春片承擔(dān)了“制造訴求”,并引導(dǎo)其象征性地獲得滿足的功能。相比有形的制度性規(guī)束,當(dāng)下青春片更多地受制于消費(fèi)市場(chǎng),部分口碑不高的青春片照樣票房大熱,其背后是相對(duì)缺乏觀影經(jīng)驗(yàn)的、數(shù)量龐大的低齡觀眾的支持。近年來(lái)中國(guó)的觀影人群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新的變化,隨著商業(yè)地產(chǎn)下沉至三線四線五線城市,“小鎮(zhèn)青年”日益成為觀影主體。類(lèi)型片講究與觀眾的互動(dòng),國(guó)產(chǎn)青春片也在努力迎合這部分新興的、龐大的觀影人群的口味,這反過(guò)來(lái)影響了國(guó)產(chǎn)青春片的類(lèi)型發(fā)展。
一、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的語(yǔ)境
(一)青春電影與青春片
當(dāng)下中國(guó)的社會(huì)情境是:一方面年輕人“喊老”;另一方面在網(wǎng)絡(luò)文化的熏染下,“賣(mài)萌”“裝嫩”等網(wǎng)絡(luò)通行法寶被各年齡段的人使用,似乎全民皆“青春”。“青春”泛化為一種全社會(huì)共享的話語(yǔ)資源,與之相應(yīng)的是本應(yīng)承載青年文化的青春電影自身的界域也在不斷擴(kuò)張,它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主流文化,它的敘事修辭也有被主流文化效仿的趨勢(shì)。在一個(gè)泛青春化的電影語(yǔ)境下談青春電影,首要的一個(gè)問(wèn)題是如何界定青春電影。現(xiàn)有的研究?jī)A向于以題材和受眾來(lái)界定青春電影,即青春電影是指瞄準(zhǔn)年輕觀眾、表現(xiàn)年輕人生活(包括成長(zhǎng)經(jīng)歷、情感體驗(yàn)等方面)的影片。青春片則一般是指青春電影在與觀眾互動(dòng)的過(guò)程中發(fā)展出來(lái)的商業(yè)電影類(lèi)型,有相對(duì)穩(wěn)定的類(lèi)型設(shè)置。
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青春題材影片并不必然涵蓋了青春片。比如一些研究也將帶有奇幻、動(dòng)漫等非現(xiàn)實(shí)因子的影片歸在青春片名下,如《暮光之城》(2008-2012)、《你的名字》(2016)等。其次,青春題材影片也并不必然就是青春電影,如20世紀(jì)80年代大陸青年題材影片就更多承載著反思?xì)v史、探討現(xiàn)代性等宏大命題,并不太注重摸索年輕觀眾的審美趣味。青春電影的核心母題是成長(zhǎng),或有可識(shí)別的成長(zhǎng)儀式,或表現(xiàn)漸變式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或表現(xiàn)個(gè)體對(duì)局限/壁壘的體驗(yàn)。可以說(shuō),對(duì)“成長(zhǎng)”的關(guān)注是識(shí)別一部影片是否屬于“青春電影”序列的一個(gè)關(guān)鍵因素。
作為類(lèi)型的青春片是觀眾與電影工業(yè)合謀的產(chǎn)物。從美國(guó)青春片發(fā)展的歷史看,青春片自成一種類(lèi)型,恰恰始自20世紀(jì)50年代電影業(yè)衰頹之際,當(dāng)制片商發(fā)現(xiàn)他們投入的巨額廣告只能將青少年從電視機(jī)前拉回到影院時(shí),專(zhuān)門(mén)針對(duì)青少年觀眾的青春片開(kāi)始涌現(xiàn)。同樣,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形成類(lèi)型的前提是消費(fèi)“青春”的群體日益龐大,隨著近幾年二三線以下城市院線數(shù)量井噴而涌現(xiàn)的“小鎮(zhèn)青年”日益成為不容忽視的電影主導(dǎo)力量。與此同時(shí),電影的平民化時(shí)代給年輕的新晉導(dǎo)演提供了機(jī)會(huì),這些導(dǎo)演往往傾向于以拍攝自我的青春作為起步。當(dāng)下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日益形成一個(gè)龐雜的體系,包容了各種差異性的風(fēng)格與敘事。從廣義上來(lái)說(shuō),“青春”已成為一種電影的制作思維。在“青春”的電影思維影響下,其他類(lèi)型片也在向“青春片”靠攏,“成長(zhǎng)”的內(nèi)核灌鑄在越來(lái)越多的類(lèi)型片中,突破了其原類(lèi)型思維中符號(hào)化的角色限定;在敘事手法上,各類(lèi)型影片也在試圖與“青春”搭界,衍生出諸多經(jīng)過(guò)一番“青春化”改造的亞類(lèi)型。
(二)“元青春”與作為類(lèi)型元素的“青春”
“青春電影”是一種覆蓋面很廣的大類(lèi)別,可以這樣說(shuō),當(dāng)下的武俠電影、驚悚/犯罪片、玄幻片、喜劇片、愛(ài)情片等大多帶有“青春電影”的思維方式,顯現(xiàn)出“青春”的肌理紋路。另一方面,當(dāng)下國(guó)產(chǎn)青春片處在一種類(lèi)型格局的建構(gòu)過(guò)程中,也在與各種類(lèi)型電影展開(kāi)對(duì)話,它們立足于成長(zhǎng)敘事、對(duì)其他類(lèi)型片的敘事手法兼收并蓄,這種亞類(lèi)型青春片越來(lái)越成為市場(chǎng)主流;相反,元青春,或曰青春本位的青春片,在經(jīng)歷了以《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小時(shí)代》等驟然出現(xiàn)的“消費(fèi)青春”高潮之后,有向小眾化的、自傳式的藝術(shù)青春電影發(fā)展的趨勢(shì),一如20世紀(jì)90年代密集出現(xiàn)的第六代導(dǎo)演的早期作品,只不過(guò)90年代第六代導(dǎo)演的青春電影往往固執(zhí)地將非常態(tài)的、邊緣的人物常態(tài)化,而近年來(lái)的元青春片則聚焦于平凡個(gè)體(也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青春體驗(yàn),如《少女哪吒》(2014)、《我的青春期》(2015)、《八月》(2016)等。本文所稱(chēng)的元青春片是一個(gè)很狹小的概念,特指以青春為表現(xiàn)對(duì)象的電影,是“關(guān)于青春的青春再現(xiàn)”[4],而當(dāng)下數(shù)量龐雜的青春片更多是元青春與其他類(lèi)型(同樣處在變異當(dāng)中)拼貼的產(chǎn)物。
正如文化歷史學(xué)家約翰·G·卡維爾蒂所說(shuō),“舊類(lèi)型片體系已經(jīng)‘耗盡生命’”[5](P210)。類(lèi)型的黃金時(shí)代關(guān)聯(lián)著從前的大制片場(chǎng)制度以及相應(yīng)的觀影文化,一種類(lèi)型往往能暢銷(xiāo)十幾二十年,然后觀眾才會(huì)感覺(jué)乏味。在當(dāng)今社會(huì)日新月異變化的時(shí)代,各類(lèi)型大抵只能各領(lǐng)風(fēng)騷三五載。比如,近年來(lái)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因其“以小博大”在商業(yè)上的成功迅速引發(fā)了一股跟風(fēng)炒作潮,其模式化的情節(jié)套路、人物形象、場(chǎng)景設(shè)置、懷舊風(fēng)格等一度風(fēng)行,亦速銷(xiāo)速朽。類(lèi)型必須時(shí)時(shí)保持著年輕與活力,才不致被市場(chǎng)淘汰;元青春片自身也必須努力更新,才能延續(xù)其生命力。可以說(shuō),“青春”已成為一種電影制作者必須保持的狀態(tài)。在一個(gè)“青春饑渴”已成為時(shí)代癥候的當(dāng)下,“青春”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電影通用的暢銷(xiāo)元素。經(jīng)由“青春”這一秘而不宣的中介,類(lèi)型片與熟諳“青春”的年輕觀眾之間架設(shè)起溝通的橋梁。
二、跨類(lèi)型——國(guó)產(chǎn)青春片的類(lèi)型嫁接
在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類(lèi)型化的大潮中,涌現(xiàn)出了幾類(lèi)初具類(lèi)型雛形的青春片,這些青春片往往立足于廣泛的社會(huì)語(yǔ)境、關(guān)注當(dāng)下的社會(huì)熱點(diǎn)、回應(yīng)大眾的情感需求,而不僅僅是單純的青春敘事。相應(yīng)地,這些青春片亦不同于《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guò)的女孩》《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這些類(lèi)型訴求純粹的“元青春片”,而是雜糅各種類(lèi)型元素,積極地拓展“青春”的能指,將“青春”演繹為一種與年齡關(guān)涉不大的、生命常新的狀態(tài),盡最大限度地勾連不同代際、不同品味觀眾的生存體驗(yàn),尤其迎合底層文化的樂(lè)天知命。這些跨類(lèi)型的青春亞類(lèi)型在人物角色設(shè)定、沖突設(shè)置、價(jià)值取向等方面具有較大的靈活度,它既可以挪用其他類(lèi)型片的敘事陳規(guī),又可在其中展開(kāi)對(duì)類(lèi)型陳規(guī)的改造、顛覆。青春片的觀眾吐故納新的能力較強(qiáng),對(duì)類(lèi)型實(shí)驗(yàn)有較強(qiáng)的包容性,因而青春片在很大程度上充當(dāng)了類(lèi)型實(shí)驗(yàn)的演練場(chǎng),新的亞類(lèi)型源源不斷地被嘗試創(chuàng)造。目前國(guó)產(chǎn)青春片跨類(lèi)型的主要有青春+犯罪片、青春+勵(lì)志片、青春+喜劇片、青春+愛(ài)情片、青春+公路片等幾種模式。這些亞類(lèi)型青春片往往以青春片加某種類(lèi)型為主要框架,雜糅了其他類(lèi)型,它們彼此之間亦有交集。
(一)青春+犯罪片
犯罪片在港臺(tái)地區(qū)有著悠久的類(lèi)型傳統(tǒng),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以來(lái),犯罪片更是被灌注了鮮明的青年文化因子。銀幕上的暴力犯罪更多地承載了年輕一代對(duì)社會(huì)象征體系壓制之反抗,而銀幕上的犯罪分子實(shí)質(zhì)上成了這個(gè)社會(huì)中某些無(wú)法解決的癥結(jié)、某些潛在沖突的爆發(fā)點(diǎn),如香港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大熱的“古惑仔”系列黑幫青春片,將青春時(shí)尚的元素注入古老的黑社會(huì)片中,試圖將黑社會(huì)描述為“合理性存在”的社團(tuán)組織、為其“正名”,其風(fēng)靡的背后是香港年輕人的焦慮和現(xiàn)實(shí)困境,正是在“社團(tuán)”這種灰色組織中,年輕人得以擺脫重荷、“活出真我”。新世紀(jì)以來(lái)青春犯罪片承載的反抗性弱化,暴力犯罪的消費(fèi)屬性被進(jìn)一步開(kāi)發(fā)出來(lái),以滿足人們的窺奇娛樂(lè)心理,比如新世紀(jì)初持續(xù)大熱的港片《新扎師妹》系列(2002至2007年出品了4部)中,警匪的沖突轉(zhuǎn)換為兩性的追逐,在雙方彼此的沖突、誤認(rèn)中制造一連串的喜劇效果。近年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亞類(lèi)型中特征最鮮明的就是這類(lèi)青春加犯罪(黑幫)片,典型的如臺(tái)灣地區(qū)出品的《一頁(yè)臺(tái)北》(2010)、《甜蜜殺機(jī)》(2014)等,在青春片中嵌套了犯罪片的敘事框架,在展開(kāi)犯罪敘事的同時(shí),以喜劇的手法解構(gòu)了傳統(tǒng)犯罪片的設(shè)定,兇神惡煞的犯罪分子被塑造成多情心軟的小男人,犯罪/破案得逞往往是陰差陽(yáng)錯(cuò),而不是精心密謀的結(jié)果。“黑色青春”奇觀化、喜劇化最成功的是2010年的《艋舺》,影片將青春故事架設(shè)在黑幫片的語(yǔ)境中,對(duì)黑幫械斗進(jìn)行了鬧劇化的處理,既沿襲了傳統(tǒng)黑幫片的敘事修辭,然而也顛覆了傳統(tǒng)黑幫片的倫理設(shè)定。主人公想象中的義薄云天的古典江湖其實(shí)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充滿人間煙火氣、充滿爾虞我詐以及權(quán)力爭(zhēng)斗的現(xiàn)代江湖。
2016年口碑與票房俱佳的《火鍋英雄》,則將這一類(lèi)型的發(fā)展推到一個(gè)新的高度。影片在一個(gè)犯罪片的框架內(nèi)展開(kāi)與青春片的對(duì)話,接續(xù)了前幾年青春片的懷舊敘事,亦顛覆了傳統(tǒng)犯罪片的人物設(shè)定,其中起案、破案的過(guò)程完全陰差陽(yáng)錯(cuò),主人公甚至因禍得福,一舉脫離了積重難返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得以從頭開(kāi)始。影片的反面人物設(shè)置給人極大的差異感,四個(gè)窮兇極惡的歹徒是白面少年,三個(gè)游走在江湖邊緣的浪子則在緊要關(guān)頭正義感“爆棚”——青春已逝的他們被“青春”救贖。“犯罪”釋放了違禁的沖動(dòng),而“青春”則成為一味靈丹妙藥,為時(shí)下飽受高房?jī)r(jià)、人際關(guān)系冷漠以及事業(yè)瓶頸困擾的年輕人提供了想象性的解決之道。
(二)青春+勵(lì)志片
新世紀(jì)以來(lái)青春電影中的反抗性弱化,填充它的是諸如夢(mèng)想之類(lèi)的可被消費(fèi)社會(huì)開(kāi)發(fā)的所指。在近年來(lái)的《11度青春之老男孩》(2010)、《中國(guó)合伙人》(2013)、《我是路人甲》(2013)等勵(lì)志類(lèi)青春電影中,主人公反抗社會(huì)無(wú)形之網(wǎng)對(duì)其實(shí)現(xiàn)自我的鉗制,拒絕平庸、卑微的現(xiàn)狀,是以其將全部能量投入資本主義體系嘉許的渠道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夢(mèng)想承擔(dān)了引導(dǎo)青年消耗過(guò)剩能量的功能。這類(lèi)青春勵(lì)志片致力于建立一種對(duì)“奮斗”的認(rèn)同,影片展現(xiàn)奮斗者所逢遇的挫折是對(duì)現(xiàn)存體制/社會(huì)的批判,然而最終的逆襲故事又成為主流對(duì)奮斗者實(shí)施的表彰。新舊時(shí)代的轉(zhuǎn)換(褒揚(yáng)前者、否定后者),或小圈子/大社群的轉(zhuǎn)換,是這類(lèi)影片實(shí)現(xiàn)主流合理化表述的常見(jiàn)策略,以主流對(duì)奮斗者的最終認(rèn)同抵消了社會(huì)對(duì)于個(gè)體發(fā)展的禁錮。
港臺(tái)青春勵(lì)志片大多是運(yùn)動(dòng)或才藝題材,如《聽(tīng)說(shuō)》(2009)、《翻滾吧,阿信》(2011)、《逆光飛翔》(2012)、《狂舞派》(2013)、《志氣》(2013)、《破風(fēng)》(2015)等,這類(lèi)影片的敘事重心是主人公在奮斗過(guò)程中經(jīng)歷的重重考驗(yàn),尤其是友情、愛(ài)情的考驗(yàn),以其在競(jìng)技活動(dòng)中的最終獲獎(jiǎng)作為結(jié)局,友情、愛(ài)情與事業(yè)的沖突以及主人公的抉擇往往暗示著主人公的成長(zhǎng)。青春勵(lì)志片中的友情通常比愛(ài)情更具份量,如同愛(ài)情與事業(yè)沖突的現(xiàn)代愛(ài)情敘事,青春勵(lì)志片中事業(yè)往往成為友情的障礙。
相比臺(tái)灣地區(qū)比較推崇個(gè)人奮斗的這類(lèi)勵(lì)志傳奇題材,大陸地區(qū)對(duì)于勵(lì)志的講述往往要升格至集體、國(guó)族的層面。如2013年的熱門(mén)影片《中國(guó)合伙人》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關(guān)于中國(guó)夢(mèng)的族群式故事。《中國(guó)合伙人》在改革大潮的背景下,進(jìn)行一種底層逆襲的敘事。逆襲表現(xiàn)在兩個(gè)層面:其一是主人公作為個(gè)體從底層農(nóng)村,經(jīng)個(gè)人奮斗實(shí)現(xiàn)了人生進(jìn)階,其起起落落的人生堪稱(chēng)傳奇;其二是國(guó)家層面的勵(lì)志,作為在國(guó)際上被小覷的弱等民族經(jīng)過(guò)30年改革的磨礪,終于在國(guó)際舞臺(tái)獲得重視,發(fā)揮出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影片中的“成功”主要體現(xiàn)為個(gè)人對(duì)加諸自身發(fā)展之界限的突破,這亦是一種成長(zhǎng)的命題。
(三)青春+喜劇片
作為當(dāng)下最重要的類(lèi)型之一,喜劇片的類(lèi)型思維如同青春片一樣,幾乎滲透到所有類(lèi)型電影中,因而青春喜劇片是一種邊界很模糊的亞類(lèi)型,它與愛(ài)情喜劇、勵(lì)志喜劇等喜劇亞類(lèi)型以及青春愛(ài)情片、青春勵(lì)志片等青春片亞類(lèi)型皆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近年來(lái)大陸青春片中的勵(lì)志故事更多是喜劇性的、自我解構(gòu)的,迎合當(dāng)下盛行的屌絲文化,如《老男孩之猛龍過(guò)江》(2014)、《煎餅俠》(2015)等。此類(lèi)影片將逆襲的過(guò)程夢(mèng)幻化、搞笑化,以勵(lì)志片的形式顛覆了關(guān)于奮斗改變命運(yùn)的勵(lì)志神話,亦可稱(chēng)之為“反勵(lì)志片”。這類(lèi)反勵(lì)志的青春喜劇片還發(fā)展出一種雜糅穿越/魔幻元素的新類(lèi)型,如《夏洛特?zé)馈?2015)、《重返20歲》(2015)、《28歲未成年》(2016)等。《夏洛特?zé)馈分兄魅斯┰健⒅胤登啻簹q月,體驗(yàn)不一樣的人生,爾后心安理得地繼續(xù)其寡淡的人生。影片有漫畫(huà)化的青春片人物設(shè)置,然而顛覆了青春片中的“女神”形象,穿越時(shí)空中終于到手的女神變成了“蕩婦”。影片利用穿越實(shí)現(xiàn)了人物設(shè)定的改寫(xiě),亦反轉(zhuǎn)了敘事動(dòng)力,主人公的人生追求由泡女神、出人頭地,到接受現(xiàn)實(shí)、擁抱平凡的家庭生活。從另一層面說(shuō),影片亦對(duì)經(jīng)典愛(ài)情片元素實(shí)施了改寫(xiě),主人公不是越過(guò)障礙、贏得女神,而是將女神污名化,轉(zhuǎn)而心平氣和地接受命運(yùn)拋來(lái)的“遺憾的伴侶”。相比美國(guó)青春片《重返十七歲》(2009),同樣是嫁接了魔幻元素的青春喜劇片,同樣傳達(dá)了一種“珍惜當(dāng)下”的意旨。然而《重返十七歲》表現(xiàn)出對(duì)“二次成長(zhǎng)”的關(guān)注,穿越回青春的主人公實(shí)現(xiàn)了與子輩的共同成長(zhǎng);而《夏洛特?zé)馈穭t有反成長(zhǎng)的傾向,過(guò)于倚靠低俗的搞笑段子來(lái)支撐影片,結(jié)果難免淪為“雜亂的綜藝短劇”(焦雄屏語(yǔ)),這也基本上是當(dāng)下喜劇片的通病。青春喜劇片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開(kāi)發(fā)“青春”的電影思維,對(duì)現(xiàn)實(shí)秉持一種批判性的視角,避免一味地解構(gòu)、迎合觀眾的低俗取向。
(四)青春+愛(ài)情片
青春愛(ài)情片也是一種邊界模糊的亞類(lèi)型,近年來(lái)的青春愛(ài)情片往往有鮮明的喜劇風(fēng)格,此類(lèi)影片主要針對(duì)年輕女性觀眾,瞄準(zhǔn)理性化的都市中年輕女性的情感需求,已形成小妞電影、都市愛(ài)情等初具類(lèi)型氣候的片種。典型影片有《杜拉拉升職記》(2010)、《志明與春嬌》(2010)、《前度》(2010)、《失戀33天》(2011)、《北京遇上西雅圖》(2013)、《被偷走的那五年》(2013)《前任攻略》(2014)、《撒嬌女人最好命》(2014)等。此類(lèi)青春愛(ài)情片的沖突模式由經(jīng)典愛(ài)情中個(gè)體對(duì)秩序的反抗轉(zhuǎn)換為三角戀、多角戀,主要的敘事動(dòng)力是對(duì)愛(ài)偶的爭(zhēng)奪,失去愛(ài)情不僅意味著自身在他人眼中的貶值,也使自身限入現(xiàn)實(shí)困境。其喜劇風(fēng)格的植入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掩蓋了愛(ài)情背后基于現(xiàn)實(shí)的利益沖突。當(dāng)下更受期待的是失戀、移情別戀、曖昧關(guān)系之類(lèi)的愛(ài)情敘事,古老恒定的愛(ài)情法則在當(dāng)下是失效的。后現(xiàn)代語(yǔ)境下一切處在流動(dòng)的狀態(tài)中,個(gè)體如何在變動(dòng)不居的愛(ài)情游戲中贏得主動(dòng)、在與愛(ài)情捆綁的生存資源的分配中占據(jù)主動(dòng),成了更具看點(diǎn)的敘事。在此類(lèi)青春片中,愛(ài)情倫理(愛(ài)情至上)與現(xiàn)實(shí)的生存哲學(xué)經(jīng)由喜劇的方式達(dá)成了矛盾的統(tǒng)一。《失戀33天》講述愛(ài)情的失而復(fù)得,但采取的是反傳統(tǒng)愛(ài)情敘事,沒(méi)有一見(jiàn)鐘情、沒(méi)有儀式化的定情瞬間,男女主人公的愛(ài)情掩藏在略帶喜劇性的“中性”外表下,以一種不易引起人緊張的、類(lèi)似“同性情誼”的方式展開(kāi),最終水到渠成。重獲愛(ài)情的過(guò)程也是自我療愈、重建自我認(rèn)同的過(guò)程。此類(lèi)影片多設(shè)定職場(chǎng)場(chǎng)景,愛(ài)情同時(shí)關(guān)聯(lián)著與職場(chǎng)生存相關(guān)的理性,主人公最終獲得職場(chǎng)與愛(ài)情的雙贏。
(五)青春+公路片
公路青春片是一種相對(duì)小眾的類(lèi)別,與青春勵(lì)志片有重疊,部分承載了旅行文化,有明顯的地域行銷(xiāo)訴求,典型影片如《練習(xí)曲》(2006)、《轉(zhuǎn)山》(2011)、《后會(huì)無(wú)期》(2014)、《尋找心中的你,王家欣》(2015)等。這類(lèi)影片觸及了“喊老”的一代潛意識(shí)層面對(duì)“告別青春”的抵觸:影片的表層敘事是通過(guò)一場(chǎng)自我放逐的尋找/旅行/冒險(xiǎn)來(lái)完成青春的告別儀式(也是成人的儀式)的。從深層意義上說(shuō),尋找/旅行/冒險(xiǎn)是一種自我療愈的方式,個(gè)體在其中經(jīng)歷身心的磨煉,獲得直面缺憾的勇氣;與此同時(shí),尋找/旅行/冒險(xiǎn)通過(guò)將主人公從庸常瑣碎的現(xiàn)實(shí)中拔出,不斷變幻的陌生環(huán)境激發(fā)了主人公體內(nèi)的原初之力,為早衰的青春重新灌注能量,因而也使主人公收獲了“青春常駐”的自信。比之其他青春亞類(lèi)型,公路青春片相對(duì)具有超越性,然而部分影片過(guò)多地負(fù)載了旅游經(jīng)濟(jì),“在路上”成了一種被消費(fèi)的生活/休閑方式,因而削弱了成長(zhǎng)的內(nèi)涵。
三、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元青春電影的類(lèi)型立場(chǎng)
相比類(lèi)型電影的黃金時(shí)代,當(dāng)下類(lèi)型電影所面臨的社會(huì)語(yǔ)境更為復(fù)雜多變,社會(huì)熱點(diǎn)更新快,觀眾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情感結(jié)構(gòu)建構(gòu)亦處在動(dòng)態(tài)之中,因而觀眾很難形成對(duì)某一特定類(lèi)型的忠誠(chéng)。如果說(shuō)暢銷(xiāo)的類(lèi)型承擔(dān)了給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之裂縫提供縫合性講述功能的話,而如今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自身也是在變化的,因此類(lèi)型電影也必須保持與時(shí)俱進(jìn)的姿態(tài),及時(shí)調(diào)整自身的話語(yǔ)策略。同樣,青春片受商業(yè)驅(qū)動(dòng)追逐既有的成功模式,但有時(shí)也表現(xiàn)出充沛的活力與反類(lèi)型的特質(zhì),比如上文提到的青春喜劇片就以顛覆勵(lì)志片的方式制造喜劇效果。
近兩年消費(fèi)青春的熱潮退卻,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大體分化成兩類(lèi):一類(lèi)往類(lèi)型雜糅的方向發(fā)展,突破了元青春敘事的拘囿,形成了上文所述的青春亞類(lèi)型;另一類(lèi)青春電影則在堅(jiān)持元青春敘事的立場(chǎng)上,往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的方向上發(fā)展,演變?yōu)橐环N個(gè)體青春經(jīng)驗(yàn)的表述,如《少女哪吒》(2014)、《黑處有什么》(2015)、《少年巴比倫》(2015)、《我的青春期》(2015)、《八月》(2016)等。不同于《小時(shí)代》《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元青春類(lèi)型片,這類(lèi)元青春電影往往有著散文化的結(jié)構(gòu),沒(méi)有儀式性的成長(zhǎng)瞬間,沖突的結(jié)構(gòu)性意義被弱化,暴力是驟然而至的,反叛也似乎是無(wú)因的,而看似平淡無(wú)奇的講述卻往往直抵極具私密性的生命體驗(yàn)。兼具普泛性與私密性,盡可能地還原生活的原初體驗(yàn),但又避免淪為某種原教旨主義式的紀(jì)錄,對(duì)于創(chuàng)作者和觀眾而言,這類(lèi)元青春電影是溝通自我內(nèi)心與他人世界的媒介,“沉默的大多數(shù)”得以在這一關(guān)于青春的表達(dá)與消費(fèi)中“舒緩身份缺失造成的焦慮”[6]。
另一方面,這類(lèi)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的元青春電影也處在當(dāng)下類(lèi)型電影的大格局中,與類(lèi)型陳規(guī)或觀眾的類(lèi)型片觀賞經(jīng)驗(yàn)展開(kāi)了對(duì)話。通常人們期待從敘事中“發(fā)現(xiàn)”潛藏的秩序、索求一種對(duì)生活的解釋?zhuān)@也是類(lèi)型片的粉絲基礎(chǔ),而這類(lèi)新興的元青春電影敘事本身是不完整的——如《少女哪吒》中有意的敘事留白,以及《黑處有什么》對(duì)于“黑處有什么”這一疑問(wèn)的懸置——而且敘事并不遵循它的某些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闡釋“模式”,相反,它致力于顛覆這些“成功的模式”、改變觀眾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少女哪吒》將“成長(zhǎng)”與“反成長(zhǎng)”的命題并置——叛逆不羈的李小路最終接受社會(huì)、學(xué)校的規(guī)訓(xùn),步入主流白領(lǐng)階層;而優(yōu)等生王曉彬則自絕于學(xué)校、家庭,自我放逐于社會(huì)的洪流之中,拒絕給出自身行為的解釋?zhuān)簿芙^給觀眾提供一個(gè)完整的故事。影片溢出了“成長(zhǎng)敘事”的地界,對(duì)“成長(zhǎng)”本身也予以置疑,少女“成長(zhǎng)”路上的重要設(shè)置——愛(ài)情被一筆帶過(guò),似乎完全無(wú)視觀眾對(duì)于青春電影之重頭戲“愛(ài)情”的消費(fèi)期待,類(lèi)似于當(dāng)下德國(guó)“后青春”電影中愛(ài)情只是充當(dāng)意義找尋和自我身份尋求的一個(gè)載體。[7]這類(lèi)元青春電影的反類(lèi)型還體現(xiàn)在敘事高潮的弱化以及對(duì)“傳奇”敘事的顛覆上。如《我的青春期》(2015)中反愛(ài)情傳奇的敘事、《少年巴比倫》(2015)中反勵(lì)志傳奇的設(shè)置,都借重了觀眾的愛(ài)情片、勵(lì)志片觀影經(jīng)驗(yàn),只不過(guò)在敘事的走向中,愛(ài)情或勵(lì)志傳奇被無(wú)聲地解構(gòu)了。又如,《黑處有什么》(2015)中反高潮的情節(jié)敘事,屢次讓觀眾在以為接近真相的“關(guān)鍵時(shí)刻”預(yù)期踏空,影片徒有懸疑片的外觀,卻無(wú)解疑的設(shè)置。不僅如此,影片還鞭撻了這種“敘事上的完滿”,正是這種必須揪出犯罪分子的、強(qiáng)迫癥式的“敘事上的完滿”制造了冤案,而所有渴望“完滿”的人們皆成了同謀。
元青春電影的生命力建筑在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的基礎(chǔ)上,它總要以一種具有超越性、革新性的類(lèi)型姿態(tài),突破既有的成規(guī)。不同于《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人物一開(kāi)始到最后基本沒(méi)有轉(zhuǎn)變,似乎一踏入青春,每個(gè)人的角色即已定型為某類(lèi)恒定的文化符號(hào)——拜金、愛(ài)情至上或?qū)嵱弥髁x。在上述元青春電影中,角色是處在變化中的,且角色本身承擔(dān)了多重身份,有時(shí)甚至是兩種相互矛盾的身份——如《黑處有什么》中的少女曲靖既是奸殺案的潛在受害者,又是參與了陷害無(wú)辜者的施害者。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青春電影對(duì)于成長(zhǎng)主題的關(guān)注與其成為類(lèi)型之間存在著天然矛盾。“成長(zhǎng)”的著眼點(diǎn)在于角色的動(dòng)態(tài)轉(zhuǎn)變,而類(lèi)型片中通常“類(lèi)型角色在心理上是靜止的——他/她只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風(fēng)格、一種世界觀,還有一種預(yù)先決定的并且在本質(zhì)上不變的文化姿態(tài)的肉體化身”[8](P32)。
四、作為消費(fèi)方式的青春類(lèi)型之變遷
當(dāng)下青春片更多應(yīng)當(dāng)從一種觀看或消費(fèi)心理的角度來(lái)理解。如前所述,“青春”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類(lèi)型制作的思維,同樣,理解青春片也要從其所服務(wù)的觀眾群體入手。美國(guó)青春片有著相對(duì)完整的發(fā)展脈絡(luò),尤其注重與觀眾的互動(dòng),我們可以結(jié)合新世紀(jì)美國(guó)青春片的類(lèi)型變遷來(lái)審視當(dāng)下國(guó)產(chǎn)青春片的類(lèi)型發(fā)展?fàn)顩r,并對(duì)其未來(lái)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進(jìn)行某種預(yù)測(cè)。
如果說(shuō)秉承20世紀(jì)60年代《邦妮與克萊德》《畢業(yè)生》《逍遙騎士》等經(jīng)典青春片之內(nèi)涵的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好萊塢青春片在喜劇的外表下真正關(guān)注的還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青春男女必須面對(duì)的問(wèn)題——即將進(jìn)入成人世界的身份焦慮、對(duì)階層等級(jí)的困惑、對(duì)享樂(lè)的追求與對(duì)責(zé)任的逃避以及個(gè)人發(fā)展的壁壘等等的話,21世紀(jì)以來(lái)的好萊塢青春片則大體上“簡(jiǎn)化為可以在敘事、劇情、人物、風(fēng)格上用‘俗套’或‘公式’來(lái)統(tǒng)籌的一系列青春喜劇”[9],試圖以游戲、惡搞的方式解構(gòu)權(quán)威、觸碰禁忌,用性或愛(ài)情來(lái)超越那些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棘手問(wèn)題,典型的如《美國(guó)派》1-6部(1999-2007),行銷(xiāo)近10年之久,在青少年中引領(lǐng)了一種“時(shí)尚的消費(fèi)”[10]。2001迪士尼出品的《公主日記》則帶動(dòng)了一種以“自我實(shí)現(xiàn)”為內(nèi)核的“童話”青春喜劇的風(fēng)行,其中不乏成系列的、有影響力的電影,如《歌舞青春》1-3部(2006-2008)、《舞出我人生》1-3部(2006、2008、2010)、《灰姑娘的故事》1-2部(2004、2008)、《牛仔褲的夏天》1-2部(2005、2008)、《賤女孩》1-2部(2004、2011)等。這類(lèi)青春喜劇片的觀眾是以女性為主的高中生群體,除喜劇外,更常配用的元素是歌舞,通常以金發(fā)美少女為絕對(duì)主角,亦是其最大的賣(mài)點(diǎn)。
以迪士尼出品為主的美國(guó)校園青春喜劇在新世紀(jì)的第一個(gè)十年如此風(fēng)行,主要還是源于其對(duì)古老敘事母題的翻新切中了茲時(shí)青少年的現(xiàn)代性困境。這些新世紀(jì)童話的敘事動(dòng)力已不是那種人的自由意志、個(gè)體價(jià)值與社會(huì)陳規(guī)、父權(quán)壓迫之間的對(duì)抗,相反,人與自我的沖突、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困境以及個(gè)體永恒的孤獨(dú)成為其新的命題。比如“灰姑娘”系列套用了童話的人物設(shè)置,但新世紀(jì)灰姑娘面臨的已不是原生家庭設(shè)置的愛(ài)情障礙,而是來(lái)自內(nèi)心的、不敢正視愛(ài)情、不敢相信愛(ài)情的障礙。又如《公主日記》系列演繹了一個(gè)平凡自卑的高中女生變身公主的現(xiàn)代童話,主人公成為“公主”的首要障礙是內(nèi)心的自卑(“To be a princess,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are a princess”)。
近年來(lái)美國(guó)校園青春喜劇逐漸退潮,取而代之的是雜糅了奇幻、動(dòng)作、冒險(xiǎn)等類(lèi)型的跨類(lèi)型青春片,如《暮光之城》系列(2008-2012)、《移動(dòng)迷宮》系列(2014、2015)、《饑餓游戲》系列(2012-2015)、《分歧者》系列(2014-2016)等,其敘事動(dòng)力有從女性主導(dǎo)轉(zhuǎn)變?yōu)槟行灾鲗?dǎo)的趨勢(shì),這類(lèi)影片的觀影群體中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游戲愛(ài)好者(以男性為主)占據(jù)相當(dāng)大的比重。與之相呼應(yīng)的是,2010年起美國(guó)出現(xiàn)了飽含形而上意味的、聚焦“尋找自我”的青春片。不同于書(shū)寫(xiě)個(gè)人成長(zhǎng)體驗(yàn)的國(guó)產(chǎn)青春電影,美國(guó)這類(lèi)青春片關(guān)注更具普適性的存在困境、認(rèn)知危機(jī),亦廣泛涉獵社會(huì)問(wèn)題、探討死亡等終極命題,兼容荒誕與小清新、天真與世故、幽默與殘酷、超脫與惡俗等各種差異性的風(fēng)格,在青少年中引發(fā)了強(qiáng)烈的反響。典型影片如《說(shuō)來(lái)有點(diǎn)可笑》(2010)、《歪小子斯科特對(duì)抗全世界》(2010)、《壁花少年》(2012)、《弗蘭西絲·哈》(2012)、《夏日之王》(2013)、《好景當(dāng)前》(2013)、《少年時(shí)代》(2014)、《星運(yùn)里的錯(cuò)》(2014)、《紙鎮(zhèn)》(2015)、《我和厄爾以及將死的女孩》(2015)等。這些影片形式上十分靈活、注重貼合年輕觀眾的審美習(xí)慣,講究一種天馬行空的寫(xiě)實(shí),如《歪小子斯科特對(duì)抗全世界》就融合了游戲闖關(guān)和漫畫(huà)的手法,而《說(shuō)來(lái)有點(diǎn)可笑》中略帶荒誕性的封閉空間設(shè)置傳達(dá)的卻是最平實(shí)的生存體驗(yàn)。從新世紀(jì)前十年程式化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到近年來(lái)文藝性的“尋找自我”,美國(guó)青春片已走出了類(lèi)型的樊籬,往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的維度邁進(jìn)。
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在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類(lèi)型態(tài)勢(shì)漸次明朗。2002年以《藍(lán)色大門(mén)》開(kāi)啟的小清新電影充當(dāng)了臺(tái)灣電影復(fù)興的主力,出現(xiàn)了《盛夏光年》(2006)、《不能說(shuō)的秘密》(2007)、《海角七號(hào)》(2008)、《聽(tīng)說(shuō)》(2009)、《艋舺》(2010)等有影響力的青春片。至2011年九把刀執(zhí)導(dǎo)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引發(fā)了海峽兩岸的觀影狂潮,隨即內(nèi)地青春片蔚然成風(fēng)。2013年后青春片產(chǎn)量驟升,大量跟風(fēng)之作皆以“青春”為主要消費(fèi)點(diǎn),懷舊、感傷的意味濃厚,如《匆匆那年》(2014)、《同桌的你》(2014)、《左耳》(2015)等,這類(lèi)墮入俗套的青春片近兩年已退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lái)出現(xiàn)的一類(lèi)相對(duì)嚴(yán)肅的、關(guān)乎二次成長(zhǎng)的青春片,如《被偷走的那五年》(2013)、《我的少女時(shí)代》(2014)、《哪一天我們會(huì)飛》(2015)等,在主打“校園青春”的基礎(chǔ)上有所提升,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懷舊”,以重返青春來(lái)尋求繼續(xù)前行的動(dòng)力。重返青春,即重返源頭、尋找最真的自我、重塑現(xiàn)在,以實(shí)現(xiàn)從現(xiàn)實(shí)困境中想象性的突圍。這類(lèi)影片相對(duì)有較大的類(lèi)型發(fā)展空間。而接替校園懷舊青春片成為國(guó)產(chǎn)青春片主力的則是上文所提到的超類(lèi)型、反類(lèi)型的元青春電影。
中國(guó)青春片作為一個(gè)大的類(lèi)型片種,其發(fā)展程度顯然落后于美國(guó)青春片,但近來(lái)中國(guó)電影工業(yè)發(fā)展迅猛,自我更新速度加快,近五年國(guó)產(chǎn)青春片即經(jīng)歷了懷舊校園青春片的速興速朽。相比之下,新世紀(jì)美國(guó)的校園青春喜劇風(fēng)行了十余年之久。而今顯而易見(jiàn)的是,國(guó)產(chǎn)青春片正朝著有內(nèi)涵的方向發(fā)展,立足于自我書(shū)寫(xiě)的青春片日益成為其主流,這類(lèi)影片需要避免沉湎于個(gè)人化的青春講述,可以適當(dāng)借鑒美國(guó)近年來(lái)青春片的表現(xiàn)手法,開(kāi)拓自身的表現(xiàn)視閾,提升青春片的類(lèi)型品格。我們可以期待出現(xiàn)類(lèi)似《我和厄爾以及將死的女孩》之類(lèi)的具有超越性的超類(lèi)型青春電影。2016年國(guó)產(chǎn)青春片《七月與安生》就是較好的嘗試。同樣是觀眾諳熟的青春電影情節(jié),《七月與安生》翻新了講述故事的手法,敘事上的多重反轉(zhuǎn)借鑒了懸疑推理片,其多聲部的講述又形成了一種復(fù)調(diào)的效果,使得影片的內(nèi)涵處在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中,超越了類(lèi)型陳規(guī),可以被一再解讀。
(責(zé)任編輯 彭慧媛)
[1] 于欣,邊靜.中國(guó)影院觀眾的十年變化與影院經(jīng)營(yíng)服務(wù)[J].當(dāng)代電影, 2015,(12).
Yu Xin and Bian Jing,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vie Audiences in 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Services of Cinema,ContemporaryFilms, No 12, 2015.
[2]于冬.我國(guó)平均電影消費(fèi)年齡21.6歲[EB/OL].http://www.anfone.net/a/BNYYJT/2017-10/5111889.html.
Yu Dong, The Average Age of Chinese Consumers is 21.6, see http://www.anfone.net/a/BNYYJT/2017-10/5111889.html
[3][英]齊格蒙·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xiàn)代道德[M].郁建興,周俊,周瑩,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2.
Zygmunt Bauman,LivingintheFragments:PostmodernEthics, trans. by Yu Jianxing, Zhou Jun and Zhou Ying, Shanghai: Xuelin Press, 2002.
[4]何謙.致青春——作為另類(lèi)歷史、代際經(jīng)濟(jì)與觀看方式的美國(guó)青春片[J].電影藝術(shù),2017,(3).
He Qian, For Youth: The American Youth Films as Alternative History, Intergeneration Economy and Viewing Measure,FilmArt, No 3, 2017.
[5][美]詹姆斯·納雷摩爾.黑色電影:歷史、批評(píng)與風(fēng)格[M].徐展雄,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
James Naremore,FilmNoir:History,CriticismandStyle, trans. by XuZhanxio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6]譚苗.當(dāng)代青春文學(xué)的時(shí)代特征、敘事主題及視角研究[J].中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2017,(1).
Tan Mia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Narrative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of Contemporary Youth Literature,ChinaLiteratureCriticism, No 1, 2017.
[7]張?zhí)?影像中的德國(guó)式后青春——當(dāng)代德國(guó)青年電影導(dǎo)演的青春敘事及其社會(huì)語(yǔ)境[J].當(dāng)代電影,2016,(7).
Zhang Tao, The German Youth in Images: The Youth Narration and Its Soci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German Youth Film Directors,ContemporaryFilms, No 7, 2016.
[8][美]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lèi)型電影[M].馮欣,譯.上海:世紀(jì)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Thomas Schatz,HollywoodGenres, trans. by FengXin,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9]楊柳.在青春的俗套里成長(zhǎng)——好萊塢青春喜劇的發(fā)展及其借鑒意義[J].當(dāng)代電影,2014,(6).
Yang Liu, Growing in the Convention of Youth: The Development of Hollywood Youth Comedy and Its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Films, No 6, 2014.
[10]陳旭光.近年喜劇電影的類(lèi)型化與青年文化性[J].當(dāng)代電影,2012,(7).
Chen Xuguang, The Categorization and the Youth Culture of Comedy Films in Recent Years,ContemporaryFilms, No 7, 2012.
Trans-genre,Ultra-genreandAnti-genre:DevelopmentTendencyoftheGenreofContemporaryChineseYouthFilm
Yang Linyu
In an age which is dominated by young audience, “youth”, as a genre thought,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so that almost all genre films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youth” in their own frames. Chinese youth film, as a genre film, is still immature. It adopts the expression methods from other genre films, trying to draw out audiences' past viewing experiences, to exceed the restriction of “youth”, and to enter the field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anks to a wide acceptance of the young audiences of the genre innovation, youth films become an experimental field of trans-genre films. In recent years, the sub-genre youth films are very active. However, these films are immature and there are spa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nres. The youth films in the U.S. have develop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hey have past the time when they followed other genres and copied themselves, turning to the ultra-genre youth film with depth. When Chinese youth films have past the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is short, adaptable and fast, they are trying the depth mode. As a result, a group of representative youth films appear with ultra-genre and anti-genr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youth films, trans-genre, ultra-genre, anti-genre, meta-youth
Abouttheauthor:Yang Linyu, Post-doctorate and Associate Senior Editor at th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
2017-11-12
[本刊網(wǎng)址]http://www.ynysyj.org.cn
J902
A
1003-840X(2017)06-0015-08
楊林玉,首都師范大學(xué)政法學(xué)院哲學(xué)博士后、副編審。北京 100048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