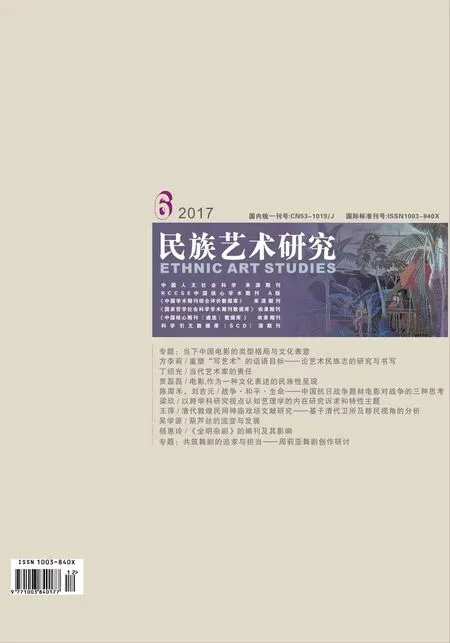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表述的民族性呈現
賈磊磊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表述的民族性呈現
賈磊磊
本文所指的民族是一個從對原初氏族、部落客觀存在的所指,逐漸演變、延伸到藝術、信仰的精神所指的文化命題,它含有從現實的世界向想象的世界不斷縱向移動的思想理念。民族的意旨經過不同歷史時代的演變,最終匯入到國家、社會和政治文化的譜系中。如今,電影中的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義已經引申、應強調、應力倡三種意義相互關聯的遞進式的集合概念內涵:民族已經引申出從現實的共同體到想象的共同體演變的意涵;民族性應強調其子民因由其民族性格而轉化為民族英雄后所彰顯出的民族個性;民族主義應力倡對民族的熱愛到對民族國的認同。
民族;民族性;民族主義 ;電影文化
民族問題不僅是一個關系到我們自己文化身份的歸屬以及文化立場確立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涉及國家歷史傳統、文化安全、社會心理、藝術發展的重要問題。在地緣政治的視野下,民族問題更是一個指涉到國家關系、地區安全乃至國際沖突的敏感問題。在電影領域內,民族問題其實一直是我們關注的藝術創作的重要問題。現在,民族問題除了涉及到少數民族文化的政策性保護問題外,還是一個關系到世界上不同國家關系的問題。除了在藝術創作領域增強相互的借鑒與合作之外,我們與世界各國在民族精神上有沒有相互近似的共同性?特別是我們與鄰近的亞洲國家有沒有民族文化上的通約性?即便我們不可能通過藝術與學術交流去進行不同民族精神的完全整合,我們還是希望實現一種能夠通過相互的交流進行相互認識、通過相互認識進行相互理解、通過相互理解進行相互合作的理想愿景。這才是我現在進行民族與電影相關問題學術研究的現實基點。
我們對電影中民族問題的研究,通常都是從民族題材的藝術創作維度展開——尤其是從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創作維度展開的。在這個領域取得了諸多的學術成果。然而,僅僅從電影藝術的表現題材將電影與民族的問題故事化,其間不僅存在著大量的尚未涉及的學術空白,而且由此還容易產生某種電影和民族問題無關聯的誤區。最起碼我們不能誤認為民族問題是一個在電影的題材論范疇里就能夠窮盡的問題。在本文中,將從電影的文化主題、電影的敘事語境與國家社會的文化語境的視野中,來探討電影世界中的民族問題,既將民族問題置放在一個電影人類學的譜系之中,來分析有關其民族、民族性、民族主義問題的理論命題,并用一種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知識框架,來闡釋、認識、判斷電影中尤其是東北亞電影中的民族問題。
一、民族與電影:從現實的共同體到想象的共同體
“民族”一詞(n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歐洲羅馬時代,它的詞義“natio”是由拉丁文“出生”(nasci)的過去分詞“natus”轉化而來的。意指種族、血統、出生物等。[1]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演變,民族的涵義由最初專指氏族、部落,逐步發展成為特指在一定地域內基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社會共同體,進而又特指那些具有共同語言、共同歷史的文化共同體。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譜系中,英國學者史密斯(A.D. Smith)又將民族問題納入共同情感的范疇,從而增加了民族的文化內涵。他說:“民族是一個縱向和橫向聯系上的一體化的、擁有固定領土的群體,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權利和具有一種(或更多)共同的集體情感為特征的”[2]族群。可見,現代的民族觀念除了強調民族成員的公民身份之外,還特別注意到其“集體情感”的特征。即從過去強調民族的部落、語言的客觀歸屬,到開始強調其精神文化歸屬。
這些文化精神的歸屬問題在各種藝術的表現形態中反映得更為明顯。不同的只是,有時是在顯在的藝術題材的層面上呈現出來,有時則是以潛在的方式以藝術的敘事主題和敘事語境呈現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那些非民族題材的電影排斥在民族問題的討論框架之外,甚至,在那些非民族題材的電影中,所涉及的民族問題比那些民族題材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民族性以及民族主義的表達——就像獲得了中國電影史上票房冠軍的《戰狼2》(2017),在這部影片中所植入的民族主義情感,可以說是推動中國電影觀眾最為直接的觀賞驅動力。可是,如果僅僅從電影藝術的表現題材而論,它可能根本就不能進入電影民族問題研究的視野。
就民族問題的社會政治論述而言,斯大林1914年在其《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中提出的觀點,一直被民族問題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高度認可。斯大林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3](P294)這個關于民族的定義在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曾經廣為使用,并且得到普遍贊同。斯大林所強調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表現在文化上的心理素質四個維度的共同性,至今也是我們認識民族問題的一把鑰匙。不論民族的分裂是源于何種因素,導致他們融為一體的關鍵因素依然不能超越斯大林所強調的這“四個共同性”。雖然,關于民族的定義后來還在不斷推出,但是,因其概念定義的全面性,直到今日,這個定義依然不能為人們所否定。盡管,許多學者曾經將民族的認知納入到不同的知識體系乃至學術研究的范疇,但是,他們依然沒有能夠超越傳統的社會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如:安東尼·吉登斯曾認為,民族是指“居于擁有明確邊界的領土上的集體,此集體隸屬于統一的行政機構。”4(P144)霍布斯鮑姆認為:“‘民族’的建立跟當代基于特定領土而創生的主權國家是息息相關的,若我們不把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將會變得毫無意義。”[5]美國文化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當代文化學研究領域,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并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用安德森自己的話來說,他是遵循著人類學的精神,對民族作如下的定義:“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它是想象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6](P6)安德森所說的這種同一個民族的人們在內心世界里相互聯結的“意象”,就是人們對民族歷史與民族文化的集體認同。這是一種來自于民族文化族群中的集體力量,在被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觀念、意識所左右、所驅動,從而形成的某種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現象。電影,有時只是這種文化現象中的一種圖景,它昭示著民族的歷史不管怎樣演變,民族的文化不論如何翻新,總是有一種恒常不變的內在力量在裝點著民族世界的景象——就像大自然的無形巨手在拉動著春夏秋冬的循環往復,它在人們不經意間改變著世界。
展望當代世界影壇,基于國家對民族情感的普遍認同,許多國家的電影越來越表現出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回歸、對民族發展歷史的守望,以及對民族精神的崇仰,相繼出現了一種回歸傳統文化的電影文化潮流。中國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2000),張藝謀導演的《英雄》(2002),陳凱歌導演的《趙氏孤兒》(2010),侯孝賢導演的《刺客聶隱娘》(2015),還有徐浩峰導演的《師傅》(2015)、《箭士柳白猿》(2016),路陽導演的《繡春刀》(2014)、《繡春刀Ⅱ·修羅戰場》(2017),這些影片的導演身份各不相同,在藝術類型與語言風格上也不盡一致,但是,在文化精神的指向上卻都呈現出一種皈依民族風范、回歸民族歷史的文化特征。應當說,武俠功夫電影是最具中華民族風范的電影類型,尤其是在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弘揚漸成風尚的時刻,這種皈依民族傳統的創作,在某種意義上不僅完成了流行文化對傳統文化的集體認同,而且為電影的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市場生機。
過去,我們對蘇聯乃至俄羅斯電影的認知主要集中在衛國戰爭電影的視域內。其實,近年來俄羅斯也創作了許多歷史題材的故事片。如:表現13世紀上半期人民所愛戴的亞歷山大公爵與敵人作戰的影片《全軍破敵》(2007),講述最底層的俄羅斯農民自覺地組織起來驅趕走了波蘭占領軍的《1612動亂時代》,以及展現拿破侖入侵俄國的軍隊在博羅季諾戰役打響前夕的諜戰故事《1812:騎兵之歌》。這些電影在俄羅斯電影中所占的數量并不多,但是,它們卻表現出當代俄羅斯電影對其民族歷史的共同回望。同處于東北亞地區的韓國,所創作的《飛天舞》(2000)、《武士》(2001)、《無影劍》(2005)、《鳴梁海戰》(2014)、都有一種對民族歷史深切關懷的情懷。作者將對民族國家的向往、對故鄉家庭的思念、對親人情感的寄托都付諸于電影的歷史敘述之中,所以,韓國電影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是一種體現國家意志、家庭倫理與個人情感三位一體的英雄形象。這種國家、家庭、個人三位一體的銀幕角色,使觀眾在電影的觀影過程中完成的是對于國家形象的認同、對群體價值的確認與對自我理想實現的想象性滿足。而不像好萊塢電影,在價值取向上更多地向個體價值認同,最起碼在相互對立的兩極價值取向之中,更多地是向個體維度傾斜。這是東北亞國家電影在價值維度上所表現出來的它們之間的文化親近性,即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基礎上所形成的民族國家在文化取向上的趨同性。它顯示出電影這種建立在產業生存法則體系之上的文化表達,更具有一種類似于標準化的文化工業意味。
綜上所述,民族的概念,是一種從現實的世界向想象的世界不斷縱向移動的文化理念。它從最早氏族、部落等客觀存在的所指,逐漸演變、延伸到藝術、信仰中的精神所指,最終匯入到國家的文化譜系與社會的政治譜系之中。況且,“在現代世界中的每個人,就像他或她擁有一個性別一樣,都能夠、應該,并且將會擁有一種民族成員的身份.”[6](P4-5)盡管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通常以族群(Nationalities)為基礎,但一個族群可以在沒有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存在。一個國家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而族群首先是文化的。在當代人文科學的語匯中,民族、族群與國家已經不是對立的概念,而通常是作為相關的概念來使用的。包括我們現在所提倡的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實際上原本就包括民族精神、民族氣派、民族風格的含義,同時,也包括對于民族精神的承傳與對民族文化的弘揚這些相關的內容。
二、民族性與電影敘事:從民族性格的塑造到民族英雄的鐫刻
在人類歷史上,民族與國家經常處于相同的語言表述序列之中。特別是在文化表達中,民族與國家通常是一體的。最起碼人們一般不會將這兩個稱謂相互對立或割裂開來。特別是“當民族與國家二者合為一體時,即國家內只有單一的民族,國家的領土界限與居民居住地范圍相同,而且文化與政治已經逐漸融合時,這種國家,稱之為民族國家”。[7](P5)不過,據統計世界上只有大約10%的國家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8](P528)事實上,盡管民族的界線與國家的界線總是難以完全縫合,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一種多民族的混合體,可是在習慣上大家還會將民族與國家統而觀之。
我們通常認為,構成民族性(ethnicity)的基礎是文化認同,決定民族性認知的前提是國家認同。沒有民族性的共同認知,國家就要分裂。其實,Ethnic是從希臘文Ethnikos經過拉丁語轉化而來的,是Ethnos的形容詞形式,Ethnic最初用于英語時表示的含義是“非基督徒或猶太人、無宗教信仰的人、異教徒。”[9]雖然我們不能說在藝術中對民族性的背離就是對國家的逆反,但是,我們卻可以說,在藝術中對民族性的堅持,就是對國家文化尊嚴的守望。世界上許多國家與民族都曾經歷過外敵的野蠻侵略,也都有過對外敵艱苦卓絕、前赴后繼的英勇斗爭。特別是蘇聯人民反抗納粹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國人民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抗日戰爭,都是兩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血火篇章,也是兩國人民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在這種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用鮮血與烈火鑄成的民族英雄,以及在真實的歷史英雄審美的基礎上生成的革命英雄主義的美學傳統,是我們兩國人民極為寶貴的精神遺產。為捍衛國家的主權而戰與為捍衛民族的尊嚴而戰,為祖國的生死存亡而戰與為民族的榮辱沉浮而戰,不過是在同一種價值體系中的兩種不盡相同的表達方式而已。
這種價值體系并不是作為一種外在的思想因素進入到電影的敘述文本之中,而是作為一種推進故事情節不斷延續、變化的敘述主體支撐著整個電影的敘事框架的。如今我們遠離那個戰火硝煙的年代已經60多年,可是,在我們的電影藝術歷史中,那個時代的烽煙從未散去。在我們的電影銀幕上不斷地展映著、再現著那些偉大戰爭的歷史畫面,它們已經成為電影藝術史上一座座不朽的豐碑。蘇聯的《攻克柏林》(1949)、《解放》(1972)、《決戰中的較量》(2001);中國的《血戰臺兒莊》(1986)、《太行山上》(2005)、《百團大戰》(2015)。民族與國家在電影特定的表現題材中是其價值體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在我們拍攝的中華民族反抗外敵侵略的影片中,有時為了表現所謂的人類視野,有時為了體現所謂的全球胸懷,刻意地設計了所謂的他者的視點。即影片的敘述者不是被設定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了所謂的人類立場上,其實確切地講,是站在了他者的立場上,去表現侵略者的痛苦,替法西斯懺悔,替殺人兇手贖罪。雖然,影片作者的主觀意圖也許并非如此。但是,因影片的敘事邏輯卻使觀眾得出了上述的結論。因為,電影攝影機的視點是有人稱指向的,而具有人稱指向的攝影機通常就是某個劇中人物的視點,觀眾就是通過他的眼睛來觀看電影中的故事、進而接受影片所表達的觀點的。事實上,正如安德森說的那樣:“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象為是等同于全人類的。雖然在某些時代,基督徒確實有可能想象地球將成為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會像這些基督徒一樣地夢想有朝一日,全人類都會成為他們民族的一員。”[6](P6-07)尤其在涉及到人類歷史上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倒退的生死之戰時,代表著正義、光明、進步的民族身份更是不能隨意喪失對于歷史的闡釋權。所以,電影的民族性并不是一個消解了社會歷史屬性的“空殼兒”,它體現著一個民族國家及其人民的全部愛國情感與切身的文化利益。
電影,作為一種敘事體,它的文化認同往往是以非強制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普遍的心理傾向。雖然,不同的民族國家在塑造自己的英雄偶像時有許多共同的特征,但是,這些相同的英雄形象卻有著不同的命運結局。中國戰爭電影中的英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來自于現實世界的真實人物,幾乎都是舍生赴死的殉道者。他們與美國電影中的那些叱咤風云的神話英雄不盡相同,這種差異最直接地表現在中國戰爭電影中的英雄形象許多都是依循著一種生死輪回的雙重邏輯來塑造的。這種雙重邏輯使中國戰爭電影對于民族英雄的再現,進入到一種比一般的藝術想象更為深邃的心靈領域。確切地說,中國電影中的民族英雄常常會有兩種不相同、但又相輔相成的結局。從中國20世紀60年代創作的紅色經典《冰山上的來客》(1963)、《英雄兒女》(1964),到20世紀年代創作的《黃河絕戀》(2005)、《紅櫻桃》(1995)、直到21世紀拍攝的《我的戰爭》(2016),這種生死輪回的雙重結局始終貫穿在我們對于民族英雄的歷史書寫之中。這就是說,當電影敘事體中的英雄人物按照現實的歷史邏輯犧牲之后,在傳統的美學范疇中已經完成了他的英雄敘事,可是,不論從電影的神話屬性還是從電影的教育屬性上來看,這種“英雄必死”的敘事邏輯,并不能真正滿足觀眾在電影的世界中所寄予的對于民族英雄永垂不朽的心理期待。所以,在同一個敘事文本中就會出現一種與按照現實主義的“英雄必死”的歷史邏輯相互平行的、按照理想主義的想象邏輯而展開的“英雄再生”的神話結局。在《冰山上的來客》中按照真實性原則表現的戰士們壯烈犧牲的敘事段落,它的補充段落是在銀幕上帶著勝利的微笑向觀眾一一走來的犧牲的戰友;在《黃河絕戀》中原本已經在黃河岸邊為了營救美軍飛行員與日本鬼子的激戰中英勇犧牲的女衛生員安潔,卻在抗戰勝利后又以想象的方式再現在銀幕上,美軍飛行員與她一起攜手并肩迎著噴薄的旭日走向遠方。在《我的戰爭》中,男主人公同樣犧牲在烈火硝煙的戰場上,他心儀的姑娘抱著鮮花站在站臺上歡迎志愿軍回國的隊列中,我們看到了穿著戎裝的這位英雄從列車上走下來……類似的雙重結局舉不勝舉。這種帶著明顯的民族想象的電影敘事,它的歷史文化淵源不僅在銀幕上,對這種民族文化的追溯,必將為我們打開認知中國電影的一扇更為悠遠、更為深邃的歷史之門。
關于民族性的影像表述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部俄羅斯、美國、法國合拍的戰爭電影《決戰中的較量》。在血光交織的伏爾加河上,年輕的蘇聯士兵冒著敵機的轟炸和掃射的危險,登上渡輪強行渡河。蘇軍指揮官對那些走向戰場的士兵發布的不是軍令,而是向他們宣讀了一位俄羅斯母親寫給自己兒子的信。在生死攸關的戰場上,這種對于民族情感的激發,對于為祖國而戰的士兵來說,有時甚至比軍令所產生的心理作用更大,它會激起士兵發自內心的愛國熱情。這種情感中所迸發出來的強大力量,是驅使士兵在決戰中視死如歸的偉大動力。與以往的戰爭影片不同的是,故事講述的兩個狙擊手的搏擊,所代表的并不僅僅是兩個國家、兩種軍隊之間的對抗,而是一位是來自烏克蘭獵狼人后代的蘇聯士兵,與一位來自巴伐利亞德國貴族的獵鹿者后裔的少校軍官的沖突。這并不是在比較兩個民族誰優誰劣,而是從地緣文化的角度,標明了一個外來民族的侵略者與一個本地民族的守護者之間的生死較量。狼與德國少校其實都是對蘇軍士兵瓦西里造成致命威脅的敵對因素,不同的只是這種威脅發生的地點一個是在瓦西里童年時代烏克蘭的森林里,一個是在瓦西里成年時代的斯大林格勒的廢墟中。所以,瓦西里與惡狼(少校)之間的交鋒,為整部影片的沖突奠定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可搖撼道德沖突的基調:兇惡與善良的對立,狼與人的角逐即成為影片潛在的生死沖突。如果說,瓦西里的民族性格中積淀了什么樣的文化基因的話,那么,生活在烏拉爾山林中時的善良只是構成他民族性格的基石。在這里,電影想要告訴觀眾的是,瓦西里不是一個天生的殺手(這點非常的重要)。瓦西里的英雄性格是在戰場上歷練、升華而形成的。他和少校之間的生死交鋒,并不是要將這場正義與邪惡的沖突指向兩個民族的認知,而是借助于延展的獵狼故事,在隱喻的層面上完成了瓦西里因其民族性格而升華為民族英雄的詩意表達。
三、民族主義與電影主題:從民族情感的傾訴到對民族國家的認同
不論是作為一個民族學的名詞,還是作為一個人類學的命題,民族主義(nationalism)都不是一個在學術界擁有統一內涵的概念。這不僅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表述系統不盡一致,既因語言的“異質性”使同一個概念在學術上難以形成統一的意義域,而且特別重要的是由于不同國家所走過的民族主義道路不盡相同,使人們難以從歷史的意義上確認民族主義的是非功過。民族主義的旗幟在世界上既引領過革命的風暴,同樣,民族主義的浪潮在地球上也曾激起過民粹主義的狂飆。在電影的銀幕上,我們看到過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典型形式——第三電影,拜讀過他們的《光與火的宣言》(1970);我們還看到過的歐洲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萊妮·瑞芬斯塔拍攝的納粹法西斯的暴力影像《意志的勝利》(1935)。對這些電影進行社會政治評價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如果我們從民族的、民族性的、民族主義的路徑上來評價這些電影以及確定其在世界電影史上的地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如果我們現在按照其在民族學范疇中的涵義來分析,民族主義即成為民族性的一種遞進形式。在現代社會政治的語言體系中,民族主義者甚至將民族確定為擁有最高地位的群體,強調的是民族的特殊性和優越性。*參閱葉夫列莫娃編纂《現在俄語大辭典》。我們必須正視,民族在它的黑色延伸地帶會衍生出基于民族優越性基礎上的邪惡的民粹主義。就像如今在美國發生的建立在種族優越感之上的“白人至上”主義那樣。我們不會忘記,希特勒曾經就是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瘋狂鼓吹者,其所持的這種狂妄的民族主義曾經將整個歐洲推進了戰爭的深淵。法西斯的鐵蹄踐踏了多少民族的土地,殘害了多少族群的生命,將他們帶進了萬劫不復的地獄。還有當代的恐怖主義者,他們也是以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猙獰面目在世界上肆意屠殺的。這些歷史的事實警示我們,民族主義的邊界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可能會與民粹主義相互接壤,延伸出危害人類的惡魔。然而,誰能夠將民族主義限定在邁向民族國家的光明大道上呢?尤其是在民族的利益需要保護,民族的情感需要傾訴,民族的尊嚴需要捍衛的時代,民族主義似乎成為一種上帝提供給人類的“雙刃劍”,它一面指向捍衛光明、民主、幸福的天堂,另一面則指向助長黑暗、邪惡、災難的地獄。
毋庸置疑,在民族主義正向的延伸部分,必將會產生基于民族主義精神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特別是在面對外族侵略與列強凌辱的歷史關頭,愛國主義的旗幟常常就是用民族主義者的鮮血浸染的,愛國主義的鋼鐵長城就是用民族主義的身軀鑄就的。盡管,世界各國紛繁復雜的發展歷史,會給民族主義寫下數不勝數的定義,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凡是那些挺身而出捍衛民族尊嚴、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而那些背棄了自己民族的敗類,同樣,也必然是國家的叛徒。在中國電影的銀幕上,對于這種邏輯的展現,曾經是我們中國電影藝術百年畫卷中極為重要的篇章。不用說那些揮寫中華民族的英雄將士與法西斯侵略者生死鏖戰的影片,就是我們那些描寫少數民族普通百姓現實生活的電影,也在表述他們對自己家園的熱愛、對民族文化的敬守與對國家的忠誠,同樣是可歌可泣的史詩。
在人類社會數千年的發展進程中,民族的歷史波瀾壯闊,民族的命運跌宕起伏,民族的英雄層出不窮。可是,正如安德森所言,在民族主義的視野內很少產生像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那樣偉大的思想家。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沒有歷史學界像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和馬克斯·韋伯這樣的引人矚目的思想巨匠。民族主義在經典理論上的“這種‘空洞性’很容易讓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知識分子對其產生某種輕視的態度”。[6](P5)包括那些同情民族主義的學者,也會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中的“神經衰弱癥”,是一種并不健康的狹隘心理。其實,民族主義的理論表述并不像安德森所說的那么悲觀。事實上,正如卡爾頓·海思說的,民族主義首先為我們開辟了一種歷史進程,民族國家恰恰就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建立并且發展起來的;同時,民族主義還包括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理念、原則、信念,以及將民族發展進程中的歷史經驗與相關的文化理念與社會原則整合起來的國家行為準則;最終民族主義還指向了對民族情感的傾訴以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在正面的意義上尊重、接受民族主義的根本理由。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承認,“民族國家只是理想的國家形式,現實中的民族國家與理想中的民族國家并不一致,它們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現實的民族國家基本上都不是單一民族建立的,民族的界線與國家的界線總是存在著程度不同的不一致”。[10](P29)
需要表明的是,我們在此從正面意義上使用的“民族主義”概念,既不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也不是18世紀歐洲歷史上的“殖民地民族主義”(colonial nationalism),更不是俄國沙皇曾經推行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ol nationalism)。[6](P110)我們在此強調的是那種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弘揚民族精神為主旨、以體現民族的利益為基點、以抒發民族的情感為特質的文化品質。影片《戰狼2》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以愛國主義為圭臬的民族主義精神。特別是在我們的國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必須要對我們的國家與公民的切身利益給予保護——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方式。在其他方式不能改變現實境遇的情況下,只有采取“以武制武”的方式。正所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當代世界,長久以來就一直有人預言“民族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可是,這種猜想不僅目前看來遙不可及。而且,民族主義不論是作為英雄主義的土壤,還作為愛國主義的根基,在歷史上都發揮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的律令為至高無上的規范的世界里,‘民族屬性’(nation-ness)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6](P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意思也許在特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民族的價值觀是我們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關于電影與民族性的闡釋,實際上只是想表明,在此類學術討論中,僅僅為其貼上一個民族的標簽是遠遠不夠的。電影所寄予的關于民族歷史的精神守望以及蘊含的關于國家與民族歷史的當代想象,都有待于對其進行更為深入的考察和更加透徹的研究。特別是在建構中國電影學派的路徑上,民族、民族性、民族主義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更是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梯。
(責任編輯 彭慧媛)
[1]約翰·基恩.民族、民族主義和公民在歐洲[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5,(2).
John Keane, Nations, Nationalism and Citizens in Europe,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 No 2, 1995.
[2]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的理論[J].民族譯叢,1986.
Anthony Smith,TheoriesofNationalism,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f Nationality, 1986.
[3]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CompleteWorksofStalin(VolumeTw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4]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M].北京:三聯書店,1998.
Anthony Giddens,Thenation-stateandViolence,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8.
[5]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導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Hobsbawm,NationandNationalism(Introduc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M] .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ExpandedEdition), trans. by Wu Rwei-Ren,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11.
[7]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Li Hongtu,StudyofModernNationalisminWesternEurope,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7.
[8]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Blackvillepoliticalencyclopedia,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2.
[9][美]威廉·彼德森.民族性的概念[A].林宗錦,譯.林耀華,校.[J].民族譯叢,1988,(5).
William Petersen,TheConceptofEthnicity, trans. by Lin Zongjin, annot. by Lin Yaohua,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f Nationality, No 5, 1988.
[10]周平.民族政治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Zhou Ping,EthnicPolitics(Introduc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Film,theEthnicPresentationasaCulturalExpression
Jia Leilei
Nationality in this paper is a cultural proposition which evolved from the signified of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primitive clans and tribes to a spiritual signified of arts and belief. Therefore, nationality concerns an idea that continuouslymoves longitudinally from real world to the imagined world. The intensions of nationality, after an evolution through many periods of times, finally converged into spectrums of natio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Nowadays, as national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films have been extended,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and promote a progressive integrated concept connotation concerning three interacted meanings as following. Nationality has been extended from a real community to an imagined community. Ethnic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on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 meaning which is manifested as a result of an evolution from the people’s ethnic characters to the nationalheroes. Nationalism should promot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devotion to nationality to 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nationality, ethnicity, nationalism, film culture
Abouttheauthor:Jia Leile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Visual Entertainment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Research Fellow at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2017-12-12
[本刊網址]http://www.ynysyj.org.cn
J90-05
A
1003-840X(2017)06-0069-08
賈磊磊,北京電影學院未來影像高精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北京 100029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