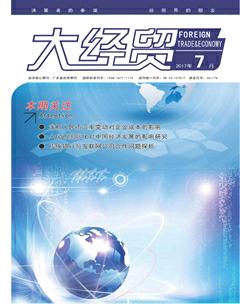人生論美學視角下的王光祈音樂美學思想中的“諧和主義”
【摘 要】 王光祈音樂美學思想的核心為“諧和主義”,起源于孔子的“禮樂”觀。王光祈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音樂的“諧和”作用:個人內心諧和;與社會諧和;與自然諧和。王光祈將音樂的“諧和”作用升華為對人生的改造,將藝術的“倫理作用”變為“美術作用”,將藝術品鑒和人生品鑒相融合;同時肯定了音樂表達情感的作用,提倡“美感”和“善心”并重,以情蘊真含善,真善美相貫通。其“音樂救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整個人生的“諧和”并不斷發揚中華民族的“諧和態度”。
【關鍵詞】 王光祈 人生論美學 諧和
一
“音樂” 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是在《呂氏春秋·大樂》中,“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1王光祈則是中國音樂史上一位完全以音樂學研究為主要目標的學者,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第一個音樂學家,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學奠基人之一。
王光祈美學思想中的“諧和主義”2,主要起源于孔子的“禮樂復興”思想,之后實踐于“少年中國學會”,但未能長久,開始試圖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來拯救當時混亂的中國社會,于是他將未完成的“少年中國”的夢想付諸于音樂當中,試圖用音樂來改變人的心理狀態,從而達到改變社會的形態的目的。他對于中西方的音樂發展進程做了詳細的梳理,結合中國傳統的音樂美學,把音樂和生活聯系在一起談音樂對于人生的改造作用,其思想的核心就是“諧和”,構建藝術化的人生,這一觀點聯系扎根于中國哲學的人生情懷和中華文化的詩性情韻的人生論美學。王光祈“音樂救國”的思想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諧和、人生諧和,世俗生活和藝術生活的渾然諧和,藝術品鑒與人生品鑒相交融,體現了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真善美相貫通的人生美學精神,凸顯了中華民族審美精神的獨特神韻。3
二
王光祈提出發揚“諧和”精神是中華民族復興之道,“諧和”是中華民族的特性,即民族性。和諧是人的自身、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應處于協調,恰到好處的一種狀態,而和諧人生是人類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在我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進程中始終體現出這一人生理念。“假如沒有音樂這樣東西,中國人簡直將不知道應該怎樣生活。”4 ““因此之故,音樂一物,在吾國文化中,遂占極重要之位置,實與全部人生具有密切關系。”5王光祈將人生的“諧和”分為了三個層次,首先是對于個人內心諧和,其次對于社會諧和,再其次對于自然諧和。
個人內心諧和“和”是中華傳統文化意識與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傳統音樂美學的核心思想,王光祈說我們的孔夫子,很懂得“諧和”的妙用,他的全部學說都建筑在音樂上面,通過音樂的“諧和”作用,將人類自私自利明爭暗奪的習性都軟化了。王光祈肯定了音樂對人類情感“諧和”的作用。音樂的情感特質在《樂記》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凡音之起,有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城文,謂之音。”6儒家以人為本,認為音樂的根本為“人聲”,音樂是“人心之感于物”。人心受到了客觀現實的感動,便產生的音樂,這種心物關系是人獨有的。王光祈指出中國近代陶養人們感情的藝術作品頗不多覷,而人類的精神作用,除理智之外,尚有感情意志兩種,極為重要。7因此王光祈極為看重音樂對人內心的“諧和”作用,將中華民族的“諧和態度”發揚光大。人的心物感應產生了音樂,就是為了表達情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8這都說明音樂離不開情感,“樂者,心之動也”,這心動產生的情感聲音按一定的規律形式表現出來,就成了音樂。正因為音樂是人類情感的表現,所以不同的情感,產生不同的音樂。王光祈說人們情感的發揮,極豐富活潑,但音樂表現的情感,不是無限制的一切欲望,不能“專靠感情用事”,要把感情納入理性的規范。王光祈繼承了儒家情理適中,符合人情的禮樂觀,因此音樂對個人內心的“諧和”來自兩方面,一方面“禮”是外面行動的一種節制,另一方面“樂”便是內心生活的一種諧和。王光祈特別強調了音律節奏的重要性,音樂之所以能夠使人心曠神怡,就是因為其中音節諧和的緣故。王光祈將人們的生活行動比作了一種節奏,我們所遵循的禮法,是我們內心諧和生活之一種節奏,行動之所以要節制,是由于人們內心情感諧和的要求。“內心諧和生活,好比一種音調,外面合禮行動,好比一種節奏。所有外面抑揚疾徐,都是依照內部諧和需要。”只有音調和節奏相互協調,才有動聽的樂音。假如一種禮法不近人情,不符合我們內心諧和生活的需要,社會秩序將紛如亂絲,人心風氣將日趨于下,我們內心的情感便不會舒暢。因此能“諧和”人心的音樂既要合乎人情,又要不失禮儀。“合情者,樂之和于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于外,所以救其流之失。”9這樣的人生才情理相繼,諧和舒心。
與社會諧和 既然音樂是人心理情感的外在表現,而人不是孤立的個體,是置身于社會結構中的,音樂同樣也是社會結構形態變化的反映。隨著社會的發展,音樂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音樂一定程度上能促進政治的和諧和文化的繁榮,起到諧和社會的作用。王光祈也說到“以樂治國”并非中國人獨得之奇,古希臘時期的美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矣嘗有此理想,有所謂“音樂倫理者”,欲利用音樂力量,以提高國民道德。當時正在德國留學的王光祈深受德國人民活潑的精神氣概感染,音樂是德國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物,但心系祖國的王光祈對當時沒有生機的中國充滿擔憂。王光祈始終強調音樂在人們生活中重要之位置,與我們的全部人生具有密切關系。沒有了藝術,沒有了審美,“中國人雖在青年,亦無不面有菜色”。人生變成了“枯燥的人生”,“殘酷的人生”,“凄涼的人生”,由此激發了王光祈“音樂救國”的理想:“吾人如欲掃除中國下等游戲,代以高尚娛樂,廓清殘殺陰氛,化為和平祥氣,喚起將死民族,與以活潑生機,促醒相仇世界,歸于大同幸福,舍音樂其莫由。”“喚醒民族改良社會之道奈何,曰自恐樂復興始。”10我國傳統音樂美學從以“和”為美的理念出發,從不同方面都反映著人類社會的諧和思想,影響深遠的“禮樂”思想認為音樂的本質是情感,但情感若不加節制就會亂,為了使社會和諧,音樂所起的審美功能應該是團結社會,而不是擾亂民心,分離社會,即“安善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王光祈希望中國能產生一種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性”,即“諧和”精神的國樂。這種國樂的責任,就在將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諧和態度”表現出來,使一般民眾聽了,無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儒家“禮樂”思想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鞏固君主的統治,所以其中夸大了音樂的社會功能,因此王光祈“音樂救國”的夢想顯得過于理想化。但是其追求諧和人生、諧和社會的理想是值得我們發揚的,秉承了中國現代美學的精神,是關注現實關懷的人生美學。王光祈和中國現代其他美學家一樣,都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基和堅實的民族立場,批判傳承了以儒道釋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生為中心、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體驗方法等,同時吸納了西方美學情感獨立、審美自律等核心理念和思辨、邏輯、科學的方法形態,與當時迫切的社會改造、人格提升、人性涵育的現實需求相結合11,形成了其獨特的“諧和主義”審美精神。
與自然諧和 音樂源于人的心物感應,心是人們內心的情感,物便是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王光祈在論述東西方音樂審美差異時談到,“東方恬淡而多情,故其發為音樂也,頗尚清逸纏綿,吾人每聞中國音樂,則多高山流水之思”12,而華麗壯闊的西方音樂常有富貴功名之感,代表一種城市文化,那平和恬淡,寧靜悠遠的東方音樂則代表自然山林文化。我國古代美學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就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呂氏春秋·大樂》中說道:“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太一”就是自然萬物按一定的規律和諧有序地運動。《樂記》中也將音樂的作用擴大到了天地宇宙:“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日月交替,四時代興,宇宙是一個和諧的整體,音樂的諧和之聲就是對自然諧和之聲的反映。老莊認為最理想的美便是自然之美,自然界的樂聲本就是“天籟”之音。“天人合一”是在個人內心諧和、與社會諧和后的最終理想,將音樂審美升華為一種超脫世俗的精神狀態。王光祈也說:“樂者也,小而言之,則為陶養人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為散布人類和平之使。”13音樂應該平衡人內心的生活,修身養性,舒暢感情,遠離功名,寄情于自然,化萬物為活潑生機,和平祥氣,這正是將審美無功利性和情感的審美意識轉換成了對人生意義,生命啟示的思考,從藝術品鑒升華為對人生的品鑒,是為人生的藝術,實現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
王光祈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歸結于一種“諧和態度”,王光祈強調音樂的作用在于“諧和”個人內心以至自然宇宙的生命。音樂之中含有的“美感”,不僅是單純地鑒賞,更是對生命于與生存的切入,也是達知通意美情的生命化育與詩意升華。14
王光祈不僅關注音樂的“美感”,同時也強調了音樂的“善”:“一首善的樂曲一定能使人平靜,而不是刺激人們的神經。”王光祈以舜帝的音樂為例,被孔夫子稱為“盡美矣,又盡善也”,以致孔夫子聽后三月而不知肉味。王光祈指出的音樂的“諧和”作用的根本就在于音樂要感動人們的“善心”。人的氣質精神有善和惡,那么音樂的聲音也有奸和正。音樂能“諧和”的要求應當是“善”,這樣的音樂,才能“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由此,王光祈提出應兼重“善”“美”兩面,偏重一方的音樂勢將“天然淘汰”。音樂來自人內心情感與外物的感應,“善心”產生“美”的音樂,來培養人的品德修養,陶養人的審美情趣,最終指向人的現實生存和生命,以情蘊真含善,真善美相貫通,整個人生都處于一種“諧和”的狀態,這是一種“美化”的人生,“藝術化的”人生。
三
王光祈音樂美學思想中的“諧和主義”,是將藝術從“倫理作用”變為“美術作用”。正如梁啟超所倡言的“人類固然不能個個都做供給美術的 ‘美術家,然而不可不個個都做享用美術的 ‘美術人”15,說明藝術審美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將藝術的“情感”和生命實踐相交融。豐子愷也說“把創作藝術、鑒賞藝術的態度應用在人生中,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藝術的情味”16,這和王光祈提出的音樂的“諧和作用”殊途同歸。音樂的“諧和”作用即藝術的“美術作用”,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實現“人生的藝術化”。王光祈美學思想中的“諧和主義”扎根于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真善美相貫通的人生美學精神。發揚中國民族的“諧和”精神是其畢生的理想,這也是中國現代美學的審美精神,其遠功利追求“諧和”人生的旨向勾連了美學理論、藝術實踐、審美生存的貫通,凸顯了中華民族審美精神的獨特神韻。17
藝術創作是面向大眾的,美育的對象也是廣大民眾,藝術鑒賞和生活體驗相互融合。藝術審美在生活中的實踐,其目的就是為生命的詩化,淡泊有限的聲名功利,追求無限的詩性和自由,在審美中得到內心的寧靜,將世俗的眼光轉變為藝術的眼光,最終達到人與天地萬物的“諧和”。
【參考文獻】
[1] 張雙棣,呂氏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
[2][4][5][7][10][12][13] 王光祈,王光祈音樂論著選集[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
[3][11][14][17] 金雅,聶振斌,論中國現代美學的人生論傳統[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0-14.
[6] [8] 賈德永,禮記·孝經注譯[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3:159.
[9] 蔣孔陽,先秦音樂美學論稿[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245..
[1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M].北京: 中華書局,1994 (5):22.
[16] 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 2 卷[M],杭州: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226.
作者簡介:楊倩云(1993-08月-28日)女,漢族,云南昆明人,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2015級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