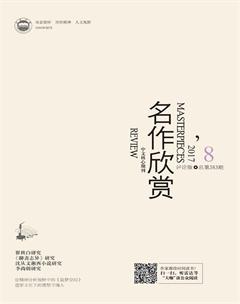“戰神在擦他的靴子”
摘 要:從年輕的時候開始,痖弦就因為戰爭遠離家鄉和親人,在顛沛流離中感知著生活,也在戰爭中失落了他的青春,關于戰爭的記憶已經深刻根植于痖弦的腦海之中,而這些生命體驗也必將融入詩人的創作之中。由此看來,戰爭應該是痖弦詩歌中一個重要且深刻的主題,其戰爭詩歌值得我們去探索。
關鍵詞:痖弦 戰神 戰爭
詩人痖弦的創作時間并不長,始于1951年左右,止于1966年,前后加起來不過十四五年的時間,其詩歌創作主要集中在三十五歲之前,詩歌作品集結于《深淵》這一本詩集。雖然只有一本詩集問世,但是痖弦在現代漢語詩壇的地位卻是不容小覷的,龍彼德稱痖弦為“現代詩壇的一座睡火山”。古繼堂在《簡明臺灣文學史》一書中談及痖弦創作生命過早枯竭時,十分客觀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多年沒有新作發表的詩人不被人們忘記,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詩質好,二是《聯合報》副刊主編的職務對他的名氣和地位也不無幫助。”{1}本文就以《戰神》一詩為例,去探尋痖弦詩歌的特質。《戰神》創作于1957年,收錄在詩集《深淵》的卷之二“戰時”。從題目看,這是一首人物詩,描寫對象為“戰神”。戰神本是指古代神話中的英雄人物,中國神話中的戰神為蚩尤與刑天、呂尚、二郎神,希臘神話中的戰神是宙斯與赫拉的兒子阿瑞斯。蚩尤、刑天等人是智謀與勇敢的化身,而阿瑞斯卻嗜殺、血腥,是力量與權力的象征,也是人類災禍的化身。依據詩歌的敘述和主題表達,推測痖弦《戰神》一詩中,“戰神”指涉的應是阿瑞斯——人類災禍的化身。然而詩人真正的創作目的,不僅僅是描寫“戰神”這個人物,其旨在透過“戰神”來寫戰爭的殘酷,所以《戰神》更是一首戰爭詩歌。
一、西方文化的影響
痖弦大量發表詩歌并在詩壇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時期,是他從大陸遷徙到臺灣的時期。地域上的隔絕、政治上的分離、文化上的斷裂,都使得他只能面向西方,從西方的哲學、西方的詩歌乃至西方的文化中去尋找精神支持與藝術范式。何況現代主義的詩風在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已經十分強盛。{2}西化精神對痖弦的影響不容忽視,正如痖弦自己所講:“對西方傳來的東西非常喜歡,對西方文學充滿幻想甚至可以說崇拜,在寫作上也一直向西走,像朝山人,像進香客,向西方頂禮膜拜,狂熱地擁抱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3}暫且不談里爾克、洛卡等詩人對痖弦詩歌創作技巧方面的影響,單從《戰神》這首詩歌中的諸多詞匯,就能看到痖弦汲取的許多西方文化中的養分。整首詩共有五個小節,第一小節中的“十字架”“V”兩個詞匯:“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標志,原本是一種刑具,后來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于是它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愛與救贖;“V”則代表英文單詞“Victory”。第三小節中的“大馬士革刀”原產于古印度,是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國的兵器。第四節中的“滑鐵盧”一詞很明顯是指布魯塞爾的滑鐵盧鎮,當然也指涉拿破侖的那場英雄之戰——滑鐵盧戰役;“銅馬刺”中世紀出現在歐洲,用于騎馬者靴子的后跟,以刺激馬快跑。
可以看出以上詞匯都是源于西方或者國外的一些名詞。而痖弦在其詩歌中,熟練地將這些詞匯精心運用,“東方”與“西方”在一首詩歌里悄然相遇,并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賦予了詩歌更深層次的含義,飽含詩的哲理,讀來韻味無窮。
二、詩中的“戲劇性”
早有研究者指出,痖弦的詩富于“戲劇性”的特色,比如張默在《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中,論定痖弦的詩作具有“戲劇性”“思想性”“鄉土性”與“世界性”。{4}余光中也曾說:“痖弦的抒情詩幾乎都是戲劇性的。艾略特曾謂現代最佳的抒情詩都是戲劇性的,在中國,他的話應在痖弦的身上。”當然痖弦詩歌的戲劇性并不只是體現在其抒情詩歌當中,讀過《戰神》后,亦可感受到戰爭詩中蘊含的戲劇性的張力。本文重點談談《戰神》一詩中富有戲劇性的情節結構。第一節中,交代了詩歌所描寫的時間是“夜晚”,地點是“病鐘樓”,描寫的物件是兩姊妹——“時針和分針”。有了一個故事中必須具備的時間、地點、人物等要素之后,又對其進行渲染:“夜晚”是“很多黑十字架的夜晚”,“鐘樓”是“病”的,“兩姊妹”是“死”的。時針和分針已經停止轉動,就像是兩只“僵冷的臂膀”,呈現出“V”的形態。第一小節的書寫已經營造了一種莊嚴肅穆且黑暗恐怖的氛圍,就像是戲劇表演中的舞臺布景,先將讀者帶領到一個情感氛圍之中,奠定整首詩的情感基調,給予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
在一種近乎死寂的氛圍中,接下來的第二、第三、第四小節繼續展開情節敘述。第二節和第三節在描寫戰爭后的狀況,一場戰爭中有贏家有輸家,但是這個“贏家”是真的勝利嗎?痖弦說了,這是一種“黑色的勝利”,因為它帶來了死亡。正值青春的孩子留下曾經心愛的裙子,過早地夭亡,只剩下無助的母親在“喊魂”;戰爭之后留下血腥的戰場,“酒囊”“大馬士革刀”“號角”“火把”“盾牌”“殘旗”都是“沉默”的,其實這一部分是詩人在以靜寫動,這些曾經在戰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似乎在言說昨日戰場的恐怖,它們是戰爭殘酷無情的最有力的證據。一切都是沉默靜止的,唯有“婦人們的呻吟”,這是詩人在動與靜之間為讀者營造的一個想象空間:昔日充斥著血腥的戰場沉寂得可怕,只有失去孩子的婦人在呻吟。動與靜的對比,讓婦人的呻吟顯得更加刺耳,也加倍體現了撕裂感和凄涼感。
詩歌來到第四節終于寫到了“戰神”,他穿著帶有銅馬刺的靴子,不停地驅使戰馬前行,越過田野來到滑鐵盧,似乎剛剛經歷了一場酣戰。痖弦將幾個地點巧妙地羅列,再對戰神的行為動作進行描寫,大致塑造出一個戰神的形象,但有意思的是這節詩的最后一行——戰神在擦他的靴子。周圍明明是一個充斥著血腥的場景,戰神卻似乎在優哉游哉地“擦他的靴子”,可以理解為戰神極為愛護他的靴子,因為這是見證他戎馬生涯的物證,似乎更是詩人對戰神的一種諷刺:他的野心是驅使戰爭發生的始作俑者,于是有了孩童的夭亡婦人的呻吟,然而對于生命的隕落和給人們帶來的災禍,他似乎不以為然。所以看似輕描淡寫再平常不過的一句動作描寫,卻蘊含了別樣的意義。
關于痖弦“戲劇性手法”的創造性運用,不僅有之前的余光中、張默等人的肯定,后來也有不少論者對此有專門的提及,比如熊國華說:“痖弦十分善于在詩的創作中借鑒和運用戲劇、小說文類的技巧和表現手法,將早期新詩人聞一多、卞之琳、袁可嘉等人曾提倡和試驗過的‘戲劇性情景‘戲劇主義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極大地豐富了現代詩的表現手段和技法。”{5}
三、用歷史的眼光關注“人”的存在
《戰神》創作于1957年,詩中幾乎都在寫過去的歷史,痖弦以一個現代人的視角,立足于當下回眸歷史。通過書寫過去的事件,于歷史與現實之中,反思現在,警醒世人,也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的關懷,這是痖弦詩觀中歷史意識的體現。
在《戰神》一詩中,痖弦在表現戰爭的主題時,并沒有選擇宏大的視野進行創作,而是著眼于刻畫戰爭背景下個人的生存狀況。詩中的“人”包括了“母親”和“孩子”以及“婦人”和“嬰兒”。在戰爭造成的荒年里,母親們失去了孩子,于是痛苦地“喊魂”;在血淋淋的戰場上,充斥著婦人的呻吟,旁邊是用戰爭的殘旗包裹著的嬰兒的尸體。透過詩人的描述,仿佛聽到了文字背后母親撕心裂肺的喊叫,感受到一個母親刻骨的疼痛。
痖弦把目光放在了戰爭中婦女和兒童身上,其實他們就像是千千萬萬“人”的縮影;戰爭狀態下“人”如螻蟻,沒有人考慮他們的生死,戰場是好戰者酣戰的地方,更是無數普通人噩夢的場所。當然這首詩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形象——戰神,可是“戰神在擦他的靴子”,殘酷的戰爭奪去了多少鮮活的生命,人們尚且無暇顧及生死,這好戰的戰神卻在悠閑地擦著他的靴子!這個行為動作的刻畫是一種諷刺,也是詩人對戰神“神”的形象的消解。
通過寥寥幾筆,痖弦就刻畫出了戰爭中婦女、兒童、戰神的形象,通過細膩的描寫和對比,透過他們的生存狀態,讓讀者感受到戰爭的無情冷漠和血腥殘酷。
《戰神》是一首關于戰爭和死亡的詩歌,說來主題是有些沉重的,詩歌除了傳遞出戰爭的殘酷,以及作者厭惡戰爭的情緒,在創作過程中詩人還吸收西方文化、運用戲劇性手法,表現對人的關懷和對生命的觀照,讓讀者看到痖弦其“弦”不“啞”。
{1}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頁。
{2} 龍彼德:《分析之綱:我的詩路歷程》,見《痖弦評傳》,三民書局2006年版,第87頁。
{3} 痖弦:《從西方到東方》,《創世紀》1982年第10期。
{4} 張默:《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源成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5} 熊國華:《論痖弦的詩》,《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 龍彼德.痖弦評傳[M].臺北:三民書局,2006.
[2] 張默.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M].臺北:源成出版社,1997.
[3] 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4]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5] 痖弦.從西方到東方[J].創世紀,1982(10).
[6] 蔣忠波.論戴望舒詩歌中的戲劇性因素[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05(2).
[7] 熊國華.論痖弦的詩[J].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1994(4).
作 者:蔣一晨,文學碩士,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學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張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