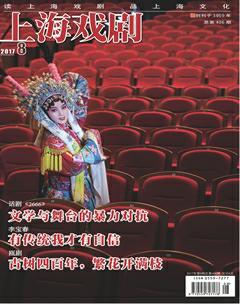文學與舞臺的暴力對抗
羅磊
對于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這部史詩般巨著的名聲與厚度,我并不想再絮絮叨叨,但首先要說的是:我們在天津看到的《2666》并不是這部作品在戲劇舞臺的第一次呈現。第一位挑戰它的是美國知名戲劇導演羅伯特·福爾斯(Robert Falls),去年二三月份在芝加哥演出。同年七月,朱利安·戈瑟蘭(Julien Gosselin)導演的12小時版本在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上演。沒有看過前者,沒法將兩者比較,但由于戲劇節的影響,這部法國版《2666》顯然有了更多的知名度與關注度。
忠于原著的宏大敘事
歐洲導演對站在全人類高度的宏大題材作品(通常時間超長)有著天然的挑戰欲望,如姆努什金8小時的《浮生若夢》、楊·法布雷24小時的《奧林匹斯山》等,時間的長度雖不意味著作品的高度,但對于導演的復雜敘事能力無疑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原著有5個部分,戈瑟蘭的版本也按5個部分劃分,每部中間安排休息,因此標榜12個小時的演出實際不到10個小時。
第一部:文學評論家。歐洲知識分子靈與肉的追尋。
4位歐洲知識分子,法國的讓-克勞德、意大利的莫里尼(他坐著輪椅)、西班牙的曼努埃爾、倫敦的麗茲·諾頓。他們在德國的文學會議上相識,相互欣賞,在學術上相互支持,連接他們的紐帶便是對神秘的德國作家阿琴波爾迪的癡迷。一開場,4個人分別拿著話筒在舞臺上講訴各自研究阿琴波爾迪的經歷,如同讀書般的身臨其境,我便有了該劇忠實于原著的預感。
之后便是克勞德、曼努埃爾與麗茲之間的三角糾葛。他們的性愛發生在玻璃房里,隔著薄紗,避免了直接的赤裸暴露。知識分子之間靈與肉的糾纏通過手持攝像機同步投影在玻璃房上方,是戲劇,也是黑白電影,唯美又寫意。
第二部:阿瑪爾菲塔諾。美洲知識分子的不幸與苦悶。
這一部其實是全劇支線。圣特萊莎大學教授阿瑪爾菲塔諾在智利軍事政變后,與妻子女兒流亡到墨西哥圣特萊莎,不久他的妻子離開他去西班牙尋找詩人,阿瑪爾菲塔諾也變得精神錯亂。兩個拼接的玻璃房構成了教授的家,他將《幾何學遺囑》掛在玻璃房前的晾衣繩上,這是效法馬塞爾·杜尚。他與女兒隔著玻璃房對話,父女之間的隔閡就像玻璃,兩兩相望又觸碰不得。最后玻璃房里充滿了迷霧,這就是教授所生活的空間,沒有方向,他就像那本幾何書,孤零零掛在外面。
第三部:法特。富有正義感的紐約黑人記者。
一開場,一個前黑豹黨成員西曼開始了長達十幾分鐘的講訴,通過他的經歷展現時代的變遷。在原著中,他本是法特的采訪對象,作者大概想通過這個人物展開對種族、金錢,尤其黑人生存境遇的探討,為法特的工作境遇以及后來他與羅莎之間黑人與白人的情愫做鋪墊,他就像一個隱喻。但到了舞臺,這個人物就像從天而降,如果沒有讀過原著,有點讓人不知所云,倒不如拿掉。
后面便是法特在墨西哥圣特萊莎城采訪的遭遇,原著中,大量的對話本是發生在餐廳,但導演將法特了解兇殺案與結識羅莎的場景轉變到了夜店,于是就像小說中寫到的一樣“音樂叫女人發狂。電影叫我發瘋”。轟隆的電子音樂在狂暴嘶吼、迪斯科舞廳的刺眼燈光在舞臺閃耀刺激著觀眾的眼球,法特與眾人喝酒的場景被投影到玻璃房上方,就如他的新聞記者身份,非常紀實。
第四部:罪行。以文字的驚心動魄展現赤裸的暴行。
如何展現兩百多件女性兇殺案?波拉尼奧的做法是以文字直白描述每一個受害者的詳細情況,而戈瑟蘭的做法是將這些慘烈文字以字幕方式直接投影在舞臺上刺激觀眾眼球與大腦,冷漠至極。同時低沉嘶吼的電子音樂裹挾著冰冷的轟隆聲浪一陣陣敲打著觀眾的耳膜與心臟。再加上閃爍不定的刺眼燈光,這種挑釁足足持續了四十多分鐘,耳朵已經發麻,直到出現新聞節目才緩和下來,隨后轟鳴繼續,中間不斷繼續插入新聞節目、警察調查、追捕嫌犯、審訊嫌犯。
極端的暴力帶來極端的冷漠,知識分子們追尋阿琴波爾迪來到圣特萊莎,糾結他們的是作家與情感,城里的謀殺與他們毫無關系。美國報社只關心拳擊賽,而對駭人聽聞的謀殺案漠不關心。圣特萊莎城里的檢察官、警察、官僚們誤將案件草草了結。一切都是那么冰冷,戈瑟蘭試圖通過對大腦和心臟的猛烈敲擊,在劇場喚醒冷漠中的良知。
第五部:阿琴波爾迪。已不再高大的巨人。
阿琴波爾迪終于出現了,一位女演員站在右邊的玻璃房子上,對著麥克風講述漢斯·賴特爾的童年、二戰經歷、他的情感以及如何走上寫作道路并成為阿琴波爾迪。三個玻璃房子,一邊一個,中間的一個不停地前進后退,給人壓迫感,上方是象征納粹的“卐”字與象征蘇聯的鐮刀錘子標志,歷史的進程、二戰與大屠殺的慘烈都在女演員強烈情緒的訴說中道來。漢斯·賴特爾赤身裸體緊貼玻璃壁,扭曲身體,通過強烈的肉身感官將人性中的一切丑陋與無助赤裸地暴露出來。如果說圣特萊莎是和平年代的黑洞,那這一部則將戰爭的恐怖揭示開來。
對于這一部,其實我很期待導演會怎么處理阿琴波爾迪的一生,導演刪減了一些枝節,尤其一些性愛的片段(不知道在法國演出的情況如何),而且幾乎全部使用了旁白的手段,女旁白者非常激揚,開始還覺得不錯,但整部如此未免又讓人覺得一直處在一個調調,總感覺導演想急于收尾,不過癮。
總體來看,在文學敘事向舞臺敘事的轉化中,雖然對原著做了許多刪減,但依然保持了對原著的高度忠誠。
冰冷文字與舞臺暴力的對抗
雷曼在《后戲劇劇場》中提到:“新型劇場讓人們認識到:在文本和舞臺之間從未存在過和諧的關系,而總是充滿了沖突。”戲劇學者貝爾納多·多爾也提到:“文本和舞臺的結合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而總是停留在一種壓迫與妥協的關系之上。” 該劇各種舞臺手段運用之豐富、嫻熟令人贊嘆,空間、燈光、聲效,與文本形成強烈的對抗。
空間:《2666》僅地域就涉及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紐約、墨西哥等國家,更別說各種場景。導演通過三個可移動的大型半開放玻璃房肆意地切割拼接,里面可空可滿,布置成臥室、客廳、報社、旅館、夜店、警察局、審訊室等。玻璃又將觀眾與演員的表演間離,當玻璃房的紗簾收起,空間更具通透性,增加了寫意性。
影像:大量的投影與影像在當下的歐洲戲劇中已經成為常態。該劇通過大量的文字投影,推動情節發展,這在第四部分“罪行”中非常明顯,這是原作中最為暴力、血腥、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部分,最難在舞臺表現,導演取巧地采用字幕快速交代兇殺案,這種冷漠的方式令人刺激。然后就是手持攝像機拍攝的實時影像,比如第二部,玻璃房內外教授的精神錯亂、掙扎與上方的黑白影像相互交錯,形成一種非常意識流的復調。
這幾年,影像技術在我們的戲劇舞臺被大量使用。還不錯的有今年的青春版《狂飆》。糟糕的有去年的《大先生》,手持攝影并實時投影,令人不知所云,反感至極。似乎中國的導演都在趕時髦,我不媚外,但如果看過去年在國內上演的德國戲劇《共同基礎》以及這部《2666》的影像運用,你會覺得人家用的是那么自然與和諧。
音樂與燈光:就像阿爾托眼中的那樣,音樂是“為了通過人體器官,直接而深刻地對感應力發生作用”,“燈光對人的精神會起特殊作用……要在燈光中再加入精致度、強度和稠度,以制造熱、冷、憤怒、恐懼等效果”。劇中大量的粗暴電音與無常的冷峻燈光,毫無溫度,尤其第四部,直接把劇場的觀眾帶入萬丈深淵之中。
所有文本之外的要素是如此暴力,就像一把冰鎬一鎬一鎬砸在冰冷的文字之上,砸入觀眾的眼里、耳里、心里。
國內青年導演
面臨的鴻溝與危機
回到該劇首演的2016年的阿維尼翁戲劇節,有兩位法國年輕導演曾引起我的關注。1981年出生的讓·貝洛里尼(Jean Bellorini)執導5個小時的《卡拉馬佐夫兄弟》(Karamazov)(2014年執掌法國圣丹尼國家劇院,并在當年法國戲劇界最高榮譽“莫里哀戲劇獎”中獲得公立劇院最佳導演以及公立劇院最佳戲劇劇目獎)。另一位就是戈瑟蘭,29歲,執導12個小時的《2666》,這是他的第6部話劇作品。我突然意識到,歐洲一批30歲左右的年輕導演正在迅速地涌上西方戲劇舞臺的中央,就像他們的前輩曾經做過的一樣開始“搶班奪權”。
戈瑟蘭的《2666》并不完美,但他展現的嫻熟導演技巧,對各種戲劇要素(文本、空間、燈光、聲效等)的掌控能力,令人嘆為觀止。他們對于宏大敘事文學作品的勇于挑戰,讓我意識到,他們的“搶班奪權”是憑著自己的實力在說話。若把目光放到國內,你能說出有哪個30歲左右的國內青年導演能有戈瑟蘭在《2666》中所體現的掌控力。就導演培養層面而言,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種失望,甚至絕望,我們年輕一代的導演與歐洲的同齡人已經有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總覺得伊沃·范·霍夫、羅密歐·卡斯特魯奇、楊·法布雷這些歐洲當紅導演厲害,可他們的作品是基于對歐洲文化根源、基于對哲學、藝術、美學、文學、科技的深層次思考與運用的結果。不想談論體制、資金、導演培養方式的因素,只是試問,我們有多少年輕導演會像戈瑟蘭那樣經常閱讀厚重的文學作品;試問,我們有多少年輕導演會比較深層次去思考哲學、美學、科學問題,真的很少。只愿下個十年,這道鴻溝不再大。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博士生)
攝影:錢程 段超 Simon Goss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