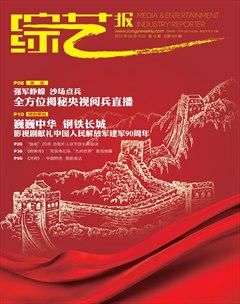《河神》:中國特色 美劇表達
陳丹
沒有流量明星,年輕團隊操刀——由愛奇藝與工夫影業聯合出品、閑工夫制作,改編自天下霸唱同名小說的網絡劇《河神》表現令人驚艷。開播以來,該劇播放量已突破6億(截至8月7日),評價人數不斷攀升,豆瓣評分穩定在8.1左右,口碑堅挺。
“在這樣一個新行業(網絡劇)的新時代下,按照‘碼大牌‘攢盤子的老套路,以‘做算術題的方式去拍攝和創作,已經沒有保障了。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很可能觀眾已經準備好拒絕。”《河神》導演田里在自己的微博中寫道。他形容《河神》的制作與播出是在“蹚一條新河”,創新與突破是愛奇藝、工夫影業對這個項目的共同期待。
人物、邏輯、內容——愛奇藝版權管理中心副總經理、《河神》總制片人李蒞櫻認為,未來網劇的制作一定要著重于這三方面。“愛奇藝一直致力于做‘中國特色的美劇。所謂‘中國特色是指內容要貼近中國本土文化,但在制作上向美劇看齊。《河神》講述了很多民國市井文化中的神秘內容,但戲劇的表達方式上更靠近美劇。”
“學院派”年輕團隊
陳國富拍板決定讓田里執導時,不過見了他兩面——一次是簡單的面談,相互認識;第二次田里做了導演闡述式的項目提報。時至今日,田里仍笑言,還是覺得陳國富的決定某種程度上有些“草率”。
整個《河神》的主創班底基本都是“學院派”背景。田里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制片人常犇是田里的同級本科管理系同學,被陶昆(《河神》出品人)譽為年輕一代制片人中的奇才。常犇既懂制片又懂創作,早年在校期間導演的短片曾入圍戛納短片獎。田里表示,常犇在這個項目上給予他極大幫助。“無論多么艱難,甚至連我都要妥協的時候,常犇也一定會站出來力保內容不失水準。”在《河神》121天的拍攝過程中,有兩次計劃外的跨省大轉場,兩大重場戲段落重拍,然而這個85后的年輕制片人維持了這個龐大劇組的正常運轉,不超支、不超期完成拍攝。
攝影指導馮思慕是電影學院2009級攝影系研究生,電影學院畢業后考上了AFI(美國電影學院)攝影專業繼續學習。他為《河神》帶來很多好萊塢的制作經驗和技術,但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在周期15天以上的劇組擔任過攝影。田里形容他“瘦小文弱,卻能扛著機器跑一天”。
美術指導邢柳亭是電影學院2001級美術系學生,劇中“小河神”居住的破廟是他將當地一座有香火的廟改造而成。造型指導袁斌是主創團隊中唯一的老前輩。從《鬼子來了》開始,她一直是姜文導演造型團隊中的骨干。田里表示,袁斌的行業經驗是他們這個年輕團隊的定心丸,“演員、美術、攝影等各個部門都有受益。”
除主創外,李現、張銘恩、王紫璇、陳芋米——《河神》的四位主演也都是90后年輕演員。“未來互聯網市場就是找合適的人演合適的角色,而不是說拿錢砸某些人了。”李蒞櫻表示。除了角色的適合度外,田里對演員提出的要求是必須能吃苦。“《河神》拍攝周期很長,預期會非常辛苦。我需要主演全程陪著我死磕,跟我一起扛到最后,不計較候場時間、不計較工作量、不要求食宿規格,理解我隨時有可能改劇本、做出各種調整。”
電影質感與網劇創作規律
導演陳可辛在今年“愛奇藝世界大會”上面的講話,李蒞櫻反復看了三遍。“未來的網劇市場是真正to C的市場。”陳可辛發言結尾的一句話讓李蒞櫻感同身受,“我們做《河神》的時候,也是奔著toC的想法去的。”
在田里看來,網劇最大的特點,即創作者和觀眾的“距離”非常近。電腦、手機、PAD,觀眾幾乎都是捧著這些移動設備觀看網絡產品,但所有的細節處理不能因為播出介質多為小屏而放棄對工藝的要求。《河神》中,田里首先想要實現的是“電影感”。從場景到造型,從拍攝到剪輯,《河神》都是按照電影邏輯推進。每個群眾演員的造型、每個道具的質感、每個特效鏡頭的邊緣細節、每個畫面的調色方案,《河神》完全是依照電影大銀幕的播放規格要求,最后的成片也都是在大尺寸投影上審核,做到“盡可能地精細化”。追求電影質感最大的代價是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長、成本高昂,但田里認為這是優質網劇必須具備的。
“網劇還有個特點非常重要。說好聽點,是我們要尊重觀眾;說得功利一點,是網劇的‘關閉成本太低了。”田里感嘆。只要讓觀眾有一絲絲的厭煩或走神,鼠標輕輕一點,HOME鍵隨意一按,他們便可關閉視頻。因此,如何把觀眾“鎖住”,拉近與他們的“內在距離”,成為網劇創作的重要課題。“情節推進速度一定要快,把信息量‘轟上去是最有效的辦法。”田里介紹。《河神》的案件進展幾乎不停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集結尾都留有懸念,每周結尾會營造更吸引人的懸念。《河神》播出第一周結尾時,200多具尸體浮現河面,很多網友表示已經等不及第二周的更新了。
為了實現快節奏敘事,《河神》幾乎沒有“廢戲”,力求每一場戲都具備信息量。觀眾看到的每集片尾彩蛋是因為節奏拖沓而被整場減掉的戲份,制作團隊從中整理出24段放在片尾。第一集中,“小河神”郭德友發現丁義秋尸體被綁在玄武銅像上的那場戲原本是水下長鏡頭。為了這個鏡頭、劇組各部門辛苦良久,實拍過程艱辛,特效制作也花費了很多功夫。但田里最終還是在劇集上線的前一天把這個鏡頭剪碎了,因為“它只有場面,單純在炫技,沒有太大信息量,觀眾很可能會失去耐心”。
“當然,這些所謂的創作規律,只是針對現在的創作環境和受眾觀影習慣。隨著時間的推移,制作環境會變化,觀眾口味也會改變,國產網劇的出路應該是跟美英劇看齊。”田里說,“我們也應該拍出像《冰血暴》文學性這么強的警匪劇,像《真探》這么極致講究的探案劇,像《奧利佛基特里奇》這么細膩動人的家庭劇。”
在他看來網劇不應該有“規律”,任何創作都不應該有“規律”。“如果一個創作者聲稱自己找到了‘創作規律,那他是悲哀的。一輩子都按照套路創作,不給自己出難題,不往自己挖的坑里跳,該多么無趣。只有根據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去創造屬于這個作品獨有的魅力,才是每個創作者激情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