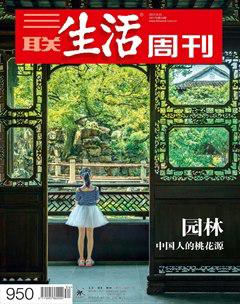余華:溫暖與百感交集的旅程(7)
朱偉
《兄弟》是余華篇幅最長的小說,上下部50多萬字,證明了他的體力。50萬字沉甸甸的,讀起來卻仍然不覺得累。余華自己的說法,這部長篇最早動筆于《許三觀賣血記》發(fā)表后的1996年,寫了兩三萬字就放下了。等撿起來再寫,2004年了,很順利,用了一年多就寫完了。“現在看,是命運的安排,1996年時覺得中國的變化很大,決定寫。到2004年再看,1996年的變化不算什么了,所以,2004年才是寫這部小說的最佳時機。”因此,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寫天翻地覆的造化弄人。我問他1996年寫的兩三萬字是什么?他說,上部開頭部分,也就是李光頭在廁所偷窺,被趙詩人揪住游街的情節(jié)。那年代,在公廁里確實能聽到女廁那邊的聲音,我下鄉(xiāng)的地方,簡易公廁只隔了一層板。余華的黑色幽默手段,虧他想得出來,能把頭插進蹲坑,“就像游泳選手比賽時準備跳水的模樣”。

我覺得,余華的寫作特點是“鋒利”,礪乃鋒刃,這鋒利指他能銳敏切割出現實的斷面,讓你直視筋髓組織。好刀鋒利不見血。換一個角度,他喜歡用“力量”,他說,他崇尚“用力量寫作的作家”。我以為,他是以鋒利來體現“力量”。他喜歡海涅的詩句:“生活是痛苦的白天,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余華的鋒利直接體現在這部小說的結構上:他以14歲的李光頭的偷窺為開頭,李光頭看到了5個屁股,最重要的屁股是林紅的。他用洋洋灑灑一節(jié)的篇幅,寫從派出所民警的詢問始,小鎮(zhèn)上一堆人對林紅屁股的興趣。李光頭就用他掌握的“稀缺資源”,做起蹭吃面條的生意,不僅鋪墊了林紅,也鋪墊了李光頭的生意腦袋。
這部小說的結構精妙在于,李光頭14歲時的偷窺,其實是一個“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引子。這個引子后,才開始上半部李光頭的父親偷窺,淹死在糞坑,宋凡平走進這個家庭的敘述。上半部完全是為下半部林紅這個人物的正式出場作鋪墊的,一般作家大約都不會采用這樣的結構方式。余華要極盡鋪墊之能事——他寫宋凡平在燈光球場上高大魁偉,一手一個舉起宋鋼與李光頭、抱起李蘭,寫李蘭被他的魁偉衛(wèi)護的幸福,是為了鋪墊婚后一年,他就為了去上海接李蘭的承諾,而被活活打死。更殘酷的是,為了鋪墊李蘭的錢只夠買一口最小的薄皮棺材,棺材里裝不進他的尸身,身體進去了,腿在外面,就只能砸斷了膝蓋,將小腿放在大腿上。膝蓋顯然是隱喻。
上部與下部,余華寫的都是變化的殘酷。上半部里,今天宋凡平還是燈光球場上眾人矚目的扣籃球星、高舉著最大一面紅旗紅光滿面的旗手,明天就被戴上高帽,打成鮮血淋淋。那個長頭發(fā)的孫偉,今天還耀武揚威,因為其父是宋凡平的看守,明天父親資本家的身份被發(fā)現,他就因衛(wèi)護長發(fā)而被割斷了動脈,他母親成了赤身裸體的瘋子,父親的精神徹底崩潰,就將鐵釘釘進自己的頭顱自殺。這是“文革”。
對我而言,上部中最難卒讀的,就是宋凡平逃出倉庫,在棍棒下一次次掙扎著也要上車,最后“身體像漏了似的到處噴出鮮血”的情節(jié)。初讀與重讀,我都是有意避開這殘酷,讀完下部,再返回來忍受這赤裸裸的血腥。上部寫宋凡平的死與李蘭的死,目的都是鋪墊宋鋼。下部里,宋鋼跟著騙子周游去走江湖,甚至做假胸手術屈辱地推銷“豐乳霜”,也是為了讓妻子“無憂無慮生活一輩子”的承諾。而李蘭的死,是為了讓宋鋼答應,“不管李光頭做了什么壞事,你都要照顧他”,是為了讓宋鋼承諾:“剩一碗飯,我會讓李光頭吃;剩一件衣服,我會讓李光頭穿。”在這樣的鋪墊下,下部,寫翻天覆地變化下的李光頭、宋鋼與林紅——當李光頭變成超級巨富,宋鋼下崗后變成一無所有,唯一的“財富”,就只剩下林紅可以轉讓了。我聽很多年輕讀者認為,下半部與上半部風格不符,或認為下半部不如上半部。其實,上半部,有了宋凡平才有宋鋼,有了宋鋼才有相濡以沫的兄弟。下半部,則是鋒利地切割兄弟的內涵——林紅是兩兄弟的結蒂,宋鋼遺書中用李光頭所說的“哪怕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們還是兄弟”,其臥軌,實際就構成比他父親之死更深刻的悲劇效益。
下部李光頭、宋鋼與林紅的關系,余華是以堅硬的邏輯來體現他的鋒利的:一開始,當李光頭以他的組織能力成為福利廠廠長后,認定林紅非他莫屬,想盡種種辦法,越追求就越把林紅推向宋鋼。此時,李光頭蠻橫地說,“林紅是我的”,以兄弟要挾,宋鋼就做到了不惜傷害林紅。而宋鋼因傷害了林紅要自殺,李光頭一句“兄弟也一樣宰了”,卻覺悟了他,使他真的走向林紅,兄弟齟齬了。但李光頭落難,宋鋼以林紅每天給的零花錢救濟他,兩人在垃圾堆前一起吃飯,做到了“剩一碗飯,也會讓李光頭吃”,溫馨感人。李光頭也非混蛋,他發(fā)達了,讓宋鋼做他的副總裁,給林紅一筆錢,保他們衣食無憂。其實,如果宋鋼做了副總裁,或者林紅告訴了宋鋼李光頭救濟的真相,后面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fā)生。但宋鋼“我沒有這個能力”的自卑與李光頭“不能讓宋鋼知道”的囑咐,也都合情合理。于是,宋鋼為了讓林紅過上好日子,就只能跟上周游,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必然。宋鋼一去不返,李光頭買來奔馳寶馬,讓林紅揭幕,這個關鍵的轉折點,余華注意了寫林紅的憂郁、苦笑、不知所措,到最后關頭,她還哀求地叫起宋鋼的名字。但李光頭給了她從未有過的快感,蘇醒了她的性愉悅后,倫理問題就變成鋒利的邏輯——李光頭給了宋鋼從未給她的東西,給了她兩性關系的本質,這時候,歷盡艱辛只掙回3萬元回鄉(xiāng)的宋鋼,就必須選擇死亡了。
我理解,從情節(jié)因果看,這部小說的上部是下部的鋪墊;從社會面貌看,下部又與上部,形成了兩個時代的對照。上部的凄慘故事是“文革”對人性的踐踏,是一場政治運動調動激發(fā)了斗爭中的獸性。下部呢?表面看不再有斗爭與血腥了,只不過社會形態(tài)顛倒了——令李蘭擔憂的李光頭靠做垃圾生意就能成為巨富,成了巨富就成為全鎮(zhèn)的權力意志。相對應,踏實本分的宋鋼就成為喪失了尊嚴的弱者,不用政治運動,金錢所構成的權力,從更深刻的內心,構成了殘酷的殺人效果。絕非“倫理顛覆”這一簡單的論斷,就可論說李光頭、宋鋼、林紅這三角關系,轉了一圈而顛倒的悲劇。
我理解余華這部長篇是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表達了“新批判現實主義”。這個“新”就體現在通過其表達手段,鋒利地揭示這兩個時代關系的深度。傳統(tǒng)的“批判現實主義”揭示的只是現實本身。余華后來發(fā)表了他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時的幾則日記,其中一則寫到他對上下部兩個時代社會形態(tài)的看法。他說,“文革”是一個極端,今天是另一個極端,是“文革”的極端壓抑反彈出了今天的極端放蕩;壓抑與放蕩,從兩個極端,都開放出黑色的惡之花。那么,余華站在什么立場呢?他說,他希望這部小說能使人人意識到,我們需要自救。(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