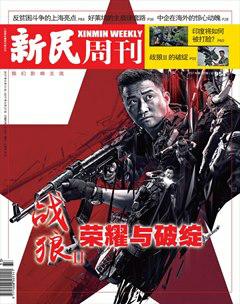在越劇的故鄉,造一個小鎮安放夢想
呂明合
做了一輩子戲劇,這次,導演郭小男決定找個地方,從容地安放生活和藝術。
夏夜,剡溪的流水潺潺穿過村莊,環繞的林木帶來鳥獸盤桓的氣息。月光、山色、湖水,有戲文在青瓦屋頂和原木柱梁間游弋,咿咿呀呀地響。
11年前,越劇百年,郭小男和妻子茅威濤被拉回嵊州祭祖。那是他第一次去剡溪,越劇的發源地。11年后,郭小男再度歸來。他決定把接下來的十年,交給此地。
“人不到那里,感受不到水質的清澈,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做了一輩子戲劇的導演郭小男,這次決定找個地方,從容地安放生活和藝術。從此,讓戲劇與自然渾然一體地融合,戲劇與村莊之間,將形成一種微妙而特殊的共生共存的關系。
“做了這么多年戲,特別向往著能有這樣一個所在”,郭小男說,“去回歸,去圓夢。”接下來,以十年為期,他準備在嵊州干成一件事:做一個國際視野的戲劇小鎮。
夢里桃源,不負江南

上圖:嵊州原生態風景。
他把回歸和夢放在這個小鎮里。郭小男直著腰坐在浙江音樂學院辦公室的沙發里,辦公桌前,小鎮規劃的藍圖攤開,一切盡在掌握。
去年9月,嵊州鄉賢、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突然找上門來,想在家鄉做一個戲劇小鎮。這事兒或許也只有他能干——郭小男最為人熟知的身份,除了小百花越劇團團長茅威濤的丈夫,更是國內著名的戲曲導演和學院教授,在國內戲劇界朋友遍天下。
小百花藝術團的十幾部經典,《孔乙己》《梁祝》《春琴傳》《春香傳》《江南好人》《寇流蘭和杜麗娘》等等均出自他手。除了越劇,他還執導過享譽盛名的淮劇《金龍與蜉蝣》、昆曲全本《牡丹亭》《西廂記》和話劇《秀才與劊子手》,同樣部部經典。而梅蘭芳之子梅葆玖的遺世巨作《大唐貴妃》,亦是郭小男的導演作品。
宋衛平素有情懷,把回饋家鄉變成了常態。這回,他又一次出錢出力,期冀著生活品質的徹底改變,建設一個將來可以依靠自身發展,形成自主循環能力的生態藝術小鎮。
落戶浙中的這座理想主義小鎮,并不具有說服力。“這事能行嗎?大家比較懷疑。”郭小男受人之托,幾經思考,定下了自己的思路:以越劇為核心,山水為承載,打造世界級的戲劇生態環境。
規劃中的小鎮,將會有三個大劇場,十多個戲劇工坊,既有經典的延續,安放傳統劇種,又有實驗創新,探索先鋒的戲劇。并將原來的嵊州藝校升級為大專,為小鎮和全國的藝術發展,培養高品質的專業人才。在商業上,他同時也配置了體驗田園生活和現代化的商業娛樂場所。
設計中的晚宴劇場,舞臺緊靠剡溪北側。這將是一個四面環繞觀眾的圓形劇場,具備晚宴功能。中央是水中戲臺:“想象一下,每到夜晚,水舞臺上演著越劇名著《追魚》,演員在水中起降升落,高潮時,舞臺背后的墻體洞開,剡溪在山體的環抱中涌入眼簾,水的后方是小鎮、是群山,如此一刻,激蕩人心。”郭小男描述著劇場,仿佛身在其中。
這是一個滿足娛樂、大眾消費的劇場,而劇場創意,緣起越劇水鄉社戲的發端。

上圖:施家岙古戲臺。
與之相對應的,是另一個“經典劇場”。“讓中國的元雜劇和明清傳奇戲劇,作為演繹主流,讓世界上各種版本的莎士比亞劇戲劇,在此落地”。郭小男說,經典劇場要呈現的,是“戲劇歷史文脈上的經典,讓東西方戲劇文學在此生根,繁華、對話、互映”。
經典劇場的獨特之處,在于兩個劇場共用一個舞臺。觀眾們看完明清傳奇,出去轉一圈,舉一杯紅酒再回來,對面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舞臺上,莎士比亞經典劇目已經開演。同時,這個劇場還保留了兩面同時觀看一個演出的可能性,如越劇《寇流蘭與杜麗娘》,即可拆解兩面分看,又可合二為一地同時演出。
此外,戲劇小鎮還將設置了十個中小型戲劇場——戲劇工坊。讓戲曲、話劇、音樂劇、舞蹈、曲藝、實驗劇、先鋒劇、搖滾音樂等藝術門類各得其所,無所不融。讓國內國外的戲劇藝術在此狂歡,讓觀眾和年輕人感受戲劇,參與實驗,享受生活。
其中最為特殊的理念,是建造一個專門演出瀕臨絕跡的劇種、劇目的劇場,名為“天下第一團”。讓那些獨自撐起劇種的唯一劇團,在這里找到常年可以演出的平臺。“把保護和傳承中國戲曲藝術的文化自覺,在越劇小鎮里落到實處”。郭小男如是說:“保護和創建一個劇種的生存形態,激活她,讓人們重新認識她,然后把它交付給今天的時代和市場,實現我們的擔當”。
三類劇場,勾勒出了越劇小鎮對戲劇文化的精神定位、原鄉情懷和追求架構。
而準備升級的嵊州藝校,也將成為小鎮的另一藝術板塊。新的學校力求完善適應藝術發展和市場需要的教學培養體系,為越劇小鎮和社會源源不斷輸送人才。
在郭小男的暢想中,人們將從四面八方的城市來到這里,看戲,度假,休閑,旅游,以逆都市的文明角度,體驗田園生活的質感。他為這個小鎮定下了主題:夢里桃源,不負江南。
傳承文脈
在郭小男看來,江南不僅是柔軟唯美的存在,其中更流淌著中國的文脈,從春秋吳越,到南北宋優雅的生活方式。只是到了今天,文脈已經斷裂。
“小鎮要拾撿起江南文脈的品質生活”。在郭小男的理解中,戲劇是人類文化歷史不可或缺的一支文脈。在傳統文言的二十四史之外,另有一套話語體系,“正史是一條線,民間是一條線”。古時候秀才少,傳承文脈的就是戲文。更多人的道德信仰和忠孝節義,都是從戲文上得來。“這條文脈的梳理不能斷,這才是為什么我們要弘揚優秀傳統和戲曲文化的根本所在”。 ‘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六百年前王實甫在《西廂記》里發出的人類追求先進人文理念的哲思和呼喚;而湯顯祖的《牡丹亭》,讓一個16歲的女孩子在夢幻中踐行關乎人生情感和理想的感受,于今天就是當代版的《人鬼情未了》”,說起這些,郭小男滔滔不絕,頗為感慨,“國家重啟弘揚傳統文化的戰略意義,就是告誡國人,勿忘文化根本,不能追求現代文明而忽略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這是我們與世界文明競爭的精神源動力”。
文脈不能斷,郭小男想在越鄉重拾:“這是越鄉的根”。當年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穿著花布棉襖,順著剡溪走了273公里來到上海。如今,從十里洋場一番打拼,姑娘們又回來了。回到越鄉,卻已是新的起點。面對這條文脈,郭小男想做的是通過越劇小鎮的創立,延續中國戲劇的繁盛,并與世界戲劇共鳴。小鎮的投資人宋衛平很同意這一觀點,他說:“戲劇不開放,不走向世界一定不會強大的。”
越劇在它的出生小鎮,顯得親切卻又陌生。郭小男管這叫“不識越劇真面目,只緣身在越鄉中”。在郭小男看來,越劇是一個“對傳統的繼承性最具有現代意義的劇種”。
拒絕在傳統里打轉
茅威濤問郭小男:“十姐妹回來該穿什么,旗袍?西裝?”
其實無論穿旗袍,穿西裝,對茅威濤和小百花劇團來說,都不會是負擔。
2012年,郭小男根據布萊希特的話劇改編,排了越劇《江南好人》。在一片非議中,茅威濤第一次扮演了女人,小百花第一次演出了時裝戲。小百花用自己藝術的方式,回答了這個話題。郭小男帶著小百花,沒少干出格的事兒。
18年前,為了越劇《孔乙己》,茅威濤甚至連頭發都剃了,與傳統老戲截然不同的劇目一出世就震驚四座。“以美飾丑,以丑為美,這個戲可能讓茅威濤真正進入了舞臺藝術家的行列”,郭小男說。
隨后的創新變得更加自由,小百花排日本戲《春香傳》,排朝鮮戲《春香傳》,甚至把莎士比亞劇本與湯顯祖的戲合在一起,創作了《寇流蘭和杜麗娘》去歐洲巡演。回國后,這出戲還是票房爆棚,演出時增賣站票。
小百花向前的步子越邁越大,但郭小男有足夠的底氣:“小百花演出傳統劇目,《西廂記》《陸游與唐琬》《梁祝》,照樣立得住啊!”
“要把小百花打造成既有傳統戲的能力,又有現代戲劇格局的一個可以趕超世界先進藝術理念和技術水準的劇團。它既認知自己的傳統,也存有世界文化的包含性,既有茅威濤這一代對于經典劇目的表述能力,也要培養出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人,適應藝術當代認知度的一種能力”。
至于那些持不同意見的批評聲,郭小男很是坦然:“我從來沒有壓力,別人愛說什么是他的事”。
“戲劇就三件事,劇目,劇團,劇種”,郭小男道出真相:“劇目不好看,劇團就會萎縮,慢慢地劇種就沒了。觀眾不去培養,市場不去占領,300多個劇種漸漸萎縮,說沒就沒。劇目怎么辦?劇團怎么辦?劇種怎么辦?”在郭小男看來,這該是戲劇人心里一桿秤,每個人都應有文化自覺的天平來衡量自己的義務與擔當。用這三個問題自問,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唯美、民族、高端”的路。
重構對戲劇的追求
接通市場——從小百花越劇團到戲劇小鎮,郭小男總結出戲曲發展的核心。
傳統的戲班制、四大名旦,無一不是由市場挑揀出來的。紅了才能挑大梁,紅不了就拿不到吃飯的包銀。這就是市場,這就是觀眾。拿到市場上來,戲曲才能成長。這就需要“更新腦子,更新觀念,更新技術,進而更新觀眾”。 更新的前提,就是源源不斷的培養人才,創造與時代審美需求同步意義的優秀劇目。
郭小男對嵊州藝校信心滿滿。如在小百花教育培養新人一樣,他要培養的戲曲演員,精通中國戲曲,刀槍靶子能練;但必須街舞也跳,爵士也玩兒,搖滾也懂。“傳統戲曲人才培養的方法,是師父教你幾出戲,學會了你就出師了,學生以像師父為目的。于是舞臺上到處是小XX,小小XX。而在小百花不一樣,這里不僅教戲,更要教育演員創作角色的方式方法”。郭小男強調:“觀念是架構藝術精神的根本,可以重構你對技術的認識,繼而重構你對戲劇追求的目的。”如果觀念永遠在原來的體系當中,就只能不斷地重復自己,所以“接通時尚和潮流以及先進理念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改變和更新自己的藝術觀念”。
改造后的嵊州藝校,學員們將不再只學幾個折子戲,還要接觸各種各樣的藝術形態。郭小男打定主意,到時候,他那些大師朋友,都要拉去講課。請張紀中講制作,請李安教電影,邀金星教現代舞,請牟森上先鋒戲劇課……總之,他要學生們“掌握現代人關于藝術與技術的生存能力”。
郭小男做了一輩子的戲,自嘲“五谷不分、四體不勤”,拿拿筆,排排戲是他的本行,如今卻要主持一個戲劇小鎮的構建,用來安放理想。“我們會做到準世界級。”郭小男給自己定下了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