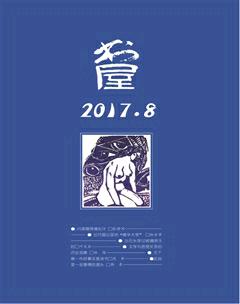道并行而不相悖
2015年2月,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原詩》第一輯,副題是“漢語詩學融通的可能性”。同年6月,由同濟大學詩學中心編選的《中華新詩檔案》第一輯,也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兩部書,無心插柳地成為當年度漢語詩壇的一個事件,忝列《非非》、《非非評論》聯合評選的“2015年中國詩歌界十大新聞”之一。作為一部學院派的詩學集刊,《原詩》的努力被譽為“開辟漢詩學術和研究新模式”;而旨在為全球華語詩人立此存照的《中華新詩檔案》,則被稱作“一部詩學視野廣闊和開放的漢詩選本”。這些不虞之譽,我們從來不敢自詡,只是覺得路還很長,不能就此止步。
一晃兩年過去,2017年,《原詩》第二輯將由岳麓書社推出。頗有紀念意義的是,2017年,距離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第一首新詩的1917年,正好一百年。所以,這一輯《原詩》的副題是——“古今與新舊的對話”。
說實話,在組稿中,我們并未刻意集中于某一視角和論域,而是依舊延續當初的辦刊思路:辨異玄同,折衷彌縫,希望能在古今、新舊、中西之間,尋找漢語詩學的轉圜余地與共生空間。盡管,這樣一種看似曖昧或騎墻的詩學姿態,或為執著己見的詩人學者們所不取,但我們立意已定,且已在詩壇和學界看到了某種從容商量、平情討論的端倪,故甚望沿著既定方向走下去,至于能否曲徑通幽,柳暗花明,則只好聽天由命。
眾所周知,自新詩誕生以來,圍繞新詩與舊詩的爭論甚至爭吵,就一直沒有消停過,至今依然不絕于耳。對此,我們不愿意、也未必有資格充當仲裁者,更不想“意必固我”地為任何一方背書,我們想做的只是一種類似“搭橋”的工作。正如三國時的天才哲學家王弼在詮釋“言意之辨”時,別出心裁地添加一“象”的范疇,遂在“言”、“意”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彼我的橋梁一樣,我們愿意在“新詩”與“舊詩”的二元對立中植入一個“古詩”的視角,以求緩沖前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揆諸中國詩歌的形式發展史,恐怕誰都不會否認,在“新舊”詩涇渭分明的體式對立背后,其實還隱含著一個作為大背景的“古今”分野,拈出這一個“古”字,真可謂境界全出!你會發現,中國詩歌史完全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且相應地形成了三個傳統:自上古以迄六朝是第一階段,形成了近兩千年的古詩傳統;自隋、唐降及清末、民初是第二階段,形成了一千五百年的近體詩或曰舊詩傳統;而自1917年以來的整整一百年,則是第三階段——無論你承認與否,也已形成了百年新詩的小傳統。我曾在拙著《古詩寫意》的自序中說:
新詩—舊詩—古詩,這是一條上行的線索。古體詩—近體詩—新體詩,這是一條下行的長河。……溯源,不是為了截流,而是為了引水——下游正是枯水期。鑒古,不是為了泥古,而是為了察今——當下不缺古樣板。你會發現,古詩和新詩,其實有著某種基因的相似性,而真正的詩性,詩意,詩境從來沒有古今之分。有的古詩,不分行,還是詩;有的新詩,分了行,也未必是詩。〔1〕
仔細打量漢語詩歌的這三個傳統,我們會發現,這好比是一個不易覺察的“洋流循環”,新詩在近體格律詩那里找不到的“同質性”,反倒可以在古體詩中尋覓到形式或者語言上的“基因”。所不同的是,古體詩和近體詩的共同傳統——音樂性——正在被新詩當作“包袱”而徹底揚棄,僅此而已。
有趣的是,本輯的好幾篇文章如臧棣、董輯、李國華等人的論文,在論及新詩發展中的重要詩人和作品時,都不約而同地涉及了新詩相對于傳統詩、詞,其性質、前途、合法性乃至特殊性等問題。而著名舊體詩人楊啟宇先生和新舊詩兼善的青年詩人朱欽運(茱萸)的兩篇文章,則被放在“詩人觀點”一欄中“示眾”,以便突顯新舊與古今對話這一議題的現實張力。類似的爭論對關注詩歌的讀者而言也許并不陌生,但相信本刊的視角和立場,還是能夠提供一種“靜觀”和“圓照”的可能性。
順便說一句,今年春節期間引發收視熱潮的《中國詩詞大會》,通過國家媒體的強勢宣導,引起坊間熱議勢所必然。然而,如果以為全民誦讀詩詞就必然能夠迎來傳統詩詞的春天,則顯然屬于高燒不退的胡話了。事實上,個別評委在本該曲終奏雅時的“荒”不擇言、捉襟見肘,恰恰證明了《禮記·學記》“記問之學,不可以為人師”這一古訓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性。換言之,如果傳統詩詞僅僅停留在口頭的記誦上,而疏于教育的普及、技法的操練和現實的感懷,則終究不過是一場脂粉氣濃厚的多媒體娛樂表演,只能墮入“被消費”的尷尬命運而不自知罷了。不過,這都是題外話,不宜在此展開。
關于新舊、古今的詩學博弈,我們看到的情況往往超出既定的成見。比如,新詩派因為已經占據詩壇或者當代詩歌史書寫的泰半江山,故對傳統詩詞派并無太大偏見,只是執著于闡釋新詩的合法性與現代性。在為新詩辯護的文章中,董輯的《他山有玉》一文值得注意。作者借助兩位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和洛夫對于新詩的不同理解,闡明了即便在新詩人中,對于古典詩歌傳統的態度也是多元的,并非千人一面,冰炭不容。如余光中在《先我而飛:詩歌選集自序》中就說:
從我筆尖潺潺瀉出的藍墨水,遠以汨羅江為其上游。在民族詩歌的接力賽中,我手里這一棒是遠從李白和蘇軾的那頭傳過來的,上面似乎還留有他們的掌溫,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不過另一方面,無論在主題、詩體或是句法上,我的詩藝之中又貫串著一股外來的支流,時起時伏,交錯于主流之間,或推波助瀾,或反客為主。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詩,從莎士比亞到丁尼生,從葉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揚五步格”的節奏,那倒裝或穿插的句法,彌爾頓的功架,華茲華斯的曠遠,濟茲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滲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聽覺的深處。同時我又譯過將近兩百首英美作品,那鍛煉的功夫,說得文些,好像是在臨帖,說得武些,簡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總會學來幾招管用的吧。〔2〕
余光中認為:“古典的影響是承繼,但必須奪胎換骨。西洋的影響是觀摩,但必須取舍有方。”
相比于余光中的左右逢源、古今都不得罪,洛夫則認為,新詩難以格律化,但是新詩自有其形式,這種形式就是“一詩一形式”,新詩是形式和內容不可分割的一次性藝術創作,其形式因素很難被反復使用和上升、定型為“格律”。他說:
我一向鐘情于自由詩,我以為一個作品的偶然性是決定其藝術性的重大因素之一,而自由詩的偶然性遠遠大過格律詩。格律當然也有他的優點,否則不可能流傳數千年,但不可否認的是每種詩體用久了勢必趨于僵化,不但內在情感變得陳腐,對事物感受的方式也日漸機械化。抒情語言更是帶有濃烈的樟腦味。一般人仍留戀舊詩,是出于心理的固定反應,讀起來和寫起來都很方便,就像買鞋子,因有固定的型號,穿上合腳就行了。韻文時代已一去不返,用散文體寫格律詩,讀起來怪別扭的。語體詩還要押韻,感覺十分做作,很不自然。
不可否認,任何一首詩都有它的形式,它被創作出來的那個樣子就是它的形式,每首詩本身就是一種形式,它并不排斥中國韻味,它同樣可以具有漢語詩歌的優良品質。格律本身是一個機械性的載體,而一首詩的存在是形式與內容不可分割的有機體。我贊成詩應有形式感,但那不是格律,我也承認典律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典律必須依附于某種固定的形式。〔3〕
應該說,洛夫的“一詩一形式”和“詩歌偶然性”的論說,非常具有理論上的革命意義。其革命性并非在于反對傳統的格律和既定的程式化,而在于,他為每一首詩賦予了新的生命和獨特意義。洛夫甚至說,“詩,永遠是一種語言的破壞與重建,一重新形式的發現”。相比于舊體詩只有依賴于格律和形式才能存活并獲得尊嚴這一事實,洛夫的觀點不僅在空間維度上直面當下,而且也在時間維度上擁抱了未來。
無獨有偶,在廢名的《談新詩》一文中,也提到了“偶然的”問題:
讓我說一句公平話,而且替中國的新詩作一個總評判,像郭沫若的《夕暮》,是新詩的杰作,如果中國的新詩只準我選一首,我只好選它,因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比我的詩卻又容易與人人接近,故我取它而不取我自己的詩,我的詩也因為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較卞之琳、林庚、馮至的任何詩為完全了。〔4〕
請注意,廢名說新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無意中道出了新詩乍一出世,帶給世人的新鮮感和錯愕感。廢名還把新詩的創作喻為“生命的偶爾的沖擊”,這頗類似于陸游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相比之下,舊詩因為必須“習得”,即便“偶得”之后也必須經過格律的嚴格檢驗,不得漫漶于傳統的河床之外,自然就成了“應然的,必須的,是全體的一部分而非整個的”了。
可見,至少在新詩人看來,新詩之所謂“新”,本來就是要擺脫某種既定的模式,比如句式、格律等的束縛,盡情地、自由地展開生命和語言的偶然之舞。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詩”之“新”,并非僅僅是時間上或詩歌體式上的一個概念,更多的恐怕還是文化精神上或者說詩歌生命上的一種“新變”追求。這在中外文學史和詩歌史的宏觀視野注視下,似乎是一個十分常見而無須自證其合法性的現象。
然而,新詩是否就應該罔顧母語的千年傳統,一如脫韁的野馬一樣狂顧頓纓、一往無前了呢?百年新詩的實驗現場到底如何?如果不是借助中小學語文課本以及現代大學中文系教科書的強勢滲透,新詩的所謂經典作品,又有多少真正堪稱經典而無愧色?特別是,新詩占據學術的廟堂之高,卻在江湖之遠上應者寥寥,新詩的各種活動、刊物、詩人等也越來越成為一種不以職業為訴求的特殊“專業”,特別是,新詩人們在精英品格和自我期許上,倒是和舊體詩詞的作者們同樣“曲高和寡”。這些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無疑值得深入探討。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現代史上作為政治人物被聚焦的汪精衛,其實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舊體詩人。他1923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涉及新舊詩之爭的段落,讀之令人眼前一亮。汪精衛說: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于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作為編者,我不能不說,汪精衛的話與我心有戚戚焉。讓人略感遺憾的是,時過將近百年,今天的詩人們依然沒有走出“新舊古今”的形式陷阱和話語魔障。孔子說:“過猶不及。”《禮記·中庸》亦有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無論是新詩詩人還是傳統詩詞作者,于此皆當有所反思。新詩也好,舊詩也罷,雖同為語言的藝術,卻各有其寫作宗旨、審美標準與受眾期待,正如流行歌曲之與京劇昆曲,各行其道、各遵其理可也,如果各自強分軒輊,甚至以己所長輕人所短,甚至必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恕我直言,此皆非詩人應該有的大心量與大情懷。
還是用余光中的話結束這篇小文吧!他說:
古典的影響是承繼,但必須奪胎換骨。西洋的影響是觀摩,但必須取舍有方。多個十多年前我早就醒悟,株守傳統最多成為孝子,一味西化必然淪為浪子,不過浪子若能回頭,就有希望調和古今,貫串中外,做一個真有出息的子孫。學了西方的冶金術,還得回來開自己的金礦。〔5〕
“調和古今,貫串中外,做一個真有出息的子孫。”誠哉是言也!
編完這本集刊,再次感嘆光陰的無情。兩年光陰倏忽而逝,忙忙碌碌的我,只能交出這么一份微薄的答卷。感謝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的顧問團隊,感謝《原詩》的新老作者,更感謝因為種種緣分而閱讀過《原詩》的讀者朋友們,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無法走到今天。
(劉強主編:《原詩》第二輯,岳麓書社即出)
注釋:
〔1〕劉強:《古詩寫意》,岳麓書社2016年版,第3頁。
〔2〕余光中:《先我而飛:詩歌選集自序》,轉引自《余光中詩歌選集》第一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頁。
〔3〕《洛夫談詩:有關詩美學暨人文哲思之訪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頁。
〔4〕廢名:《談新詩》,轉引自《廢名集》第四卷,第1822頁。
〔5〕《先我而飛:詩歌選集自序》,《余光中詩歌選集》第一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