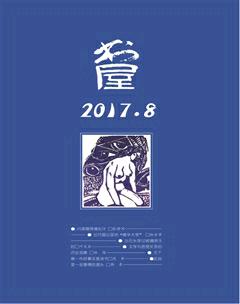此地是一些事情的源頭
韓秀
一
列夫·托爾斯泰在1898年出版的《藝術論》里有著這樣的論述:“將來的藝術和現在不同,它并不只是描寫少數富人們的生活,它將要努力于傳達人類共同的情感。”我看到這段論述的時候,剛剛讀完果戈理的小說《外套》,不禁心生疑問。果戈理的時代比托翁早,他去世的時間是1852年。托翁若是讀過《外套》,他一定會同意,果戈理所寫的正是貧苦公務員的生活,努力傳達的正是人類期待被了解、被尊重的共同的情感。而果戈理所寫的并非“將來的藝術”,而是離托爾斯泰很近的,時間上還超前一點的“當代文學”。
徐四金的小說《香水》在1985年出版時,歡呼聲大起,許多人熱烈地表示“這本書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歐洲表現”,“才華洋溢、引人入勝、獨一無二的原創幻想”。這樣的贊美也完全地適用于果戈理的小說《鼻子》,只不過,果戈理比徐四金早了不止一百年,比拉美魔幻小說也早了一個世紀。小說家納博科夫說:“果戈理的作品至少是四度空間的,能夠與他相較的同時代人,是毀掉歐幾里得幾何世界的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這話聽起來非常的驚人,但是,當我們進入果戈理文學世界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發現,現代小說、后現代小說、后設與解構之類的文學概念在果戈理的小說里都能夠找得到至為明顯的例證。換言之,此地,圣彼得堡恰恰是某些事情的源頭,在這里,我們能夠毫不費力地從果戈理的書寫里找到一把鑰匙,來解讀許多現代人寫的、多數讀者完全看不懂的文學理論。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真正欣賞果戈理的小說,這些小說離我們這么近,近到我們可以伸手觸摸到,近到幾乎是在書寫我們自己的困頓、疑惑、焦慮與希冀。原因何在?現代人同果戈理小說中的人物一樣還是沒有得到了解、得到尊重。“同情”這個情感因素在當年的圣彼得堡和當今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還是稀薄得無可救藥。而小說,這樣一種虛實交錯的體裁,在果戈理筆下被發展成多么有趣、多么可笑、多么可怕、多么“荒謬”的一種書寫啊。更為可貴的是,果戈理的書寫是親切的、周到的、溫煦的,絕對不以讀者看不懂為能事。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都是從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來的。”這句話概括了世界上千千萬萬讀者的心聲。我讀《外套》的時候還是一個十歲的孩子,那是一個相當簡陋的譯本,紙張的粗糙、字體的模糊、譯文的不甚通順都無法阻擋小說的穿透力。我跟著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一道穿著破舊不堪的外套走在徹骨的寒風里;我跟這位小公務員一樣地熱愛抄寫,只想著怎樣把字體寫得更漂亮;我甚至曾經跟他一樣完全不能了解,我從來不曾麻煩人而為什么人家卻總是不放過我?有人跟我說,阿卡基好不容易有了一件新外套卻被壞蛋搶走,他哪怕變成了鬼魂也沒能教訓那些壞蛋,卻把那個羞辱過他的“大人物”的外套剝了下來,而且從此便安靜了,不再折騰。這是什么緣故?我回答說,因為尊嚴比新外套還要重要。當年,我脫口而出的話跟我的處境有關。現在我還是會說這句話,因為人的尊嚴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時候仍然沒有得到尊重。一個人勤勤懇懇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是應當得到尊重的。但是,他卻被肆意批評、被刁難、被欺凌、被恐嚇,這個人在生前受盡煎熬,連一句完整的抗議都說不出來,他身后化為鬼魂是一定要討還公道的。果戈理以魔幻手法真實寫出一個人內心可能有的悲憤。更為精彩的是,在淚水不斷滴落的時候,我們還能笑得出來。
小說如同一只飛鳥穩穩當當飛向又高又遠的天際,去完成她的史詩,而對于這只鳥的評論卻宛如鳥兒的影子,雖然也在移動卻從來沒有離開地面,而且離這只翱翔中的鳥兒越來越遠。1927年愛德華·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所談到的這個現象完全地適用于果戈理的小說。不幸的是,果戈理太在乎評論界的意見,竟然一次焚書、兩次焚稿甚至舍棄了自己的生命,在他四十三歲的時候。
距離我初讀果戈理半個世紀之后,我終于來到白夜籠罩下的圣彼得堡,走上了涅瓦大道,在瑪拉雅·卡紐施娜婭街,果戈理住了很久的公寓附近,同果戈理巨大的雕像見面。小說家雙手環抱胸前,低頭下望,神色嚴肅,目光深沉;他穿著一件巨大的披風,披風的長度直達鞋面。我伸手摸著這件披風的下擺,跟果戈理說,我會跟著您的小說飛翔,飛到又高又遠的地方。這時候,我似乎看到了他隱隱然的笑容。
我終于有機會來到莫斯科,在新圣女墓園,在果戈理的墓石上,在那個金色的十字架前獻上一束玫瑰。我跟小說家碎碎念,很快,您的小說會有最好的中文譯本。
果真,最新版本的《外套與彼得堡故事》問世了。譯者同編者都是俄羅斯文學學者,他們根據197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果戈理作品全集》翻譯出版了這本經典小說。經過再三揣摩,新譯本的結構有所改變,篇章順序依次為《涅瓦大道》、《鼻子》、《狂人日記》、《外套》、《畫像》。于是,角色同場景相呼應首尾相接,讀畢全書,似乎是跟著一個圓旋轉下來,我們會感覺到回到了原地,有如夢境。這樣的編排真正體現出果戈理語言的強大魅力,讓讀者在虛幻與真實間看到圣彼得堡,一個在沼澤上興建起來的、內涵極其豐富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讀者經由這樣的一個閱讀歷程,可以看到人生中時時不得不面對的荒謬困境,不但能夠沐浴人性的光輝,也能夠體察人性的柔弱與缺失。熱愛文學的讀者更能夠透過這樣一本書來接受文學理論的一次洗禮。畢竟,許多的事情是從圣彼得堡開始的,其源頭正好在果戈理的筆下潺潺流出。
二
“我們不習慣抗議,習慣哀痛、埋怨、遺忘”。這樣的一句話印在一本小說的封面上,當然有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小說的作者是新加坡的英培安,小說的主場是新加坡。
新加坡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那里的華人在怎樣地生活著,都是華文讀者關心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新加坡位于東南亞馬來半島的最南端,北部以柔佛海峽與馬來亞相隔,南部同印度尼西亞隔著馬六甲海峽遙遙相望。除了本島之外,新加坡還有六十三個離島,總面積只有七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國家卻聚居著五百五十萬人,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本地居民中,華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第二順位的馬來人只占百分之十三。
1819年,此地成為英國殖民地,在漫長的歲月里,新加坡是大英帝國在亞洲重要的航運與戰略基地,更是“日不落”帝國重要的經濟據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1942到1945年,新加坡被日軍占領了三年半,并被更名為昭南。戰后,英國再次控制新加坡。直到1965年,新加坡才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獨立建國。但是,在短短的歲月里,這個島國卻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即使在橫掃全球的經濟風暴中,失業率極低的新加坡仍然屹立不倒。現在,除了紐約、倫敦之外,新加坡是全世界第三個最為活躍的金融中心。
英國人、日本人、馬來人都曾經是主子的新加坡華人的精神狀態是怎樣的復雜,我們不難想象。在英文是主流語言的新加坡,多數來自福建、廣東、海南的華人在復雜的語境中艱難掙扎的內心糾結,我們能夠了解。因此,當英培安的小說中出現相當數量的廣東話,并且在書中附有《粵語華語對照表》的時候,我們體會到,華語對于生活在新加坡的華人來講絕非最重要的語言,粵語仍然是或曾經是母語,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不可徹底分離的部分。有了這樣的認知,我們讀這本優秀的小說,才能感同身受。
國家小、歷史短,絲毫不影響文化的多元,因為這個移民國家有著漫長、復雜的移民史,而每一位移民的艱辛跋涉便足以構成一部或數部長篇小說。
英培安的這本小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以第一代廣東移民梁炳洪老先生的回憶與夢境為主線,細致描述移居南洋的曲折歷程,并非一個“窮”字能夠概括一切。是的,廣東鄉下的貧困已經到了父親準備賣掉妹妹的地步,做哥哥的終于得到家人允許同朋友一道到省城尋找活路,繼而到香港,終于抵達新加坡。兩位少年人離開家鄉之后,并非沒有生存機會,而是仍然懷有夢想,希望著“遍地黃金”的南洋會帶給他們幸福的生活。當他們二人在一間咖啡茶鋪找到工作,安頓下來之后,兩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梁炳洪安于現狀,不想再冒險,也不想吃苦學藝,而終生留在了這間茶鋪。朋友德仔卻吃苦耐勞積極學藝,成為粵劇名伶。不僅如此,兩人共同喜愛的女子雖然嫁給了梁炳洪,他卻知道實際上,她愛的是德仔。于是,事業、愛情都充滿遺憾的梁炳洪被妒火焚身許多年,如此人生遭際足夠成篇。但是,小說的主場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歷史、文化成為雄渾的背景,為人物的際遇延拓出深度。華人人口眾多,但華語始終受到官方的限制同排擠。下一代要有前途需進英校而非華校,粵劇是無數廣東移民心底里的最愛,卻在日新月異的社會里迅速地沒落。一件藏在箱底多年的戲服成為鄉愁的具體表征,成為一個美麗的隱喻,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它牽連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情故事,愛恨交織;對故國的希冀、失望、惆悵,對現實社會的哀怨、猶疑、彷徨都同這件戲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整部小說閃耀出華彩。
日軍占領期間,無論怎樣地逆來順受,百姓依然遭到殘酷的荼毒。這段史實在書中有著清晰、沉痛的描述,是小說中特別撼動人心的部分。梁炳洪同妻子在這生死攸關、艱難度日的歲月里,反而能夠心心相印、能夠互相扶持。作者的敘事脈絡便得以深植于人性之光輝面。
小說的第二部分以梁炳洪的孫女如秀為主線,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新加坡的社會變遷。如秀念的是英校,在公司里做事使用的是英文,同女友們相聚聊天也是使用英文的時候居多。因此,如秀的中文程度不是很高,廣東話講得也不是很流利;有趣的是,這樣一位現代女子對粵劇卻情有獨鐘,工作之余樂于演唱。在個人感情方面,她的前男友雖然一表人才,卻用情不專,終于分手。如秀同第二任男友劭華卻很快進入婚姻,隱隱然有著同粵劇的某些關聯。劭華不但曾經同梁老先生“對歌”,而且認識如秀的大哥劍秋——粉雕玉琢、熱愛粵劇并且獻身藝術的劍秋。英培安為劭華埋下了長長的伏線,這根伏線的首尾都同粵劇相連,千回百轉終于回到了那件戲服上,成就了這本小說在結構上的特別優異之處,使得戲曲同小說相輝映,曲折、婉轉、引人入勝。
然而,英培安畢竟是卓越的小說家,他并沒有讓那件優雅的戲服占據舞臺,他也沒有讓纏綿悱惻的粵曲成為主旋律。那么善解人意、那么體貼、那么樂于傾聽的劭華竟然是冷漠的。而那位為了學戲荒廢了學業,終于翩翩登臺的梁劍秋卻并沒有真正得到良師指點,竟然只學得皮毛,終至遭人譏笑、輕慢,而幡然醒悟自己只不過是“半桶水”,尋根究底,年少時并非真正愛演戲,沒有下過苦功夫,而只是虛榮心作怪而已。
情何以堪?正是這四個字道出了真章,人性的復雜與多面同哀痛、埋怨、遺忘相應和,寫出了曲折、隱晦而不堪回首的人生。小說成功地描摹了八十余年動蕩不安的歲月,展開了梁家三代人曲折多舛的命運,讓我們看到了新加坡的社會政治風情,以及顫動在廣東移民心弦上的雖然微弱卻年復一年繞梁不去的優雅韻致。
三
當人們準備購買一個居所的時候,房屋中介們都會耳提面命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聽到這樣的提醒,人們便注意著學區的優劣、公共交通的便捷、公共設施的齊備、空氣水質以及自然環境的種種指數,當然還有安全的考慮。一切考慮周全之后,這才付諸行動。而且,感覺上自己做對了一件事情,對自己、對家人都有了一個很好的交代。
但是安居樂業不久就發現,山火蔓延騰起的濃煙竟然逼到了門前,本來價值百萬美元的房子竟然被土石流掩蓋,自家房子已然成了斷崖邊的懸樓;本來居于美麗的小島上,蔚藍色海波在遠處蕩漾,不知何時海水已經漫上街道,連通陸地的橋梁已然隱入水下,自家豪宅成了不可救藥的“泰坦尼克”。
怎么會是這樣?答案很簡單,人們對所謂家居位置的考慮通常是只見樹木未見森林。或者更糟糕,連樹葉的形狀都沒看清楚,更不用說整株大樹了。何以至此?信息爆炸的今天,怎么會有這樣的結果?信息爆炸是事實,但紛至杳來的信息不等于知識,信息更不等同于思想。有沒有想到過,世界上有一門學問叫作“地理思想”,這門學問古老而又年輕,這門學問在新世紀更加彰顯出它的重要性。跑到大學去念這門學科有點遠水不解近渴,快捷方式便是找一本真正有用的書來讀一讀。
《地理思想讀本》所提供的論文是現代大學地理系學生必讀文本,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則具有豐沛的知識、饒有趣味的啟發。這本書告訴我們,早在荷馬活著的時代,他用腳丈量的山川、土地的樣貌就出現在他的詩歌之中,因此人們將地理著作的出現歸功于這位偉大的行吟詩人。但世界上最早的地圖卻是公元前兩千七百年的時候,由閃族人繪制的。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希臘學者伊拉托尊尼斯來到了世界上,他是第一個使用“地理學”這個名詞的人。地球上的人類要生存,必定要將自己生活的環境做個合理而且有用的記錄,非如此,根本不知自己身處怎樣的險境。于是,地理思想史這樣一種記錄就在數千年的歲月里逐漸成形,幫助人類更好地化險為夷,更好地適應環境,更好地活下去。
綜觀這漫長的地理思想史,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一個有秩序的、有條理的、和諧的宇宙觀。如果我們熟悉西方藝術史,馬上可以得到一種印證,卓越的藝術家往往也是卓越的思想家,他們對于秩序與條理有著頑強的堅持,比方說十九世紀的法國畫家塞尚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對于秩序與內在力量的不懈追求幾乎是他離開印象派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人類有著極其撼動人心的智力激蕩時期,發生在古代希臘,公元前三、四世紀為其高峰。此時的希臘學者將巴比倫學者對于觀察同原則的關系做了徹底的修正。觀察所得不符合原則時,將觀察視為例外是巴比倫的概念。希臘學者卻在觀察不符原則時修改原則,科學之法于焉誕生,占星術走向了天文學。尤其是創立歸納法的亞里士多德總是寧可用經驗來修正概念。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幾乎人人都對地理學有著貢獻。地理研究有著兩個傳統:數學傳統與文學傳統。數學傳統由泰勒士發端、希帕庫斯創立了用經緯度確定位置的理論、托勒密在天文學與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與著述則集合發展了前人的觀念。文學傳統始于荷馬,第一位散文家赫卡泰將其發揚光大,然后斯特拉姆的充滿歷史感的地理學專著為現代地理思想奠定了基礎。
從公元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再一次的智力激蕩引領人類前進,達文西同哥白尼引領潮流,敢想敢說,沖破黑暗中世紀帶來的一切束縛。1809年,柏林洪堡大學創立,教師同學生在這里不受任何宗教與政治的束縛,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到了十九世紀末,達爾文的進化論概念使得這一番動蕩達到高峰。
與此同時,學術世界得以分門別類,而實驗科學的興起則是學科分類的重要促成因素。古希臘以降的學者如同百科全書,例如希羅多德在歷史、地理、人種學諸方面都有巨大貢獻。最終,全方位學者洪保德同李特爾在十九世紀中葉辭世,古代學術也在此時抵達高峰與終點。
戰爭是人類行為的一個極端,戰爭帶來的危害無以計數,但是戰爭帶來的深遠影響也是超乎想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副產品之一便是普通系統論的創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諸多元素有了整合的可能性,于是對事務的預測便必然要依靠幾率理論。更妙的是,為了破解敵方密碼,計算機應運而生,地理學倚重的計算有了大為快捷的可能性;而衛星的出現,則使得地理學產生了巨大的飛躍。
地理學一向有著整體高于局部的傳統思想。因此,一位優秀的地理學者必然地要對區位、距離、方向、擴散以及空間秩序提出問題,并且尋求解答。因之,微積分、線性代數、矩陣代數等基礎數學以及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習精進對于一位地理學者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現代科技的推動下,地理學對空間的研究、對地域的研究、對人與地球之關系的研究以及對地球本身的研究都發展迅速。地理學早已攜帶此一歐洲學科的優秀傳統而在全世界開花結果。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當中,地理工作者、地理學家一直在身體力行地負擔起一個教育的功能,啟發人們去研究,告訴人們如何去研究以及為什么要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方說地震、海嘯、植被保護、生物保護、地表暖化等等直接同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課題。以及人們尚未意識到其嚴重性的諸般課題。在這個系統當中,方法論讓位給哲學。
換句話說,古老而又年輕的地理思想在鼓舞人們將地球視為人類世界,不只是我們居住的家園,而且是我們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地理思想在引導我們“去驚嘆、去哀傷這一個人類的世界”,將對地理的概念上升到心靈與倫理,繼而真正敞開心胸拓寬視野,繼而采取正確的行動。
四
沒有想到,“新銳”作家陳列竟然是我的同齡人。說他新,因為多年來極為關注臺灣文學的發展,卻沒有見到過他的作品結集,說他銳氣十足,是因為臺灣印刻出版社在2013年一口氣為他出版了四本書,而且,其中《地上歲月》以及《躊躇之歌》獲得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細查這四本書,乃是陳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以來發表在報刊上的散文精選,最后這一本《躊躇之歌》則是歷時約十年,無數次反復刪修的大散文創作,甫一問世便受到讀者歡迎。
我是老派的讀者,喜歡從頭看起,于是我先看第一本《地上歲月》,作者陳列步步留神,為八十年代的臺灣留下了至為貼切的影像。
就拿《礦村行》這一篇來說,就非常的震撼人心。這篇文章是1985年寫的,那時候,臺灣經濟起飛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平靜的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礦村。作者首先寫到的是“在崎嶇的山嶺重重包圍的谷地里”小學生放學的情境,沒有喧嘩、沒有笑聲、孩子們沿著鐵路旁邊狹窄的人行道,排成一路縱隊,默默地走回家去。作者注意到,在學校的校門上有一對標語“走出校門,步步留神”,幾乎成為這些小學生的人生寫照,也是這所學校的師長對于這些孩子們最為貼心的叮嚀。因為,在他們的生活環境里充滿了不可知的危機、當頭罩下的厄運隨時隨地可能發生。
這是一個老舊、破敗的礦村,一條著名的河流的上游從村子里穿過,雖然是上游,已然在河床里堆積了垃圾。河岸邊有一座礦工宿舍,“破落的磚造房子并排相望,中間隔著潮濕的有點黏糊糊和著煤屑的甬道”,門窗歪斜、氣味雜陳。女人們無聲地舀水洗菜、淘米做飯。礦工們回來,就在這里休息,準備著迎戰下一個工作的日子。
礦坑的深度平均四百米,最深的可達九百米,長度可達三千米,地熱高達40℃,坑道狹窄,手工采掘,隨時隨地可能出現各種狀況。
柴油車載著礦工們回家來,陳列看到了他們,驚訝著他們白皙的皮膚、斯文的舉止、安靜的談吐以及他們身上完全沒有煤炭的味道。偶爾,他們坦然地交談幾句,贊美著孩子們用功上進。在返家之時,順便買一把青菜、兩條魚、一斤肉。他們不談自己,他們坦然面對一切,包括災變。明明知道災難不會遠去,仍然平靜地對待,并無怨言,更沒有憤怒。作者來到這個礦村,又搭車離開了這里,卻沒有能夠同任何一位當地的人交談過,然而,我們卻從字里行間看到了陳列自己的憂心忡忡,面對他人艱難而并不絕望的生涯,他說不出話來。文章之外,一幀黑白照片,簡陋的礦坑口、低矮的木架、空著的鐵皮煤炭車,礦井外明亮的天光,想必是仍然在礦井中工作著的礦工們最希望看到的。臺灣的經濟起飛正是站立在這些堅定有力的肩膀上,我們隨著陳列復雜的心緒從心底里對這些建設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出生于嘉義農村的陳列用《地上歲月》來描述他對土地的情感,以及臺灣農人對于生活的永不放棄的追求。在農村里,大自然是當然的主宰,能夠溫柔地滋育,也時時露出狂暴的猙獰。從受制于自然,到了解自然,到尋求解救之道,文明的演進在臺灣的農村是發展迅速的,科技的發展更帶來了希望與秩序。對于用筆寫字的陳列來說,在農村的成長經驗讓他對于人生的真諦有了更為切實的體會,“耕耘”這樣的兩個字對于這位作家而言有著無與倫比的切實美感。
在教科書里被稱作“山胞”的男女老少,在陳列的筆下,成為《同胞》。他細說從頭,無論是被“文明的演進”擠上山去的泰雅族,或是被擠到海邊去的阿美、雅美族,他們在古早時期都是平原上的居民。石牌、古亭、頭城這些地名是他們遺留下來的痕跡,但是現在的人們卻很少去回顧他們不得不離鄉背井的辛酸過往。“步步留神”的陳列卻從單獨出現在各個地方的男女老少靦腆、矜持、拘謹的言談與行動中感覺到他們在融入社會大潮時的某些不適應,以及他們自己的文化習俗在這個融入的過程中所遭受到的不可避免的流逝。陳列在用他的書寫提醒人們,首先就不應當將他們視為異族,不應當懷著獵奇的心理去探究他們,而應當切實地了解,我們本是同胞,有著共同的悲喜。對于整個混亂而癲狂的當今世界而言,陳列的敘述、理想與追求正是人類最迫切需要的救贖。
陳列是一位樂意親近大地的旅行者,他行走《在山谷之間》,將美麗的風景化作奇偉的文字,非常的傳神。透過他的文字,我們看到了畫面,流水、高山、植被都有了聲音、氣味、顏色、形狀,可以觸摸得到。“步步留神”的陳列卻在這美麗的景致中發現人的蹤跡,山地同胞的蹤跡,以及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外省人”的蹤跡,并無隔閡。更動人的是,身為本省人的陳列還寫出了《老兵紀念》的篇章,同情之外,有著更深的理解。文章末尾的那一幀照片黑白分明,道出了一種無法彌合的悲愴,與今天、與昨日都無法彌合。
全書讀畢,我返回第一篇《無怨》,那是寫鐵窗歲月的,陽光透過鐵窗被分割為十二塊,于是泛黃的書頁上出現了兩小塊柔和的光亮,陳列從來沒有想到“陽光移動的腳步竟會那樣令人怦然心動”,然而當他枯坐囚室時,卻為“幾小塊投射在房間內的光線而激動、而守候”。于是,我能夠感覺到文學人陳列“步步留神”的源頭,他在尋找人類互相理解、同悲喜、共命運的途徑。
五
夏志清教授不但撰寫了論文《端木蕻良的小說》,于1974年在麻州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宣讀,而且從這一年秋季就開始收集端木蕻良的早期作品,長篇稍微容易,可是要把分散在報章雜志上從來沒有結集成書的作品收集起來就非常的困難了,一定要依靠專業圖書館的幫助。哥大、哈佛、耶魯、芝加哥、普林斯頓、香港中大之外,最終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豐富館藏幫了大忙。端木先生自己對于他當年在香港、桂林等地所寫的作品不但沒有自留底稿,而且連刊載這些作品的雜志也都沒能夠保存。
由于這些資料的匯集,當端木蕻良的研究者孔海立在1995年初冬造訪夏先生的時候,才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機緣,編輯出版一本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選。這本題為《大時代》的書于1997年7月由臺北立緒出版社出版,此時,端木先生已經辭世,未能親眼看到這本他自己題了詞的書問世。這是一本非常扎實的書,讀者不但能夠讀到早已散失的八篇小說、戲劇與電影腳本、論文,更能了解端木自述家庭史、四十年代他的創作總表,以及這本書成書的來龍去脈。
讀這本厚重的選集,讀者一定會被小說《大時代》深深吸引,被丁寧這個人物深深吸引,而想去一探究竟。這個人物最早出現在端木的成名作《科爾沁旗草原》中。1933年,端木二十一歲,完成了這部長篇,1939年在烽火連天中才得以出版。1956年出版過一次,“被刪改得不像樣子”(夏志清語),1997年6月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新版。端木夫人在端木先生辭世周年這一天題贈給我,用了“存正”兩字。由此,關東的沃野便在我的書房散發出黑土地的芳香,隨著歲月的推移,日見濃郁。
遠古時代,由于黃河之兇猛的泛濫,由于水災之后更加兇猛的瘟疫,由于水災與瘟疫造成的大饑饉,關內的農戶扶老攜幼奔向關外。在北遷的途中,瘟疫如影隨形,死亡的陰影每時每刻脅迫著離鄉背井的人們,于是求——于是拜佛。人群中識風水的丁姓老人便受到了人們的信托,倚仗著人們的信托,倚仗著自家尋找風水寶地的能耐,在關內的大地主到了關東的沃野之上成為更加殷實的一方霸主。巧取豪奪、欺壓良善、與官府勾結鏟除對手并且吞沒對手之家財……,無所不用其極,終于奠定其富甲一方的地位。
盛極必衰是鐵律,二十世紀初葉的日俄戰爭使得丁氏家族受到重創,在逃難的路上,丁家的孩子丁大寧同大管家黃家的孩子大山同時出生。數年之后,大寧有了同父異母的弟弟丁寧。自此,三個男性角色的互動于焉展開。
丁氏家族如此占地為王、作威作福,家中人際關系又是這樣的復雜,自然是寫長篇小說極好的素材,而且,年輕的端木蕻良不但受到俄羅斯文學的深刻影響,也受到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刻影響。如此這般,豈不是會寫出一部關外的《紅樓夢》來?非也,端木走了一條別人未曾走過的路。家族的歷史、人際錯綜復雜的關系沒有詳加敘說,只是成為一道相當模糊、沉滯、濃厚的背景。在這樣的背景里,軍閥時代的混亂、民不聊生的現實,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禍害,日本人的步步進逼,交織在一起,成為那個時代最為具體的舞臺。在青島念書,回到家鄉省親的丁寧同未曾離開故土、在血與火的淬煉中長大成人的大山必定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之路,這臺戲便這樣生猛而緊鑼密鼓地上演了;主導著情節發展的是熾烈的情感。端木用了急促、跳躍的節奏來主導劇情,換句話說,二十一歲的端木無師自通地書寫了一部現代小說。想來,這才是在四十年后令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驚艷的最主要的原因。二十世紀末,晚年的端木先生這樣回顧他的創作歷程,他每讀一本小說都會不時地合上書本,問自己,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這個自問自答的過程就是他個人的“小說教室”,古今中外的小說藝術就這樣在他的閱讀中融會貫通,然后,他走出了自己的路。
端木先生出生于遼寧一個小鎮上,此地在清朝以前曾經是個被封為“遼海衛”的地方,其實,那地方并沒有海,只有一馬平川的大草原,這就是科爾沁旗草原。端木的祖上是一位相當“有頭腦”的地主,他所使用的策略是一種兼并的方法、一種蠶食的方法,將周圍小地主的土地逐漸地收攏到自己的手里,而成為大地主。端木的母親出身貧寒,卻因為美貌而被“搶奪”而來。因之,少年端木就對地主家庭的種種有了切身的體會。然則,端木絕非丁寧,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絕非豐沛的親身經歷可以成就的,而是對社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的產物。
端木熟悉農民的生活、熟悉他們的語言,因此他筆下的農民形象鮮活,絕非千人一面。在《科爾沁旗草原》這部書里,當天地干旱、谷物歉收、佃戶繳不出租糧的時候,他們相聚商議對策,這些充滿時代氣息、鄉土氣息的對談深刻地刻畫出他們各自不同的處境、性格、精神狀態,形成了端木小說極為精彩的特質。
面對佃戶們的困頓,大山唆使人們同丁家對抗,集體退佃。年輕的丁寧正遭父喪,家里的二管事又遭綁票的危難關頭,卻能夠四兩撥千斤,以“免租糧”化解了危機。如此書寫,在三十年代自然不是問題,到了五十年代,卻無法避免“被刪改得不像樣子”的命運,而才氣橫溢的小說家端木蕻良也就有了幾十年沒有創作自由的日子,直到晚年才得以集聚精神,奮力一搏,投身長篇小說《曹雪芹》的創作。
小說結束在關東的沃野換了主人的狂飆之中,讓日本皇軍聞風喪膽的“馬賊”們組成的義勇軍里閃耀著大山平靜的面容、矗立著大山威風凜凜的身影。
另外一部史詩揭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