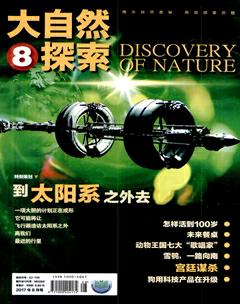怎樣活到100歲
劉安立
那些壽星的DNA,可能隱藏著長生不老的秘密。
“現在,我們當中只留下我倆了。”耶米瑪頗有些悵然地說。他們曾經是興旺的大家族,但現在她那一輩就只剩她和94歲的弟弟了。她的兩個姐姐分別在105歲和107歲去世。2017年1月,在孫輩和曾孫輩簇擁下,耶米瑪在加拿大中部馬尼托巴省布蘭登市的家中度過了106歲生日。守寡50年來,耶米瑪一直獨自生活,自己做飯,自己洗衣服做清潔。她服老的唯一一個表現,就是坐輪椅。
耶米瑪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的許多大事件。她至今能清晰地回憶起軍人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回家時的慶祝場面,能記得家人們在狂風呼嘯的草原上舉辦盛大野炊,能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汽油配額(那時她是一位有著5個子女的年輕媽媽),能記得橫跨歐洲、非洲北部和美國的旅行,還能記得自己退休后在澳大利亞大堡礁潛水的經歷。這位前學校老師說:“我的一生真是充滿冒險。”她承認自己是個夜貓子,上午常常睡過頭。記者問她長壽的秘訣,她的回答是:“樂觀開朗。”
耶米瑪是新英格蘭百歲壽星研究項目的參與者之一。這是由美國波士頓醫療中心主持的一項長期研究項目,其研究課題是:為什么像耶米瑪這樣的壽星能如此長壽而又健康?該項目團隊迄今為止的發現是,健康習慣和正面生活態度只能讓人相對健康,百歲壽星其實是“基因彩票”的贏家。就像耶米瑪那樣,百歲壽星大多有家族長壽史。他們的心智非常健康,他們當中90%的人都獨立生活到90歲以上。活過100歲意味著:盡管種種病痛讓他們的同輩還不到90歲就紛紛離世,他們自己卻能在很大程度上避開這些病痛,原因是他們有一系列保護性的基因。就算他們患上種種老年病,他們的身體保護機制也優于常人。換句話說,他們越老反而越健康。
現在,科學家通過篩選數百萬個DNA標記物,辨識百歲壽星身體每個細胞攜帶的長壽基因組合。一些科學家已經發現了281個看來執行著保護功能(即延緩衰老進程,讓百歲壽星不受致命疾病影響)的基因標記物。另一些科學家則通過對百歲壽星的基因組測序,發現他們的主要致命疾病基因數量很少。也就是說,百歲壽星之所以能長命百歲,是因為他們不得病。
百歲壽星為什么能不得致命疾病?科學家相信,或許有某種生物鐘在他們身上變慢,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變快(即加速衰老進程、消磨身體的保護機制)。那些生物鐘變快的人更容易患致命疾病,去世更早。對百歲壽星遺傳特征的研究,以及對可能影響衰老進程的其他生物學機制的研究,對了解這類生物鐘背后的機制提供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線索。如果能破譯這些生物鐘的工作原理,或許就能讓科學家調整人體內部的這些生物鐘,從而真正延緩衰老進程。
真實年齡
時機看來是上述生物鐘奧秘的重要一環。生物學年齡并非總是與一個人出生證上的年齡匹配。畢竟,無論我們見到一位還不滿70歲的老人備受病痛折磨,還是見到一位快要75歲的老者精神矍鑠地全國奔忙,我們都不會覺得有什么好奇怪。只不過一些人就是比其他人老得快,科學家則剛開始明白這究竟是為什么。對一項具有標志意義的縱向研究所獲數據進行的分析結果讓人大開眼界。這項被叫做“達尼丁”(達尼丁是一座新西蘭城市)的研究,追蹤了新西蘭南部一家醫院里超過1000名20世紀70年代初的出生者。
許多研究聚焦的是老年人的衰老進程,但與年齡相關疾病的種子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埋下,這就是“達尼丁”項目團隊相信更重要的是研究年輕人如何衰老的理由。他們希望解釋為什么時間催人老,為什么癌癥、心臟病、糖尿病和阿爾茲海默癥等慢性疾病會與衰老進程相關。美國、英國、以色列和新西蘭的科學家運用但尼丁項目數據跟蹤954位志愿者的18個生物學指標,其中包括肝腎功能、血糖、膽固醇水平、平衡能力、認知能力、心血管健康和牙齦萎縮等。
根據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不出所料,大多數人的生物學年齡都聚集在40歲出頭,與他們的實際年齡相差幾歲。但其中的差異很大:實際年齡40歲的人中,少數人的生物學年齡只有30歲左右,而很多人的生物學年齡已達50幾歲,其中有人的生物學年齡竟然已達61歲。就算還未到中年,有些人也未老先衰,出現爬臺階不容易、解決不熟悉的心智問題有障礙、平衡能力差、肝臟功能開始失調,總體健康水平不佳等問題。
總結所有數據,科學家被人體所有系統內發生的協同改變驚呆了。很明顯,有一些基本的衰老分子機制導致不同的疾病,這些疾病最終殺死我們。
細胞計數器
50多年前,一位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內部生物鐘可能調控衰老的首批證據。他發現,讓人體逐漸枯萎、最終死亡的原因,并不僅僅是人體外部的種種磨難。20世紀50年代后期,年輕微生物學家海弗利克在美國費城的維斯塔研究院研究可能致癌的病毒。在那里,他研究的對象是取自人體胎兒組織的細胞培養物。有一天,其中一只燒瓶里的細胞分裂看來減緩了。經過大約40次分裂后,這些細胞停止分裂。
當時,科學家相信所有細胞都是不死的,只需把細胞泡在合適的營養液里,它們就會一直分裂下去。海弗利克當時認為自己犯了一個技術性差錯,或者是細胞受到了污染。可是,他接著又在不同胎兒組織的其他培養物中觀察到細胞停止分裂。他回顧自己的實驗記錄,尋找出現這一異常的線索,結果發現在他制作的許多培養物中,總是最老的停止了分裂。
雖然癌細胞是不死的——它們的標志就是失控性繁殖,但海弗利克發現正常細胞的壽命有限,這就是所謂的“海弗利克極限”。后來的研究證明,就算把細胞冷凍幾個月,解凍后它們也會從冷凍前的狀態開始分裂,分裂40~60次后就不再分裂。海弗利克后來回憶說:“當我發現正常細胞有記憶時,我簡直驚呆了。(在此之前)沒人想到過正常細胞有記憶。一定會有某種細胞外的計數機制在限定細胞的分裂次數。但這是一種什么機制呢?”
1975年,海弗利克和研究生懷特證明了這個計數裝置位于細胞核內,但他們缺乏技術工具來破解其中的精確機制。海弗利克的發現違背當時的科學信條。他說:“我第一個證明細胞內存在衰老根源。”盡管當時生物學界對此不予認同,但海弗利克和懷特的發現依然激發了對衰老進行研究的大潮。又過了10年,海弗利克所說的“計數器”才被找到。
DNA碎片
盡管人們對她的突破性研究給予大量美譽,伊麗莎白卻依然保持著純真的熱誠、敏捷的智慧和作為澳大利亞原住民的那種勇氣。2016年初,這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化學家離開了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實驗室,前往由小兒麻痹癥疫苗先驅索爾克創建的科學孵化器——索爾克研究所。該研究所位于美國加州拉荷亞海岸,是一系列現代混凝土和玻璃建筑。記者和伊麗莎白一起坐在她的大辦公室里,那兒有面朝太平洋的大落地窗。
伊麗莎白來自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她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20世紀70年代,她來到美國耶魯大學,測定單細胞生物四膜蟲(她稱之為“池塘泡沫”)的染色體末端序列。這些DNA片段被稱為端粒,它們覆蓋染色體的末端。長期以來,科學家推測它們起著穩定染色體結構、阻止染色體末端磨損的作用,正如鞋帶末端的塑料鞘可以阻止末端散開一樣。但端粒究竟是怎樣工作的呢?隨著細胞每一次分裂,端粒都會變短,但科學家對端粒的確切功能一直不明了。伊麗莎白回憶說:“我們略微知道有某種細胞生物鐘,因為每一次DNA復制,染色體末端都不會復制。”
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端粒與細胞衰老之間的強烈聯系才被建立起來。這一突破有一點點源自科學的機緣巧合。伊麗莎白帶過的前研究生卡羅爾當時與一位生物學家談戀愛,后者與在加拿大渥太華的麥克馬斯特大學研究衰老的生物化學家卡爾文共享實驗室空間。實驗室里的隨意交談,最終演變成卡羅爾和卡爾文之間的全方位合作——或者說,是細胞衰老和端粒專業知識的融匯。
其結果是分別發布于1990和1992年的兩篇重要論文,它們提出了讓人信服的理由:端粒可能是海弗利克極限背后的細胞定時器。隨著每一次細胞分裂,端粒都會縮短,直到只剩下很小的一節,它促發細胞功能失調,停止分裂,最終死亡。伊麗莎白說,這項研究提供了一些好線索,表明“我們的研究正朝著正確方向發展,但又經過了好些年,經過了許多科學家的觀察,真相的細節才被拼接在一起”。
受阻的端粒
端粒縮短現在被認為是細胞衰老的一個生物標記。更多證據表明,這些小小的DNA碎片可能是與年齡有關的衰退背后的元兇之一。后續研究已經表明,端粒縮短和許多與年齡相關的疾病(包括心臟病、糖尿病、老年癡呆、中風和阻塞性肺氣腫)有關。伊麗莎白說,這些疾病是對老年人的主要殺手,“我們已開始不再認為端粒與這些疾病之間只是存在相關性,而是看到了真正的因果關系”。
21世紀初一項對身患慢性疾病、卻又要照顧孩子的產婦的研究發現,就算是面臨壓力也會磨損端粒。伊麗莎白和加州大學圣弗朗西斯科分校心理學家艾麗莎的研究發現,大多數面臨嚴重壓力的女性的端粒都較短,導致她們提前衰老了10年。這證明外部壓力會破壞細胞的分子機制。
曾經有一些研究檢驗了屬于美國北加州一個衛生維護組織的超過10萬人的唾液樣本,得出的結論公布于2012年的一次科學會議上。這些研究透露的主要信息是:端粒受阻的人死得更年輕。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雖然女性一般比男性長壽,但剛成年時兩性的端粒幾乎等長。雖然每個人的端粒都會隨著個人的衰老而變短,但50歲之后男性的端粒縮短會加速。這一兩性差異會持續到大約75歲,此時那些端粒受阻的人大多會死于疾病。
這些結果在分子層面證明了科學家觀察到的百歲壽星情況:長壽者擁有一種生物學優勢,它讓長壽者躲過或更好地忍受伊麗莎白所說的、殺死我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槍林彈雨”。伊麗莎白說:“大多數人都會死于75歲左右,所有活得更久的人都是生物學上被選定的幸運兒。我們已知端粒縮短會導致細胞衰老,因此有理由說端粒縮短也在導致人體患病。”
然而,端粒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表觀遺傳鐘
“這里有個硬結,它會讓你不舒服的。”何塞一邊給記者按摩手指,一邊通過翻譯用西班牙語對記者說道。盡管已經高齡,何塞卻顯露出淘氣的露齒笑。身高不到1.6米的他,穩穩地坐在他與孫女一起住的自家磚屋里。他們家位于哥斯達黎加的伊爾多利托村,一些土路連接著這個小小的雨林村。
2015年11月的一天,這里依然悶熱。這是哥斯達黎加西北角的尼科亞半島上的雨季結束期,數月來的傾盆暴雨帶來了叢林的蒼郁。何塞是當地出名的按摩師,他通過解剖雞自學了解剖學——就在他與記者談話時,3只雞懶洋洋地走在他家院子里。他不僅能通過按摩舒緩被按摩者緊張的肌肉,而且能復位脫位的關節。當地一些來自國外的沖浪者和退休者背痛時,也會找到他。
何塞一生從事農業,到80歲才退休。當時他被診斷患上了白血病,但這對他幾乎沒有影響。再過幾天他就要過98歲生日了。他對記者說,他至今記得80年前自己害相思病的情況:那時沒有道路,他只能沿著海岸步行到另一個村子去見心上人。他把自己的長壽歸因為辛勤工作、健康的食物和家庭——他的妻子不到兩年前去世,他的兒女、孫輩和曾孫輩全都住在他家附近。
在尼科亞半島上,何塞的長壽并非罕見。這個半島有100多千米的原始海岸線,有牧場、農場和長滿樹木的山坡,這里不乏活到90歲、100歲甚至110歲的人。雖然生活貧困,當地人卻比其他地方的富人長壽得多。尼科亞半島是全球5個“藍區”(長壽熱點地區)之一,其他4個分別是日本沖繩縣、美國加州羅馬琳達、意大利撒丁島和希臘伊卡里亞島。
一位哥斯達黎加人口統計學家2005年發現,那些活上了60歲的哥斯達黎加人最終在全球最長壽者中占比最多。2012年的后續研究發現,尼科亞的長壽居民更長壽,比哥斯達黎加其他壽星多活3年。在201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成果中,美國斯坦福大學流行病學家瑞克夫及其同事希望探討前述現象的原因。他們提取超過60歲的尼科亞居民的DNA樣本,測量端粒長度。測量結果表明,他們的端粒長度的確長于同齡的其他哥斯達黎加人,前者平均多出大約81個堿基對,相當于戒煙或經常性體育鍛煉帶來的好處。
尼科亞半島居民為什么如此長壽?看來關鍵在于哥斯達黎加流行的一個口號:純凈生活。哥斯達黎加是一個有著數百年歷史的民主國家,有全民醫保,沒有固定的軍隊,在中美洲有最高的識字率,基本沒有困擾鄰國如巴拿馬、尼加拉瓜和危地馬拉的腐敗、毒品、恐怖主義和內戰問題。科學家相信,尼科亞人閑適的生活節奏、主要吃素食、和親友一起生活、經常鍛煉和有明確的生活目標,看來是他們的長壽秘訣。
雖然外部因素——壓力、貧困、環境毒素等可能加速衰老,但從某種程度來說衰老可逆看來也是真的。我們的生活經歷會對我們怎樣衰老施加深遠影響,甚至在無需改變DNA序列的情況下改變基因運作的方式。這類基因改變被稱為表觀遺傳改變。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生物統計學家霍瓦斯領導的一個科學團隊發現,一種表觀遺傳生物鐘或許有助于破譯表觀遺傳改變的發生機理,從而有助于解釋尼科亞人的長壽。霍瓦斯說:“對那些衰老比較慢的人來說,他們的表觀遺傳鐘不知為何也走得慢。有一種內在過程在驅動衰老,表觀遺傳鐘在其中很可能起了作用。”
衰老機制
出生于德國的霍瓦斯已經49歲,但依然帶著孩子氣。表觀遺傳鐘的發現是他一生夢想的結晶。這個夢想要追溯到他的高中時期,當時他就決心要一生致力于延長人的壽命。但直到2006年,隨著一大批數據的出現,他才能開始梳理數百萬個數據點,以便搜出與年齡相關的生物標記。
霍瓦斯團隊聚焦于一個天然發生的過程,它是人體內部管理系統的一部分,被稱為甲基化。我們的基因組會被環境因素強烈影響,而甲基化對基因組造成化學改變。從西班牙、德國、意大利、美國、英國及澳大利亞研究者那里,霍瓦斯獲得了超過50個數據庫。這些數據庫包含上萬名志愿者的基因檔案,這些檔案來自于對健康組織甲基化進行的研究。
在3年時間里,霍瓦斯及其團隊分析了來自于這些數據庫的近8000個組織樣本,其中包括血液、唾液以及來自于大腦、直腸等器官的細胞。他們從51類細胞和組織中辨識了353個DNA標記,檢驗衰老怎樣影響一個人一生中的甲基化水平。接著,他們運用數據設計了一種算法(實際上是一種表觀遺傳鐘),它能準確確定不同器官、組織和細胞類型的年齡。
當他們比較身體某個組織的生物學年齡和實際年齡時,這種表觀遺傳鐘能準確預測生物學年齡。提取自胚胎的干細胞被這個表觀遺傳鐘認為是非常年輕的,而來自百歲壽星的神經細胞被估計的年齡是大約100歲。就算細胞很年輕,例如只存在了幾天或幾周的白細胞,也攜帶著50歲捐血人的明顯的基因印記。霍瓦斯說,那353個DNA標記提供的加權平均數,能非常準確地反映出身體組織的準確年齡。
從那時起,霍瓦斯把表觀遺傳鐘作為一種工具來開始了解衰老機制。后續對意大利百歲壽星的研究顯示,根據表觀遺傳鐘的測量,這些百歲壽星后代的生物學年齡,比與他們實際年齡相同的非百歲壽星后代的生物學年齡小5歲之多。但霍瓦斯最重要的發現可能始于2013年。當時,致力于研究百歲壽星和超百歲壽星(年齡超過110歲)的洛杉磯老年醫學研究團隊,把3位百歲壽星和3位超百歲壽星的組織樣本提供給了霍瓦斯,其中一位超百歲女壽星不久前去世,年齡是112歲。
霍瓦斯對這些樣本的研究取得了驚人的發現。這些發現有可能最終能延長我們的壽命。霍瓦斯團隊檢驗了來自于這位112歲老婦的30個解剖部位的表觀遺傳年齡,發現小腦是其中最年輕的部位,它根本不像其他部位衰老那么快。小腦是充滿神經元的大腦區域,它位于腦半球下面,在運動控制和認知功能(例如注意力和語言)方面起作用。看來,小腦在80歲這個基準線上停止衰老,這樣一來,它在以后幾十年里都不再受時間影響。但小腦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2016年初,霍瓦斯及其團隊又更進一步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通過檢測,發現了小腦中與衰老加速有關的兩個基因的小變異。霍瓦斯指出,這一發現的令人興奮之處在于,這些變異發生在一條神經通道附近,而之前的研究發現這條通道有助于調節蟲和蠅的壽命。霍瓦斯團隊還發現,讓來自于這一大腦通道的化學信號停止,就能延長實驗鼠的壽命。霍瓦斯說,雖然這一發現還不算是確鑿證據,“但如果我們能了解為什么小腦衰老慢,我們就可能找到讓其他部位衰老減緩的辦法,甚至找到逆轉衰老的方法”。
端粒與衰老
諾貝爾獎得主伊麗莎白談這兩者之間關系
端粒是位于每個染色體末端的小小DNA片段。諾貝爾獎獲得者伊麗莎白在自己的整個學術生涯中一直在研究端粒的功能。在這里,她談及端粒在衰老中的作用。
問:端粒就是衰老背后的生物鐘嗎?
答:近似地說,衰老有點像時鐘,因為衰老是一個過程。但在“衰老”這個詞的真正意思方面,我們應該再靈活一點。人類衰老是不是指患上與衰老相關疾病的風險更大了?要是這樣,百歲壽星根本就沒有衰老。但很明顯的是,他們老了:他們的皮膚起皺紋,他們變得干枯、瘦小了;他們的健康表現很好,但他們并不是年輕人。衰老體現在多個方面,但我們經常會把衰老簡單化。在不同階段,大量不同類型的事物在起作用。就算我們避免了所有嚴重疾病,衰老進程卻依然存在,只是這樣的衰老與一般人的衰老有所區別而已。端粒縮短看來是那些殺死我們的疾病背后的風險源頭。
問:此話怎講?
答:包括基因特征在內的種種跡象告訴我們,端粒與衰老之間、端粒與致命疾病(心臟病、糖尿病、癌癥甚至阿爾茲海默癥)之間存在因果聯系。我們知道端粒縮短驅動細胞衰老。觀察皮膚起皺和沒起皺的人,你會發現后者的端粒更長。如果你的端粒只剩最后1/3長度,那么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會上升40%,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悲觀情緒也與端粒縮短有關。考慮到這些,我們就有理由相信端粒真的在推動人類疾病。
問:端粒越短,是否意味著人越可能得病,老得越快?
答:如果你遺傳來的是很短的端粒,那么你就患上了現在被稱為“端粒綜合征”的可怕疾病。這種病很罕見,但患上此病的兒童很少能活到成年。因為地球上的人口總量很大,所以全球罹患此病的人依然有幾百個,各個國家都有患者。此病患兒常常因為一種皮膚病看醫生,但真正問題不在于此。這些患兒的所有內臟都有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經常都與衰老有關。其中大約10%的患兒會死于某種罕見的癌癥,大量患兒會死于各種感染,他們的內臟功能失調,他們都病得很厲害。調查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因為他們的端粒遺傳自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你會發現他們的祖父母可能攜帶肺纖維化基因。所以,這些兒童患上端粒綜合征的原因,正是其父母、祖父母的一個端粒基因中同樣的堿基對變異。但這方面表現不同。這些患兒祖父母的端粒比他們同輩人的短,父母的端粒比同輩人的更短,孩子的端粒則短得可怕。如果一個人天生端粒較短,但他不吸煙,也不生活在壓力環境中,也就是沒有外因進一步縮短他的端粒,那么他還可能不會出大問題。不然的話,就可能會要了他的命。雖然端粒并不是衰老和死亡故事的全部,但它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