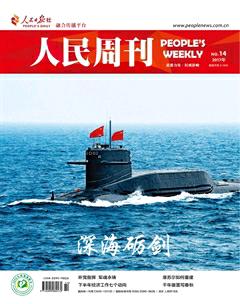好好聊聊王者榮耀,不必著急扣帽子
公子無忌
海外網俠客島2017年7月11日刊文
2億注冊用戶、日活5000萬、單季度貢獻60億收入,光憑這些數據,已經足夠使其成為現象級的談資。當然,圍繞這款游戲,現在的討論幾乎都在“外溢”部分:它如何毒害了未成年人、如何讓家長老師痛心疾首、有多少極端案例(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矛盾激化、偷家長的錢給游戲充值等)。作為危機公關的一部分,騰訊的“防沉迷”系統也應聲推出。
一
我也曾是“玩物喪志”的少年之一。并且我心里也明鏡兒似地明白,自己屬于自制力比較差的那一種。時至今日,我的母親大人依然會偶爾在我耳邊念叨:“若是你當年不玩游戲、不早戀、不沒事兒下課去踢球、不跟那幫狐朋狗友野混、不讀那些亂七八糟的科幻玄幻,沒準兒你的高考也不會那么爛……”
人生的確沒法兒重新來過,但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沒有一段人生經歷乃是虛度。無論何種經歷,最終都會以不同方式成為養分。比如,在我母上的訓斥中,出現了影響我成長的形形色色因素。未來也許有今天的年輕母親,會以另外的方式訓斥孩子:“如果你當年不玩王者、不看亂七八糟的網文、不看那些鬼畜視頻、不跟二次元新番、不看美英日韓劇……”
用臺灣詞作家鐘永豐的話說,這大概叫“升學主義”——往遠了說,這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歷史留存;往近了說,這是中國社會競爭激烈的一個突出表征。
想想也是,在喧囂的輿論場中,中產階級的焦慮,已經延展到了“拼在起跑線”上,不僅有學區房,還有各種補習班、花樣繁多的幼兒園、甚至連取個英文名都要有鄙視鏈——為了下一代出人頭地,父母已經拼成這個樣子了,作為孩子,你怎么居然還不好好學習,居然在沒事兒打游戲?
對網絡游戲的口誅筆伐,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二十多年過去了,對于“游戲”的“原罪”式討伐,似乎從未超出此前的范式。據不完全統計,在這種批判中,“玩物喪志”“不務正業”“毒害未成年人”等話語的出現頻次較高。
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文藝批評中心主任孫佳山列舉:從1905年電影誕生開始,一百多年了,隨著技術和媒介的迭代,幾乎每一個時期的新媒介、新藝術形式,都曾經被冠以原罪式的討伐——電影,長時間被視作魅惑人靈魂;電視大規模進入家庭時,也曾被認定是“可以傳播色情、暴力、毒害青少年”的媒介。1980年代初,有著作提出電視的出現導致“童年的消逝”,也暢銷至今。
從這個角度看,如前所述,網絡游戲被扣上這樣的帽子,并不新鮮和奇怪。用他的話說,“這不過是所有依托于新媒體的文藝門類在各自時代都要遭受的歷史洗禮”。“歷史的洗禮”,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們已經見過太多次。但將其視為“依托于新媒體的文藝門類”,倒是一個新鮮的、值得正視的看法。
二
人類為什么會喜歡游戲?
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行為方式之一,這大概是如同康德說審美一樣,屬于“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范疇。早在電子游戲出現前很多年,席勒就在《審美教育書簡》中說:“只有在游戲時,人才是完整的。”另一位哲學大家伽達默爾則論述道:“游戲的真正本質就在于參與者能夠從現實生活中永遠在追逐目的的緊張狀態中解放出來。”
就連奧林匹克,在Olympic后面,都是一個“Games”。足球是游戲,麻將是游戲,象棋圍棋也是游戲。寫作又何嘗不是?可以說,所有的藝術門類,都是廣義上的游戲——從人類第一次在墻上畫出線條,到第一次發現音律的協調。
中學時我喜歡讀一些亂七八糟的書,其中很多成了現在的流行IP。比如有一個奇幻的作家,他寫的《悟空傳》已經上映了。另一名奇幻作家,后來成了作家榜的首富(這位作家大學學的是化學,寫作大概也是不務正業吧)。彼時他們倆在小說中經常會寫到游戲,有時候是《帝國時代》,有時候是《大航海》,又有時是《最終幻想》。
事情皆有兩面。學會自制、學會分清主次、學會合理分配時間和精力,大概也是教育中的必修課。甚至,在游戲中學會配合、學會奉獻、明白友情的意義、明白堅持不投降直到勝利,也會是令家長和老師感到意外的“玩物”滋養。
三
騰訊有問題嗎?
當然有。防沉迷很難嗎?并不,完全用不著刷臉之類的黑科技。我記得以前玩一款類似的PC端對戰類網游,連續玩幾個小時后之后,會被強制下線,甚至戰績清零或倒扣。從技術上說,做到防沉迷并不困難,就看企業有沒有這個決心。
另一種指責則來自于其對歷史的扭曲:荊軻是女性啊,李白項羽劉邦都是動漫形象甚至西方游戲形象啊……需要一款游戲去教育孩子歷史,這本身可能就過于苛責。游戲中“歪曲”歷史的現象,抗日神劇、歷史神劇中一樣有;對于游戲玩家的崇拜打賞,直播亂象中也有足夠體現。試圖防止孩子被形形色色的東西“污染”,就像祈禱花朵長在真空中。
監管需要跟上嗎?孫佳山給我舉了個例子:現在的網游監管,網絡游戲的內容檢查權和文化經營審批權在文化部,版權在廣電總局,技術開發標準在工信部,電子競技則在體育總局。就連網游面臨的法律問題,也被分解在《網絡安全法》《知識產權法》《廣告法》以及眾多規章、條例之中,還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穩定的上位法。
而我對于騰訊的期待,或者說苛責式的批評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在于作品還不夠偉大。或者說,作品背后的價值觀還不夠偉大。技術上說,作為一款手游,“王者榮耀”已經很好,不展開細節。但一定程度上說,對于歷史的“扭曲”,大概也說明了內在價值的空洞。“王者榮耀”是在英雄聯盟基礎上的改變優化,內核的英雄、競技規則、道具都并非原創,指責其“暴力抄襲”的評論并不鮮見。甚至連人物用了歷史人物的姓名,非要畫成西式的樣子。如同每一款野蠻成長又凋零的游戲一樣,內在精神的缺乏,可能會是其生命期能否持久的關鍵。換句話說,這款游戲很難令人激動——那種如席勒、如伽達默爾說的,讓人從現實中解放出來的激動感,在這款游戲中應該很難獲得。
什么樣的激動感呢?2016年,《魔獸》游戲改編的電影在中國上映了。觀影的影迷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穿著整齊的T恤,喊出“為了部落”的口號。看電影,大抵能讓他們想起那個奇幻的世界,里面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職業,以及與隊友并肩作戰的每個夜晚;在《守望先鋒》里,有一個不會動的人物,中國人,穿著宇航服,上面有兩個字“宏宇”。暴雪公司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一名叫吳宏宇的年輕中國玩家,沒有等到這款游戲,就因為見義勇為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超越國界,不分人種,許多玩家來到名為漓江塔的這個地點,向這個年輕人致敬,留下“這個世界需要更多英雄”的寄語。
從這個角度看,“王者榮耀”只能算一款商業上極其成功的游戲,而非偉大的游戲。我甚至開玩笑說,如果我有孩子,如果看到他在打王者,會覺得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的好游戲值得去玩,我會教他,帶他進入那些奇異的世界,看不同的風景,領略歷史之美、人物之美、想象之美。而這些,恐怕都不是現在游戲行業追求的現金流、高黏性,甚至是對“人民幣玩家”的推崇,以及對“游戲模式越簡單越好”“有錢就可以變厲害”這樣的行業通行理念、慣用做法可以實現的。畢竟現在,網絡游戲的影響力已經遠超我們的想象。
孫佳山列了一串數據:2008年,我國的網游產業就已經是全球規模第一;2016年我國自主研發的網絡游戲的海外實際收入更是多達72.3億美元——單是出口這一塊,我國的網絡游戲行業就已經達到了我國電影的國內票房規模。同樣,在我國現有的近8億網民中,有近80%年齡未超過40歲,有近90%未受過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農村網民開始接近1/3。
換句話說,提供給如此巨量的受眾什么樣的網絡游戲,就是提供給他們什么樣的文化產品;他們的審美體驗、趣味的養成,網絡游戲提供的,可能遠遠超過學校教育的范疇。
我真誠地期待著,也許有一天,中國的游戲人做的產品,不是因為最能賺錢而成為新聞頭條,而是因為故事的精彩、體驗的豐富,成為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一如現在美劇、日漫、美歐日的游戲做到的文化輸出那樣。而在做到這一點之前,可能首先需要去除的就是將游戲視為洪水猛獸的陳舊觀點。這大概也需要典范和偶像的作用——就像在丁俊暉之前,無數的家長都把孩子進入臺球廳視為不務正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