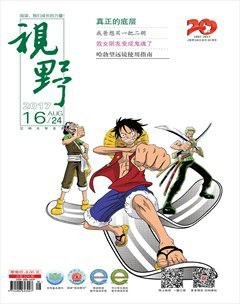我的木匠生活美學
西岡常一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們通常管我們這樣的人叫作“法隆寺木匠”或“斑鳩寺工”。我家從祖父那一輩開始就是法隆寺的棟梁,一直到我這輩都是這么延續(xù)下來的。我從一生下來,周圍看到的人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岡常吉,他的弟弟■內(nèi)菊■,我的父親西岡■光,我,還有我的弟弟西岡■二郎,都是宮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區(qū)還居住著眾多各行各業(yè)的手藝人,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是看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長大的。
身為木匠,我有幸參與了法隆寺的解體大修復,法輪寺三重塔的重建,藥師寺的西塔、中門、回廊以及整體伽藍的重建,跟眾多手藝人一起經(jīng)歷了這些難得的修建過程。
現(xiàn)在社會發(fā)展了,電腦普及了,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便利的時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機械來解決,就連一毫米的幾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間完成,技術(shù)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 這樣的機械也來到了我們木匠的世界中,它讓我們的工作變得方便了很多。
但是,這些機械的到來卻讓很多手藝人消失了。機器和電腦取代了手藝人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技術(shù)和智慧,因為它們已經(jīng)開始代替我們制作東西了。
現(xiàn)代社會什么都是科學第一,一切都被數(shù)字和學問所置換了,教育的內(nèi)容也因此而發(fā)生了變化。都說這是一個注重“個性”的時代,而在我們這些手藝人看來,現(xiàn)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個規(guī)格統(tǒng)一的模子里的,用的東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問題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我自己是靠手藝吃飯的人,也跟很多活計好的手藝人一起工作過。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們手藝人的工作是機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為一個好的手藝人,需要長時間的修煉過程,沒有近路也沒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地埋頭往前走。這跟在學校的學習不同,它不是光靠腦子死記硬背、死讀書來完成的。這種修煉不是很多人一起學習同一樣東西,并以同樣的速度記住的過程。它的過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地體會和積累,靠繼承祖輩們傳承下來的技藝和智慧來完成的。所有的活計,從基礎(chǔ)開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進入下一步的。因此無論你做什么都會遇到最基礎(chǔ)的問題,無論你中途退出還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還是需要你自己去解決所有的問題,沒人能幫得上你,這就是我們手藝人的工作。
我是從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一千三百年前,到現(xiàn)在還保持著跟初建時一樣的優(yōu)美形態(tài)。我在這當中領(lǐng)教了各業(yè)中的先人們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無一不是偉大的,是應該世世代代繼續(xù)傳承下去的。因為那里邊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為日本人繼承下來的技能和智慧。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能靠機械和電腦來繼承的。盡管數(shù)據(jù)能被輸入機器,機器也會告訴我們結(jié)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們?nèi)耍貏e是作為我們手藝人,是不行的。對于面前每一塊不同的材料, 在找出它們彼此不同的同時,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們的方法。這是靠多年的經(jīng)驗和直覺來判斷的。但是,不知道從什么時代開始,人們開始認為這種傳統(tǒng)的方法太陳舊、太封建,于是開始用機器和自動化的設(shè)備來取代先人們堅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機器成了無所不能的萬能。
在我們宮殿木匠的工作中,打交道最多的應該是扁柏樹。這種樹就跟人一樣,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宮殿的時候, 需要我們對每一棵樹的癖性了如指掌,在這個基礎(chǔ)上再把它們用在適合它們的地方。那樣的話,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這一點法隆寺給了我們最好的印證。
在建造法隆寺的整個過程中堅守的正是這種活用樹木的智慧。這種智慧可不是靠數(shù)據(jù)來計算的,更沒有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文獻,因為這個智慧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它是靠一雙手傳遞到另一雙手中的“手的記憶”。在這“手的記憶”中,是已經(jīng)傳承了一千三百年的智慧。
在這個傳承的過程中,有一種叫作“師徒制度”的傳統(tǒng), 師父帶徒弟一傳一的修煉方法。這是一種既不省時更不省力的方法。這種方法被認為陳舊,正在被時代所拋棄。
但是,手藝人的技能和直覺是學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與人、師父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體會得到的。
我八十五歲離開自己的工作現(xiàn)場。回想自己幾十年來所走過的路,我這一輩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建打交道,我說的話離不開樹木。(龍燕妮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