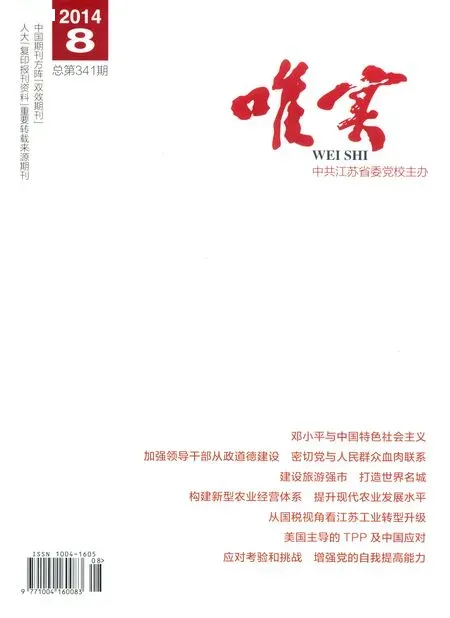江蘇城鄉居民增收的難點與發力點
吳熙云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江蘇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為江蘇未來五年發展確立了“聚力創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綱領、總目標、總任務,而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讓人民群眾有更強的獲得感,既是“聚焦富民”之根基,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撐。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江蘇能否卓有成效地促進城鄉居民增加收入,關鍵在于能否瞄準短板、發現難點、抓住重點、精準發力。
一、江蘇城鄉居民增收的主要短板
自2006年江蘇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富民優先的第一發展導向”以來,江蘇城鄉居民增收取得了明顯成效。十年間,全省城鄉居民收入增幅與京津滬浙四省市相比總體靠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縮小。但另一方面,與江蘇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城鄉居民收入還是不夠相稱,一些地方老百姓收入還不高;比照京津滬和近鄰浙江,江蘇城鄉居民收入還有較大差距,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還有不少短板需要下大力氣補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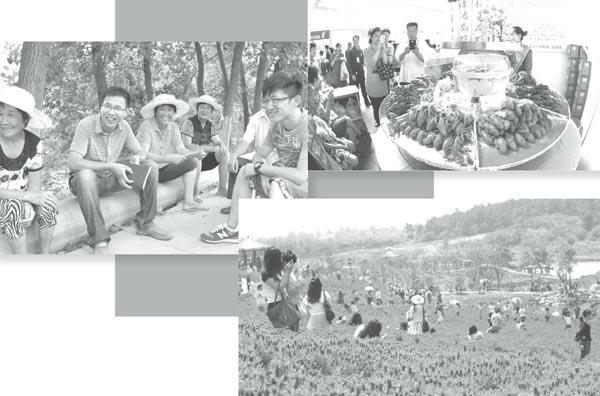
最大短板:江蘇城鄉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明顯偏低。從城鎮居民收入來看,2015年江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國第四位,較上海、北京約少30%,較浙江少15%。其中,工資性收入分別少30%、31%和10%,對總差距的影響力分別為60.5%、64.4%和38.0%。上海、北京是直轄市,主城區覆蓋范圍大,歷史上地區類別就遠高于江蘇,工資基數與水平是江蘇所無法企及的。而浙江民營個私經濟相對發達,以規模以下工業為例,2015年浙江有80.21萬家,而江蘇只有42.05萬家,僅為浙江的一半多一點,浙江個私老板遠多于江蘇;浙江人口規模遠小于江蘇,就業狀況相對優越些,居民就業層次和工資薪酬水平也就整體高于江蘇。從農村居民收入來看,2015年江蘇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平均為上海、北京的一半,與浙江和天津分別相差38.8%和27.3%,對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響力分別均超過100%。
關鍵短板:與浙江相比江蘇城鄉居民的地區收入差距過大。江蘇高收入人口比例低,低收入人口比例高,明顯拉低了全省平均水平。以農村為例,浙江全省高收入農民過半,江蘇僅占三成,比例較浙江低20.4個百分點。2015年,浙江嘉興、寧波、舟山、杭州、紹興、湖州農民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以上,六市農村人口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51.2%;江蘇蘇州、無錫、常州、南京、鎮江農民收入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以上,而五市農村人口僅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30.8%。江蘇南通、揚州、泰州和浙江溫州、臺州均屬各自省份的平均收入水平地區,農村人口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3.1%、28.1%,江蘇比浙江低5個百分點,平均收入水平與浙江相差26%。浙江金華和江蘇鹽城屬于本省偏低收入地區,兩市農民收入各低于本省4%和3%,農村人口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10.8%和10.2%,比例大致相當。浙江全省低收入農民僅占一成,而江蘇超過三分之一,比例較浙江高24.8個百分點。浙江麗水、衢州農民收入平均低于全省24.2%,兩市農村人口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10.5%;江蘇宿遷、連云港、淮安、徐州農民收入平均低于全省18.3%,四市農村人口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35.3%。正是因為高收入人口比例低,低收入人口比例高,使得江蘇農民收入平均水平整體下移,低于浙江。
短板之三:江蘇城鄉居民家庭經營非農產業收入不及浙江。浙江城鄉居民家庭較早走上了親商重工之路,2015年全省城鄉居民家庭經營收入中,第三產業收入比重分別為68%、44%,人均分別比江蘇多1639元、1591元;第二產業收入比重分別為29%、26%,人均分別比江蘇多1074元、583元。江蘇地勢平坦,耕地居多,農民家庭傳統農耕理念相對較強,2015年農業收入比重為52%,高出浙江22個百分點,比浙江多1029元,但浙江城鄉居民家庭人均二、三產業總收入是江蘇的1.6倍,比江蘇多2158元。
短板之四:與浙江相比江蘇農村養老和離退休金還不高,各類社會保障程度相對較低。江蘇農民轉移凈收入多于浙江,但養老金收入明顯少于浙江。2015年,江蘇農民人均轉移凈收入2651元,比浙江多585元,高出浙江28.3%,主要原因是江蘇外出打工農民比例高,人均寄回或帶回家里的收入1106元,比浙江多538元。而作為轉移性收入主體的養老金,江蘇卻比浙江少很多,全省農民人均1432元,比浙江少858元,低37.5%。江蘇各種社會保障水平如退休養老金、新農保基礎養老金、低保標準等普遍低于浙江。2014—2015年三年間,江蘇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人均每月比浙江少126元。江蘇失地農民達到退休年齡享受的養老待遇,也明顯不及浙江,浙江在全省范圍內對失地農民實施農保轉城保的養老政策,退休可享受每月最低1500多元的城鎮養老保險金;江蘇蘇南地區雖也實施失地農民農保轉城保政策,但享受金額明顯低于浙江,蘇州地區每月只有800多元,常州等地每月為700多元,而全省其他大部分地區退休失地農民只享受每月僅300元左右的養老補助金。此外,江蘇農村基礎養老金也普遍低于浙江。
二、當前江蘇城鄉居民增收的主要難點
世界經濟復蘇的艱巨性、不確定性將直接影響今后一段時期江蘇城鄉居民增收的總體步伐。江蘇是制造業大省、出口大省,也是中小企業大省、人口就業大省。經濟的平穩發展與企業經營的正常運轉,才是保就業、促增收的蓄水池、穩壓器。目前世界經濟復蘇與發展依舊艱難,江蘇經濟發展正處在調結構、轉方式的關鍵階段,回穩向好的基礎還不夠牢固,還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下行壓力依然較大,這為今后一段時期穩定就業、促進居民增收增添了一定的壓力和不確定性。
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工資性收入進一步提高的空間逐漸受限。隨著我國經濟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比較優勢明顯弱化,已經成為制約當前多數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發展的重要瓶頸。在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企業經營困難普遍增多的情況下,居民工資性收入進一步提高的速度和空間將明顯受限。
城鄉居民增收渠道還不夠寬廣。目前,江蘇城鄉居民增收渠道相對單一,增收途徑仍較有限。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中,近八成靠工資性收入和養老、離退休金等轉移性收入的剛性增長,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的貢獻率分別約為11.8%和9.6%;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中,六成多靠工資性收入和養老金等轉移性收入的剛性增長,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的貢獻率分別約為33.6%和3.2%。
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依然較為艱巨。近年來,江蘇各地采取多項政策措施,加大了對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促增收的力度,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連續六年快于城鎮居民,城鎮低收入群體增收步伐有所加快,居民收入的城鄉差距和高低差距逐步有所縮小。但應該看到,江蘇城鄉居民之間和城鎮居民內部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比較明顯,低收入群體增收主要依靠政策措施,自身創造財富的能力不足,城鄉分別約有六成左右人群的收入水平尚未達到全省平均水平。
三、當前江蘇促進城鄉居民增收的發力點
為深入貫徹江蘇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精神,集中力量、集中資源、集中政策打好“聚焦富民”主攻仗,黨代會閉幕以來,省委、省政府相繼出臺了《關于聚焦富民持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見》和《全省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行動計劃(2017—2020)》。當前,在凝心聚力狠抓落實的基礎上,全省上下應認清國內外形勢,瞄準發力點,在攻克短板上求突破、見成效。
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提高居民工資性收入。工資是居民收入的主體,對帶動居民整體收入增長具有顯著作用,富民增收的主要發力點應瞄準工資增長,全方位提高各階層工資水平,縮小與高水平省市的差距。主要途徑包括:一是通過經濟轉型升級,壯大實體經濟,提升就業層次,造就更多更好就業崗位。二是著力拓展就業新空間,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創造更多高端就業崗位;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培育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現代物流、融資租賃等新型服務業,加快發展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產業。扶持發展小微企業,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主渠道作用。三是強化職業技能培訓,采取更為積極有效的方式和途徑,重點實施新生代農民工和低收入、弱勢困難群體為主要對象的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四是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確保職工收入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增長。
大力推進創業富民,提高居民自主經營性收入。支持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推進返鄉下鄉人員創業,鼓勵各類有專長的能人創業,政府部門應積極搭建平臺,開辟各類群體的創業園和示范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落實創業財稅優惠政策,努力為創業者優化創業環境,從而形成全社會自主創業的濃厚氛圍。
加快蘇北農村居民增收致富步伐。繼續加快蘇北區域經濟發展,為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積極壯大蘇北經濟薄弱地區村級集體經濟實力,增強富民帶動力;全面推進確權賦能,挖掘現代農業增收潛力;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積極拓寬增收新渠道;進一步完善支農惠農政策,增強農業主產區農民增收的可持續性;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加快低收入地區居民增收步伐。
重點幫扶困難弱勢群體增收脫困。逐步提升低保對象生活保障標準,積極推進城鄉低保標準一體化;及早將符合條件的殘疾人對象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強化社會救助托底功能。統籌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制度,構建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為基本,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教育、住房、就業救助和臨時救助等專項救助銜接配套的社會救助體系。發揮紅十字會、慈善會、基金會等示范作用,促進人道慈善事業與社會救助功能互補。完善鼓勵回饋社會、扶貧濟困的稅收政策。
(作者單位: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
責任編輯: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