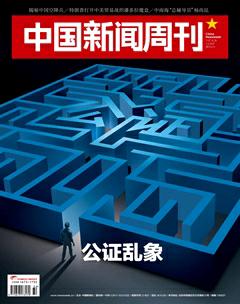特朗普打開中美貿易戰的潘多拉魔盒
李巍++宋亦明

特朗普及其主要閣僚所信奉的理念和言論充分表明了此次“301調查”
來勢洶洶,從根本上有別于先前的5次調查。它很有可能不局限于“調查”和談判,
而更可能是行將爆發的中美全面“貿易戰”的先聲
8月18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正式宣布,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將對“中國貿易行為”展開調查,涉及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領域的法律、政策和行為;四天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在白宮高調簽署了授權萊特希澤開展專門針對中國的“301調查”的行政備忘錄。這一切距中美首輪全面經濟對話在華盛頓結束尚且不足一個月。
如果說分歧明顯且成果寥寥的首輪全面經濟對話表明中美經濟再平衡路遠且艱,那么美國揮起“301巨斧”則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已經絲毫不顧雙方在過去半年里所營造起來的“友善氣氛”,執意打開中美貿易戰的潘多拉魔盒。
美國“301調查”溯源
“301條款”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經濟衰退和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的產物,長期充當了美國通過單邊手段處理貿易問題、扭轉貿易劣勢的一柄“巨斧”。它的誕生和強化也標志著美國從戰后的“自由貿易”政策全面轉向“公平貿易”政策。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不僅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貨膨脹吞噬著美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成果,凱恩斯主義幾乎完全失靈,從而帶來了長達十年的經濟“滯脹期”。此外,面對歐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國的貿易劣勢也逐漸顯現,貿易赤字不斷攀升。
為了安撫國內“經濟民族主義”,美國出臺了自1934年以來最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1974年貿易法》,設立了明確的針對貿易伙伴的報復性條款,即301條款。這一條款要求,如果美國貿易代表認定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或貿易政策與兩國簽訂的貿易協定相抵觸,或造成了不公平的貿易結果,那么可以依照總統指示采取單邊報復措施,迫使對方遵守貿易協定或調整其貿易行為。
此后,《1988年貿易法》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單面貿易報復的手段,提出了“特別301條款”與“超級301條款”。前者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對沒有充分保障知識產權的國家和地區發布評估報告并依據評估結果采取不同的報復措施;后者針對其他國家設置的針對美國的貿易障礙,查證此類國家的貿易政策并對其中的重點國家進行談判。
美國曾多次向其貿易伙伴發起“301調查”,但大多數調查以雙方談判和解告終。換句話說,雖然美國多次高高揮起“301調查”這柄巨斧,但這柄巨斧大多并未真正落下。
歐盟、巴西、泰國、韓國、日本以及德國等均遭受過“301調查”,例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與歐洲圍繞香蕉、牛肉和鋼鐵等商品接連出現了貿易爭端,與日本在汽車貿易方面爆發了貿易戰,期間美國均針對上述商品的進口展開了“301調查”。但美國發起“301調查”后,歐盟和日本分別與美國開展了馬拉松式的談判,重新明確了上述商品的貿易規則并約束了雙方的貿易行為。最終,美國對歐盟和日本的“301調查”均停留在了調查和談判階段,沒有演變為美國征收報復性關稅。
總之,美國充分利用“301調查”以及可能征收報復性關稅為威脅,向其貿易伙伴發出了強烈而可信的報復信號,迫使后者作出必要的改變和妥協,“301調查”成為了美國最為強有力的貿易權力工具,旨在扭轉美國的貿易劣勢。
美國曾先后5次開展針對中國的“301調查”,5次調查均以兩國進行艱難談判、簽署貿易合作備忘錄或協議,然后美國鳴金收兵而告終。
在中國還不是世貿組織成員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貿易代表分別于1991年、1994年和1996年,就知識產權保護先后對中國發起了3次“特別301調查”,并公布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征收清單。隨后中國與美國分別開展了異常緊張的談判,先后簽訂了3個知識產權協議,承諾完善國內立法并堅決打擊侵權行為,而這3個協議的簽署幾乎都是在美國設置的報復期限的最后幾個小時里達成的,可見當時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之激烈。后來擔任主管貿易事務的中國副總理吳儀當時就是這3輪談判的中方代表。
此外,1991年,美國還就市場準入的不公平壁壘向中國發起了“301調查”,并且公布了總價39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征收清單,中美歷經4論談判最終簽署了關于市場準入的諒解備忘錄,承諾在5年時間內取消許可證、配額、管制等進口壁壘。最近一次的“301調查”是在2010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根據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提交的指控材料,對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發起了“301調查”,最終中美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達成諒解,中國承諾取消可能造成不公平貿易的補貼或項目。
針對中國開展的5次“301調查”表明:首先,美國發起“301調查”并非完全是要采取征收高額關稅等懲罰性措施,而是希望以此提出要價,施壓中國與之談判,“301調查”并不必然導致兩國最終發生真槍實彈的貿易戰。
其次,美國對中國的“301調查”多集中于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也是中國努力“復關”的關鍵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美國的IT革命使得美國重新恢復信心,美國不再針對中國展開“301調查”。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世界貿易組織于1995年正式建立后,美國對貿易伙伴開展“301調查”的頻度明顯降低,美國希望支持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發揮解決貿易爭端的核心作用,從而約束了自身使用單邊政策工具的沖動。而在中國入世之后,中美貿易摩擦主要從具體產業轉向宏觀匯率問題。
最后,就美國而言,“301調查”是一項非常行之有效的貿易施壓工具,中國和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都不得不就“301調查”所涉及的領域進行改革和規范,以避免代價高昂的貿易報復。
統計數字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這次特朗普一反常態,堅決重新啟動針對中國的“301調查”程序,有著深刻的根源。
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貿易外交的核心議題在于“縮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向美國出口4628億美元,從美國進口1158億美元,美國對華逆差為3470億美元,占美國逆差總額的47%。日本、德國和墨西哥分別為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大國,美國對上述三國的貿易逆差分別為689億美元、649億美元和632億美元,遠低于對中國的逆差額。
在特朗普看來,降低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兌現其保護美國制造業工人的競選承諾的關鍵環節。兩國雖然在首輪全面經濟對話中達成了縮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這一原則共識,但在如何縮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具體方式上,仍存有明顯的分歧。
特朗普及其主要閣僚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中國通過不正當貿易行為獲取了貿易優勢,因而有必要對中國開展“301調查”,以“貿易戰”的威脅來迫使中國大幅讓步。然而實際上,美國對華貿易“不平衡”的產生遵循著下述三個邏輯:
首先,從生產的邏輯來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世界工廠”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也必將成為重要出口國。中國生產了美國所需的玩具、鞋襪、機電以及電子產品,其低廉的價格和良好的性能使得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大量進口,由此帶來了貿易逆差。
其次,從貿易政策的邏輯看,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又一重要原因。當前美國限制包括導航系統、集成電路、光學纖維在內的二十類,近兩千余種高科技產品的對華出口。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報告稱,如果美國將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降低至法國的水平,那么會降低12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最后,從統計的邏輯來看,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統計數字扭曲中美貿易的真實情況,夸大了兩國貿易的“不平衡”。中國除了對美出口玩具、鞋襪等“本土制成品”外,還大量出口了在全球生產但在中國最后組裝的“全球制成品”。換句話說,中國對美貿易逆差的統計數字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當前,“全球制成品”在中國對美出口中近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如排除此類商品,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將大幅降低。
從根本上有別于先前的5次調查
面對美國對華發起“301調查”和中美貿易戰“山雨欲來”的不利局面,中國需要未雨綢繆,靈活應對。
第一,做好長期與美國進行“貿易戰”的思想準備。特朗普及其內閣多位高官信奉貿易保護政策,主張通過發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來降低兩國貿易逆差。
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其施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貿易領域強調“保護國內市場、擴大對外出口”,并且將諸多國內問題歸咎于中國,中美貿易關系必將長期面臨嚴峻挑戰。
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則又是一位強硬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其多次批評中國通過“操縱貿易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剛剛離任的白宮戰略顧問班農高調宣稱“與中國的貿易戰決定一切,而且贏者通吃”,盡管班農已經離開,但他的思想卻并沒有離開白宮;而曾就鋼鐵貿易與中國開展過“斗爭”的商務部長羅斯也在近期高呼“中國正對美國的知識產權發起猛烈攻勢,美國的天才正遭受中國的攻擊”。
特朗普及其主要閣僚所信奉的理念和言論充分表明了此次“301調查”來勢洶洶,從根本上有別于先前的5次調查。它很有可能不局限于“調查”和談判,而更可能是行將爆發的中美全面“貿易戰”的先聲。因此,中國在思想上需要做好充分的應對大規模貿易戰的準備。
第二,做好反制美國貿易戰的策略準備。一方面,中國相關部門需要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反制預案,保證能夠對諸如美國的教育、電影、民用客機等產業和部門進行貿易反制,為“以戰促和”做好充分的準備;另一方面,重視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應對美國的“301調查”,盡可能充分且主動地與美國保持接觸,嘗試主導雙邊貿易摩擦談判,力求避免“301調查”快速滑向大規模貿易戰。
第三,通過加大從美國的進口來動員美方對中國的支持力量。具體來說,從長遠來看,中國需要適時、適度、適當擴大從美國進口的規模,力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控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中國可以大幅加強與美國在能源和農產品貿易領域的合作,擴大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和石油的規模,增加對美國牛肉和谷物的進口量。這樣既滿足了國內日益增長的能源和糧食消費需求,又降低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安撫了美國國內的“怨憤”情緒。
以石油進口為例,當前中國每天從美國進口的原油僅為10萬桶,如進口量提升至每天50萬桶,全年將會降低1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進而緩和美國國內對高額的對華貿易逆差的憂懼。
而中美液化天然氣貿易更是潛力巨大。國家能源局局長白克力在最近表示,2016年,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結構比重中,石油約占33%,天然氣約占24%,核電和新能源約占15%。中國的石油、天然氣、核電和新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費結構比重分別約為18.3%,6.4%和13.3%,差距最大、發展潛力也最大的就是天然氣。2016年中國首次進口了美國液化天然氣,總計3船19.9萬噸,但在中國當年進口液化天然氣2610萬噸的總量中連一個零頭都不到。2017年,如果中美能夠共同做大液化天然氣這塊蛋糕,無疑將成為中美扭轉貿易失衡的新的增長點。
總之,針對此次美國發起的“301調查”,中方需要高度重視并做好充分的準備,切不可大意和輕視。因為此次“301調查”很有可能并非貿易領域的技術性調查,而是特朗普發動對華全面 “貿易戰”的第一槍,這是遲來的也是必然會響起的槍聲。
(李巍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宋亦明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