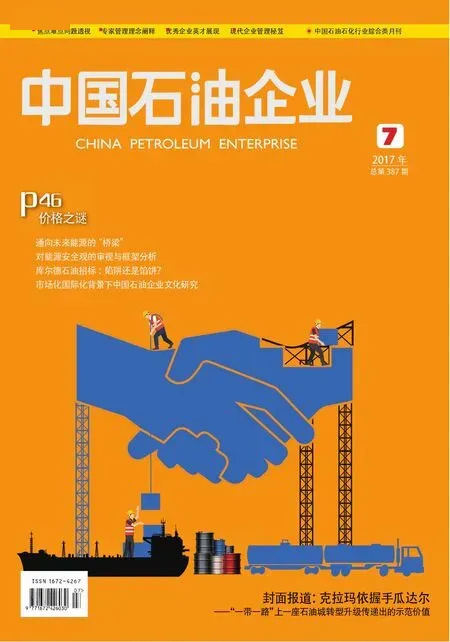價格競爭不是“通向春天的地鐵”
價格競爭不是“通向春天的地鐵”
“價格競爭是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競爭手段,沒有這種所謂的‘低層次’競爭,其他‘高層次’競爭無從談起。因此,決不能把價格競爭與質量品種競爭對立起來,二者主要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回顧我國油品市場發展歷史,正是在劇烈競爭壓力下,油品品質才不斷得以改善、提升,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毛加祥認為,作為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在完全市場化語境里,價格競爭仍然是最常見、也最為有效的競爭手段,特別是在行業出現技術轉型升級、產品更新換代之際,廠商多會以價格方法快速出清庫存產品,通過市場凈化功能,淘汰‘劣質’廠家。但在非完全市場化環境里,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事實上,上個世界90年代初期,國家就下發了《關于嚴格控制擴大煉油生產能力的通知》(國發〔1991〕54號)文件,命令未經國務院批準擅自新建、未列入1998年國家原油分配計劃的小煉油廠,包括加工進口燃料油的小煉油廠,必須在1999年7月31日前關閉。后來也確實關閉了100多家‘小煉油’作坊。但后來發現,這些‘小煉油’都以各種名目、改頭換面被地方政府‘保護’起來。現在成氣候的地煉企業,大部分都來自這些當年被淘汰的‘小煉油’,有些甚至是‘土煉油’、‘黑煉油’。”中國石化工程建設公司副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啟業認為,目前我國煉油能力最大的增量來自地方煉油廠。
經過10多年清理整頓,地煉非但沒有在清理中沉寂,數量反而不斷增加,一次加工能力超過1.6億噸。與2000年相比,山東地煉一次加工能力增長超過25倍,主營業務收入增長超過70倍,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主營業務收入均占全國地方煉廠的70%以上。
“重復建設導致了產能過剩,而重復建設主體實際上就是地方政府,不同企業代表了不同地方利益。稅收、就業、GDP增長率都要由企業來完成,所以當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落敗后,地方政府往往會采取扶持政策,盡力避免企業破產(下崗問題)和被其他地方企業收購(稅收流失問題)。該轉移的資源轉不出去,該減少的產量減不下來,使得整個產業產能始終處于‘飽和’狀態。”白頤稱。

這或許就是解開煉油行業產能過剩“越治理越嚴重”怪圈之謎的鑰匙。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9年我國投資率不足30%,2000年之后從36.3%逐年遞增,到2009年底達到47.6%的峰值,2014年仍高達46.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快速收縮,因高經營杠桿的存在無法及時調整,會在整個產業鏈條上引發產能過剩。目前我國煉油產能利用率僅為75%,地方“茶壺煉廠”產能利用率不超過55%。在面臨減少產出、收縮規模、破產清算、兼并重組等市場出清行為時,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由此可見,去產能實際上成了一場央地兩級政府在結構性改革和市場本能沖動兩股力量中博弈與均衡中的暗戰。
也許有人認為,發生在石油產業鏈終端的價格競爭是好事,因為消費者可以買到越來越廉價的商品。然而,事情并非想象那么簡單,市場經濟讓所有人都擔當了雙重角色: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當人們買到更便宜商品的同時,也許正在付出更昂貴的成本。成品油價格長期下跌對國家經濟和居民生活而言,一是逐步影響石油石化及交通運輸業等行業產出價格,并在經過一段時間后,通過投入產出關系影響產品和服務價格;二是影響通脹預期,而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將起到“加速”油價向核心通脹傳導作用;三是油價下跌雖然給普通消費者帶來利益,但油價是通脹率減慢主要推手,持續低油價會給宏觀經濟帶來較大輸入性通縮風險;四是造成石油產業蕭條,各大石油企業裁員、削減開支,并引發連鎖反應。事實上,低油價對我國CPI和PPI造成的拖累早已體現,直接導致下游產品價格聯動走低,對CPI和PPI指數走勢產生較強助跌作用,進一步強化通縮預期。
盡管所有石油化工企業都明白,只有淘汰落后產能才能拯救整個行業,但憑什么要我先減產?想想過剩產能出清后行業會回暖,減產的動力又從何而來?
“所以說僅僅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完成結構性落后產能出清工作,即便規模很小,市場需求不景氣,企業也寧愿在虧損中煎熬,而不愿意主動去產能。因為一旦被淘汰出局,就意味著所有的投入都變成沉沒成本,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了。他們更希望行業內其他企業主動去產能,自己能夠搭便車,等待行業回暖之后帶來的市場和利潤。”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表示,在煉化去產能戰役中,至少有1億噸落后產能出局。怎樣界定落后產能,可以借鑒美國和日本去產能模式。
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結束高速增長期,國內供需矛盾惡化,產能結構性過剩。1974—1977年,日本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支出加碼、稅收減免等刺激需求,但收效甚微。1978—1983年,政策轉向供給側:一是處置過剩設備,整體廢棄20%落后設備;二是加快企業兼并重組,行業企業數量下降30%以上;三是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轉移過剩產能。為了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政府還專門出臺相關政策保護高端產能。以兩次石油危機為標志的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結束之后,美國政府在減稅配合下,開始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淘汰落后工藝和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最終不僅使美國產能過剩嚴重的鋼鐵業走出低谷,還獲得了在全球鋼鐵產業鏈中高端位置。兩國政府政策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政府出資收購部分過剩產能,通過政策援助協調退出者和非退出者之間利益關系。
“美日在去產能的同時升級了本國產業體系,這本身就值得借鑒。”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表示,我國也應明確劃定關停退出范圍,設置環保、能耗、質量、安全、技術、資源規模、經營情況、稅費繳納情況等多個紅線,凡是有一項不達標的相關產能必須退出。而對于先進工藝和產能予以保護,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支撐。
“淘汰落后產能僅靠價格肯定不行。從價格角度看,落后產能比先進產能成本低,加上機制靈活,更具有價格優勢。”毛加祥稱,價格戰對擴張市場有沒有效果,也是一個問題。經濟學上有個專有名詞,叫“需求價格彈性”。需求價格彈性等于需求變化率與價格變動率之比比值。簡單地說,需求價格彈性表示市場需求量對價格變動敏感程度。有些商品需求對市場價格不敏感,譬如糧食,需求量一般不會隨價格變動而變動。和糧食一樣,成品油價格需求彈性也較小,人們不會因為價格高而放棄購買燃油等石油化工品。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通過實驗,測定石油制品需求價格彈性短期為0.2,長期為0.7。按照這個系數,如果汽油價格上升30%,短期油品需求量下降幅度也不會超過5.2%。所以在成品油領域,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個性化需求,比價格更有吸引力。
從發展趨勢來看,價格競爭不是“通向春天的地鐵”,也不可能出清沉淀于市場中的落后產能。價格競爭帶來的邊際成本遞減,將導致“產出”和“需求”分離。這就是說,無論生產多少油品,如果賣不出去,同樣變不成利潤;如果賣出去薄利甚至無利可圖,企業將喪失技術研發和產品升級所需的資本和精力。
未來成品油消費將由過去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轉向個性化、多樣化消費。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消費需求逐步成為需求主體。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必將對煉油工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在石油終端市場產品日趨同質化的當下,創造稀缺,創造個性,創造價值,增加產品含金量,才是企業開疆拓土最重要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