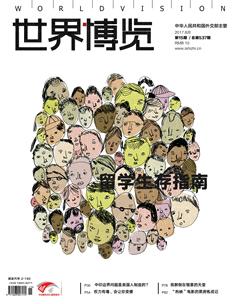留學美國生存指南
捷夫
導語:中國從滿清時代,到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青少年出國留學沒有中斷過。新中國成立后,曾經大量派遣學生留學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中國的建設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文革時期這種交流雖基本中斷,但文革之后,從1979年開始,隨著中美關系改善,中國很快就對西方社會逐步開放,出現了大批中國青年學生學者赴美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留學的熱潮。
正文:

這些年,留學和交流的形式多種多樣,有自費、國家公費、接受美方資助的,有前去讀博士、碩士、本科的,甚至去讀中學的,也有長期、中期、短期進修,短暫受聘工作的,等等。
青年學生負笈遠洋,不管是公派自費,都肩負著祖國人民、家庭父母的重托。留學歲月既漫長又短暫,漫長于日日夜夜的耕耘苦讀,寒窗不知歸期;短暫于時光流逝的來去匆匆,光陰一去不返。
怎樣才能在轉瞬即逝的光陰里,真正學到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又讓自己的留學生活盡量過得順利、安全、愉快,卓有收獲,既讓親人放心,又做到不虛度年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良好的開端,然后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走好。
確定申請策略,交出最佳答卷
倘若要對即將考慮來美留學或初來乍到的青年學生對如何走好留學路的問題提供一點參考,我想,與其籠統地高談一些條條框框,不如介紹一下筆者自身的經歷。
1984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碩士畢業之后,留校任教,參與中大地質系海洋地質研究室的創建和發展。數年之后,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出國深造,并開始探索不同途徑。
自費留學,在當時的環境下,對于我來說是不可能的。作為大學講師,當時的月工資加獎金是100多元人民幣,而家庭和父母也絕對不可能有能力資助我出國學習的。海外倒是有一些親戚,但留美數年費用可不是小數目,自己也恥于開口請求親戚贊助。
在這種情況下,出國深造有三兩個途徑可以考慮。一種公派,二是獲得美國大學的資助,三是先獲得錄取,赴美后邊學習邊打工掙學費。當時,對我來說,這幾種可能都存在。學校里通過“重點培養青年教師”項目,進行了英文摸底考試,我的成績排在第二,校方明確告訴我,計劃把我作為交換學者,公費派送到已與中大有交流的大學,比如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另外,自己也可以直接向美方大學申請讀博和資助。
我發現,通過校方辦理公派留學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一是過程太長,二是不一定能夠選擇到自己專業學科最先進的學校,雖說等待校方辦理,對自己可能少費事,容易些。另一方面,當時我覺得直接向有興趣的大學申請獎學金或資助,條件已基本成熟。這有幾個原因,一是我在四年大學和三年研究生期間的幾十門課的成績,只有一個及格、一個良好,其余均為優秀,總分排名第一,成績好對美國大學錄取很有利;二是我任教的中山大學畢竟國際上也有名氣,美國大學基本知道;三是我當時已經實實在在地做過一些南海沿岸的海洋地質研究,并已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了數篇科技論文,而且這些研究可能符合美方大學和教授研究課題的需要。
于是,1987年初,作為嘗試,我申請了美國最有名的公立礦業大學-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并很快就得到他們的博士生錄取通知。但是,通知書說,因為我提出申請的時間過了申請資助的期限,當年不能提供資助,只能在入學之后第二年再申請獎學金或其它贊助,學校會考慮。這雖是好消息,但如前所述,對我來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自費出國是不可能的。當然,拿了錄取出去,邊讀書邊打工掙錢交學費,也是可能的,但我覺得按照自己的條件,有能力拿到獎學金,再出去深造,不必著急。所以,1987年我沒有接受科羅拉多礦業學院的錄取前往該校讀博。

到了1988年,我便“憋足了氣”,一口氣申請了美國布朗大學(八家常青藤名校之一),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Scripps 海洋研究所,喬治華盛頓大學,和英國的劍橋大學等四家英美名校,順利得到所有這些大學的博士生錄取和各種資助。因為布朗大學的錄取通知來得最早,而且提供了全額獎學金,我于88年3月向校方和教育部提交申請,要求同意我赴美留學。
關于布朗大學的錄取,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值得一提。1987年夏天,我在北京外文書店,看到布朗大學世界頂級的同位素地質、沉積地層學家馬修斯教授一本名為“沉積學和動力地層學導論”的教科書,買下來一讀,啟發良多,便申請到布朗讀博,同時給馬修斯教授寫信,希望跟隨他學習。不料馬修斯教授接到信件后就強力推薦地質系和研究生院錄取我。這樣,布朗大學的研究生院在還沒有收到我的”托福“和”雞阿姨“成績的情況下就給我發出錄取和給予獎學金的通知書。
從這些經歷,可以得出兩點啟發。一是,選擇赴美留學,路子很寬,選擇很多。二是,一旦有決心赴美深造,就要有一個切實可行的策略,訂好目標并朝著目標穩步前進。
隨著中外交流的加深,也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高漲,中國的教育事業日益與世界接軌。很多高中生很早就走出去參加暑假課程,還參加各項國際比賽,并取得了好成績,成為小有名氣的“學霸”。對這些尖子而言,可以直接申請美國的頂級大學,并力圖得到學校的獎學金。
對成績比較好,但算不上”學霸”的學生,如從中學申請讀大學,主要仍然會以自費為主。對他們來說,可選擇學科齊全,信譽好的一大批州立大學,學費比較合理,教育質量也可靠。
對在國內學業不夠好,但家庭富有,父母經濟條件好,希望把孩子送出國“鍍金”,我勸他們要謹慎加謹慎,一是不要被所謂“野雞大學”所騙,需選擇實實在在辦學而不是以掙錢為主要目的的學校;二是家長要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能以為僅僅出錢就能把孩子培養出來。
對于那些在國內讀完大學,準備到美國讀博士或碩士的青年學生來說,幾個要素需加以考慮:大學成績,社會活動,托福和“雞阿姨”成績,教授推薦信,和個人興趣、對學業和生涯發展方向的陳述。這些東西都弄好,取得獎學金或資助的可能性不小,尤其是申請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因為美國大學,尤其是比較好的大學,研究生導師多數手里都握著可觀的科研基金,樂于接受他們認為有學術前途而且能夠助其一臂之力的青年學者。
至于那些大學畢業了并已在國內讀研或工作了的青年學者,象我當年的情況,因為有工作經歷,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最佳的途徑是尋找有合適、對口專業的一流學校,力爭得到贊助。原則是,越好的大學研究基金一般來說會越多,越有機會為新研究生提供贊助。
美國的大學界總的來說自由思潮開放,但相比之下,一些州立大學比私立大學條條框框多些,而私立大學中,東部的常青藤大學更為開放,那里可謂是自由派的天下。這才會有象當年我申請布朗大學時,一旦強勢的教授滿意和推薦,研究生院連研究生入學的標準考試成績都不需看就同意錄取那樣的情況。我并不鼓勵大家都走“捷徑”,需要走程序仍需走程序,但“捷徑”的確存在,前提是你必須有足夠的實力。
做好充分準備,力求開局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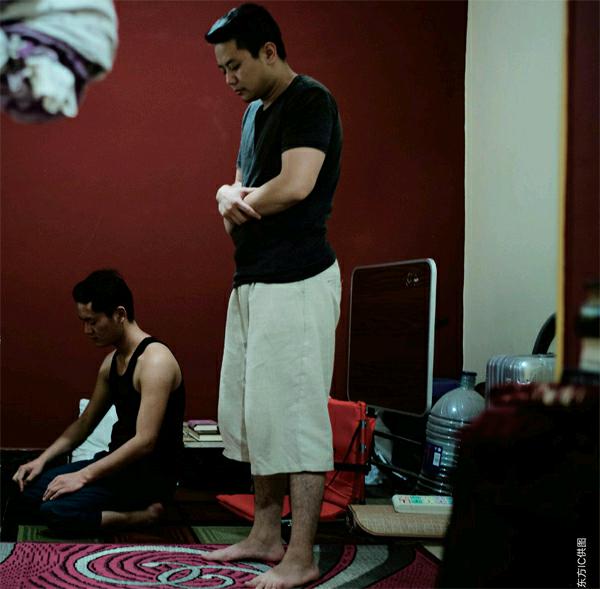
得到錄取之后,就要做好充分的準備,讓自己從踏出國門的第一天,就有比較順利的開始。
記得當年,我出國之路可謂是諸多曲折。中山大學雖然位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省,但當時學校負責師資培訓的“師培科”卻還是比較保守的。我3月份提出的出國留學申請被師培科壓住,遲遲不批。直到我所在的地質系領導和學校一位朱姓的外事處處長聯手向時任大中校長的李岳生教授陳情,在他干預下,才得到批準,這時已是8月,學校快開學了。
我以為可以在香港逗留兩天,順便看看親戚。于是買了8月30日廣州到深圳的火車票,想從羅湖海關出鏡。不料在海關被告知,中國公民赴美,即使持有美國簽證,也只能在香港機場過境,當天離開,不得離開機場進入香港逗留。
這樣,我只得拖著行李與疲憊的家人,一起折回廣州,再從廣州買了9月2日到香港的機票,同日離開香港赴美。當時我心里窩著火,心想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何持有效美國簽證的中國公民不能在那里逗留一兩天?慢慢地才理解,香港當時作為英屬殖民地,對各國公民入境有那樣的規定不足為奇,要逗留必須取得入港簽證。關鍵是我自己未有做好充分準備,事先了解清楚有關規定,結果既浪費時間、車費,還累壞自己和家人。
88年9月2日,我乘美客機聯航的到達洛衫磯,本應轉機經華盛頓機場再飛往布朗大學的所在地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市。但在洛杉磯過海關排隊太長,錯過了前往華盛頓的飛機。這件事本來可以避免。排隊時有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日本籍女生告訴我,如果轉機時間不夠,可到前面請大家讓你一下。但我沒有聽她的,覺得不好意思。這樣,航空公司只好安排我轉乘前往芝加哥的飛機,再從那里飛往普羅維登斯。
這時又出了問題。在登機的時候,工作人員說我隨身帶的一那件行李超體積,必須托運。但是,我不懂得隨機托運的行李一到目的地可從到達的登機口取,當我到達芝加哥時,卻直奔取行李的地方去,空等了好長一段時間,又錯過了當晚前往普羅維登斯的飛機。好在航空公司還挺仁慈,給我安排入住芝加哥機場的賓館并提供了餐票,并給我找到隨機托運的那件小行李。但我兩件托運的大行李卻不知去向,直到抵達目的地數天之后才被航空公司送到系里。
行李丟了不說,當晚還讓布朗大學自告奮勇去普羅維登斯機場接我的中國同學撲了空。就這樣,在不知所措的狼狽中度過了我到達美國第一天。
那天晚上,在芝加哥機場的希爾頓賓館,想起幾個月來申請出國的歷程,還有旅程的種種波折,我已經疲憊到幾乎麻木,不知疲憊,唯有望著滿天星星,任心中感概萬千。
現在的條件比我當年留學要好得多,通訊十分發達和簡便,出了問題可以隨時與家庭和各方聯系,但是,初出國門的留學生仍然需要做好各種準備,設計好旅行路線和各種應急方案,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挫折和麻煩,還要多一份心眼,弄清各種旅行有關的問題,比如過海關排隊要控制好時間,旅行之前要弄清楚有關行李的規定,萬一隨身帶的行李被要求隨機托運時,到達目的地后如何處理等等,以免出現我當年幾乎所有行李都“丟光” 的情況。
培養堅強意志,勇于接受錘煉
因為誤機,我9月2日當天沒有按計劃到達普羅維登斯,3日才到。一到目的地,只好請當地熱心人士的義工組織“國際大家庭”的一位美國友人到機場接我。她與先生十分熱情,把我接到家中,并告訴我,在找到合適的出租房之前,可以呆在他們家。我一方面給航空公司打電話詢問那兩件托運的行李的下落,一方面與布朗的中國學生會聯絡,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盡快安定下來。數學系一位叫周翔的同學很快就到美國友人家來看我。我至今還很清楚地記得他在美國朋友家,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對我說,“這樣的家庭你不能多呆,一呆就會因為太舒服而失去艱苦奮斗的動力”。我說完全同意,并讓他幫我找同學合租房子。
他很快就幫我找到一個與另外三位新來的同學合租一套四居室公寓的機會,包含一客廳一廚房兼食廳。二話沒說,我就從美國友人家搬出去了。一到公寓,但見客廳通往我睡房的地毯上有一道黑黑的腳印,已經臟得難以入目了。出國前因為怕棉被太占地方,我竟然沒有帶任何被子。9月初的新英格蘭氣溫已經只有十來度了,還是周同學,給我送來一塊街上撿來的小床墊和一張舊棉被,就這樣開始了“接地氣”的留學生涯。有了棉被好些了,但晚上仍然感到出奇地冷。
在打電話給航空公司詢問行李下落時,還出了一個大笑話。在被問及行李中有什么東西時,我說有書、小禮物和一些便藥。我雖知道“藥物”英文可以是“medicine” 和“drug“,卻不知道”drug“多用于處方藥品,同時也可以是”毒品“,在回答問題時說是”book, small gift,and drug”。這樣航空公司可能懷疑有毒品,便在我的一個箱子邊上劃了十字口子檢查(因為東西一件都沒少,除了航空公司或安檢部門外不可能有其他人打開)。順便說,這件事我本來說算了,行李箱也不是很值錢的那種,但我的美國同學知道了,替我打抱不平,要航空公司賠償。航空公司開始說,讓我付25美元,便給我一個全新的,值上百元的箱子,但美國同學不干,說這是航空公司揪住機會賺錢。為把這件事他們還去找我們共同的導師,要他出面給航空公司公關經理寫信,說他們這樣對待外國學生太不地道。他們最后竟然很執著地幫助我向航空公司索要到75 美元的賠償。這些美國同學,以后成為一生的好友。
留美的生活,就在這樣一種亦苦亦累的情況中開始,但是,因為重任在前,任何艱難都必須克服,任何辛酸苦辣都不足一提,回頭看,歲月的推移,那段艱苦的經歷反而變成人生一種豐富的體驗,成為一生中鼓勵自己向上的一種力量。
今天來美留學的同學們,經濟條件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好得多了。但是,人生艱苦的環境,更能磨煉意志。家庭條件好的,也不能有“公子哥兒”的習氣,在留學期間肆意揮霍。出身寒門的子弟,更要好好珍惜來之不易的環境,為自己交好“留學美國”這一人生重要的答卷。
專心致志學業,做到名符其實
除了日程生活上一時的不適應,學習生活也會有一個適應的過程。
美國博士教程十分嚴格,博士研究生除了選題做博士論文外,必須上完一系列規定課程,獲得足夠學分,而不是單純做博士研究。碩士生依校而定,有的需要做論文,有的完成學分即可。
記得我到校后,第一學期的必修課就包括地球化學。第一節課,我就傻了眼。講課教授東拉西扯,不僅專業內容沒聽懂,連他的英文都聽不懂。參考書章節又那么多,抓不住重點。我只好硬拼了,告訴自己,不能開局失利,決不能拿個C 或D。我硬著頭皮一頁一頁地鉆教科書,比美國同學付出加倍的努力,使出“洪荒”的勁兒,終于拿到一個B。順便說,這是我在布朗大學幾年里拿到的唯一一個B,其它科目都在A- 以上。
要以優良的成績取得學位,最重要的是心無旁騖,專心致志投入學業。的確有些學生,到了美國之后,不好好努力,只顧著體會“外面的世界好精彩”,荒廢了學業,最終難以肆業,或甚至被勒令退學。
學校的圖書館,是24小時開放的,我記得,不管是白天,還是午夜,圖書館里總有伏案埋頭苦讀的學生。作為理科生,還要幫教授管管實驗室,我經常是三更半夜都要到實驗室換材料,檢查設備和實驗結果,周末、假日都一樣。
除了成績要好之外,要培養優秀的學風和專業道德。我記得,上面提過的馬休斯教授,曾經親自帶我到圖書館,手把手教我如何利用那一本本厚厚的索引查閱參考文獻,并要求對自己文章的每一個論點都要認真交代,如是引用前人的,一定要注明出處,列入參考文獻。科研成果是誰的就是誰的,不能有半點剽竊行為。美國導師在這一點上做得特別好,學生做的研究,成果如果發表,導師真正有參與才會署名,也不會把名字放在研究生的前面,盡管研究成果是在他的資助和指導下完成的。
其次是要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我有一個學期,為馬修斯教授當助教。有一次下大雪,我的車子被雪掩蓋了,清理積雪花了太多時間,結果上課時遲到了,十分尷尬。下課后馬修斯教授嚴厲地批評我,我跟他解釋,因為清雪花太多時間,他倒是表示原諒了,但我心里一直不舒服,很自責,清雪用多點時間是真,但沒有充分估計天氣不好需要更多的時間而早點準備,也是真的。自此之后,我十分注意,決不在當助教或上課時遲到。
做人,必須靠普。有責任心,就是靠普。有些人,與你討論某些問題,討論了半天,沒有交代沒有回應就嘎然而止,這就是不靠普。做一個負責的人,一個靠普的人,能得到別人的信任,才能有朋友。在社會生活中是這樣,在留學的生涯中也是這樣。讓你的導師覺得你值得信賴,他就會更樂意培養你,在你專業的道路上幫助你。
智商情商并重,處好師友關系
作為留學生,遠離父母和親人,遠離曾經熟悉的環境,到美國來,社會和文化背景存在著實實在在的反差。孤獨、沉悶、無助、甚至壓抑的情緒隨時都可能給留學生活造成頗為負面的影響。
首先是情感上的失落和煎熬,可能導致自己作出錯誤的判斷,走上正常情況下不會走的道路。我有一位好朋友,與新婚妻子感情很深。妻子先其來美留學,一年之后,她為我的朋友辦理來美探親手續,卻在機場接機時向他宣告,她已與別人同居,他來美后必須自尋生路。這婚變的原因可以有多種,外人也不宜胡加猜測。但是,這兩位朋友原來的確是天合的一對,卿卿我我,形影不離。婚變的原因不能不令人生疑。做人還是厚道些好,尤其是在國外,更要經得起感情和其他種種誘惑,有自己的底線。
另外,情商不足,溝通欠缺也會令留學生的心態出現偏差。以美國愛荷華大學發生的盧剛事件為例。盧剛生于北京市,18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85年本科畢業后進入愛荷華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攻讀研究生,本是一個很有才華很有前途的學者。他希望獲得最佳論文獎,但是系里卻選中另一位高材生的論文,并在限期前四天提交了。盧剛認為是他的導師和系里壓制他,精心準備實施報復。 1991年11月1日,他進入了正在進行專題研討會的凡艾·倫物理系大樓三樓的309室,在旁聽了約五分鐘后,突然拔出左輪手槍開槍射擊,先后射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和導師助理,又把槍口瞄準了當時在場的另一位中國留學生,27歲的山林華博士,接著射殺了系主任尼克森。隨后,盧剛自己飲彈自盡。
盧剛事件在中國學生中只是個案,但是曾經對導師不滿、有報復念頭的研究生可能并不少,只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心中的道德感、責任感、情感和懦弱戰勝了那個邪惡的小念頭而已。從中我們能得到這樣的啟發,身為學子,要學會感恩,能以寬容、欣賞、諒解的心態接納別人,要做到智商情商并重,有強大的心理力量,要學會自我解脫。生活中要有一個積極向上的朋友圈,要有業余生活和愛好,比如體育、藝術、音樂,即使只是和朋友聊聊天也好。否則生活上有點受挫就以為天塌下來了,一時解脫不了,就試圖采取極端行為去解決問題。還要適當融入本地社會,了解當地文化,快樂面對生活,包括各種挑戰。
數年的布朗博士經歷,卻給我留下極為美好的記憶。那里的教授不僅是世界一流的學者,也是可親可敬的良師益友。因為篇幅所限,我就不在此一一描述與導師們交往的點滴往事了。
留學生涯,是人生一段珍貴的經歷。正在美國留學或正在考慮申請的赴美留學的青年學子們,要好好把握這段美好的歲月,真正做到學有所成,學有所用;要讓自己智商、情商和體商全面發展,無愧于社會,無愧于父母,無愧于人生,無愧于自己寶貴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