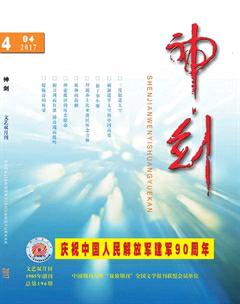為“紅學(xué)”添一抹殷紅
吳平安
年逾古稀的將軍詩(shī)人朱增泉,剛打完一場(chǎng)“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捧出5卷本洋洋130萬(wàn)言的《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之后,未及解鞍少駐,又沉浸到《紅樓夢(mèng)》詩(shī)詞曲賦中去了。從烽火硝煙的古戰(zhàn)場(chǎng)轉(zhuǎn)身到花柳繁華的大觀(guān)園,由蒼涼的刁斗胡笳切換為纏綿的江南絲竹,一張一弛,倒也正合文武之道,只是紅樓憑一書(shū)而成一門(mén)顯學(xué),前人之述,早已汗牛充棟,如作者所言“紅學(xué)常紅,深不見(jiàn)底”,即以其詩(shī)詞的“單項(xiàng)研究”而言,學(xué)者專(zhuān)家,也大有其人,已有多個(gè)版本在前,不憚以“業(yè)余段位”側(cè)身其間,是要有一點(diǎn)勇氣和底氣的。
作者的勇氣,源于“紅學(xué)常紅”的美學(xué)判斷。經(jīng)典的魅力,就在于常讀常新,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部紅樓,每一個(gè)讀者不同時(shí)期的閱讀又會(huì)有不同的感受;作者的底氣,不但源于此前在詩(shī)歌和散文領(lǐng)域的豐富著述,更源于歷經(jīng)半個(gè)世紀(jì)軍隊(duì)實(shí)際工作歷練的辯證思維,已經(jīng)深入骨髓溶于血脈,登高望遠(yuǎn),自有別一番風(fēng)景,于是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全鈔》,便能自成一格,為“常紅”的紅學(xué)再添一抹殷紅了。
體例編排,是作者碰到的第一個(gè)問(wèn)題。作者首先斟酌版本,勘定異同,將一百二十回245首(篇)詩(shī)、詞、曲、賦、聯(lián)、令、謎、偈、歌,分回悉數(shù)收錄,而《全鈔》文本呈現(xiàn)最醒目之處,是將作者245幀書(shū)法作品縮小影印,置于正文之前,一則與所錄詩(shī)詞構(gòu)成互文,二來(lái)行草瀟灑,裝飾頁(yè)面,相得益彰;詩(shī)詞錄于中,再以按語(yǔ)接于后,展開(kāi)解讀。按語(yǔ)所寫(xiě),也并非詩(shī)詞的簡(jiǎn)單詮釋串講,而是將其置入到原著語(yǔ)境中,以見(jiàn)其意涵,卻又不是對(duì)原文的照錄,而是引中有評(píng),評(píng)從引出,且牽連全篇,環(huán)顧首尾,不拘泥于一章一節(jié)的內(nèi)容。在評(píng)述的文字風(fēng)格上,簡(jiǎn)潔而雅正,盡量與原著行文風(fēng)格諧調(diào)一致,是作者努力把握的尺度。如此這般,讀畢《全鈔》,不啻把紅樓全書(shū),又從頭至尾溫習(xí)了一遍。這些看似形式問(wèn)題,反映的卻是治學(xué)的思想方法。
比體例編排更內(nèi)在的美學(xué)價(jià)值判斷,是對(duì)紅樓詩(shī)詞“定位”的獨(dú)到見(jiàn)解。《紅樓夢(mèng)》是中華瑰寶,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頂峰,已為世所公認(rèn),自不待言。那么,將同樣的評(píng)價(jià)賦予紅樓詩(shī)詞是否恰當(dāng)呢?以往論著,便多有闡釋過(guò)度之嫌。作者則跳出紅樓,將其詩(shī)詞置于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尤其是唐詩(shī)宋詞的宏大背景之下,便“立刻被高峰聳立的群山所淹沒(méi),不顯其峰巒”了。作者對(duì)第二十三回寶玉所作的四首即事詩(shī),便作了“詩(shī)品、辭藻均一般”的評(píng)價(jià),并借曹雪芹嘲諷“一等勢(shì)利人”,對(duì)賈府十二三歲公子所作溢美不絕的趨炎附勢(shì)之態(tài),無(wú)疑有點(diǎn)醒時(shí)弊之效。吟詩(shī)賦文,可以而且必須有作者的情感投入,甚至在鑒賞闡發(fā)上,也認(rèn)可“趣味無(wú)可爭(zhēng)議”的審美現(xiàn)象的存在,而一旦涉及價(jià)值判斷,則毫無(wú)疑問(wèn)必須盡量將主觀(guān)性放在一邊了。
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將《紅樓夢(mèng)》定位于“政治歷史小說(shuō)”一派,這誠(chéng)然也是紅學(xué)的重要一支,有其學(xué)理上充分的合理性,但以往有些文章往往過(guò)度執(zhí)著于政治層面的探幽發(fā)微,有意無(wú)意拔高其思想性,這也是作者力圖避免的傾向。作者并未否認(rèn)《紅樓夢(mèng)》“對(duì)封建制度、封建官僚家族的強(qiáng)烈批判色彩”,但他認(rèn)為這種批判動(dòng)力,是源于曹雪芹因家族敗落而飽嘗的人世辛酸的“切身感受”而非“思想認(rèn)識(shí)”,因此其批判“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作者在解讀《紅樓十二曲》的“收尾總曲”《飛鳥(niǎo)各投林》時(shí)闡發(fā)的這一觀(guān)點(diǎn),籠蓋了對(duì)《全鈔》的整體解讀。
上述認(rèn)知,可視為作者對(duì)紅樓詩(shī)詞的宏觀(guān)把握,在具體到一篇一首、一聯(lián)一語(yǔ)的解讀時(shí),作者又自我劃定了不可逾越的邊界。詩(shī)無(wú)達(dá)詁,系學(xué)界共識(shí)。越是優(yōu)秀的詩(shī)詞,越是享有巨大的闡釋空間,而經(jīng)典則是不可窮盡的。不過(guò)這一基本的美學(xué)原則在解讀紅樓詩(shī)詞時(shí),卻不能不受到限制,蓋因紅樓詩(shī)詞是特定章節(jié)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其解讀便不能脫離具體語(yǔ)境,自成一格式的別解,在常規(guī)詩(shī)詞鑒賞中通常會(huì)受到贊譽(yù),而面對(duì)紅樓詩(shī)詞,審美的發(fā)揮卻應(yīng)當(dāng)在科學(xué)性前止步了。
第一回《中秋詠懷聯(lián)》,便是一個(gè)典型例證,聯(lián)曰:“玉在櫝中求善價(jià),釵于奩內(nèi)待時(shí)飛。”聯(lián)語(yǔ)中“玉”“釵”所指何人?有研究者認(rèn)為當(dāng)指寶玉和寶釵,并從脂批“二寶和傳”一語(yǔ)找到了堅(jiān)實(shí)的論證基礎(chǔ),且進(jìn)一步將此聯(lián)解讀為對(duì)寶玉寶釵婚姻的暗示,乍看似乎天衣無(wú)縫了。《全鈔》的商榷指謬,先從寶玉對(duì)寶釵,從未起過(guò)“求善價(jià)”之心,所鐘情者唯黛玉切入,繼而將賈雨村中秋之夜所賦五律一首、聯(lián)語(yǔ)一副、七絕一首相互聯(lián)系,考證出上聯(lián)語(yǔ)出《論語(yǔ)·子罕》:“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下聯(lián)則嵌入了賈雨村的表字“時(shí)飛”,得出“玉”乃賈雨村自比,“釵”乃甄士隱家丫鬟,此聯(lián)乃賈雨村內(nèi)心世界真實(shí)流露的結(jié)論,這一結(jié)論,顯然持之有據(jù),合情入理,而更重要的是透過(guò)這一案例,匡正了對(duì)脂批所抱的“凡是”態(tài)度,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毫無(wú)疑問(wèn),245首(篇)紅樓詩(shī)詞,無(wú)論是著眼其在全書(shū)中的地位,或是著眼其藝術(shù)水準(zhǔn),甚至其字?jǐn)?shù)的多少,都并非是“等值”的,按語(yǔ)的解讀,便看菜吃飯,量體裁衣,長(zhǎng)其宜長(zhǎng),短其宜短,絕不平均使力。且看第十二回那篇《會(huì)芳園賦》,寫(xiě)的是鳳姐從秦可卿房?jī)?nèi)出來(lái),繞進(jìn)寧國(guó)府會(huì)芳園時(shí)眼前景致,無(wú)非花紅柳綠,鶯啼燕舞,以四六體鋪排渲染一番而已,很難說(shuō)別有深意,文字亦無(wú)甚繁難處,按語(yǔ)遂只把相關(guān)章節(jié)略加介紹,告訴讀者此賦背景即止,并未在賦文解讀上流連。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詞》按語(yǔ)卻大異其格,因系紅樓詩(shī)詞名篇,便不惜以4個(gè)頁(yè)碼篇幅,用心用力,多方切入:首先是依編排體例介紹原著語(yǔ)境以通其意,繼而抓住其纏繞回環(huán)、細(xì)膩綿密的寫(xiě)作特點(diǎn)和凄楚悱惻、真摯感人的情感表達(dá),在鑒賞上寫(xiě)下許多精彩文字,又進(jìn)一步將此篇和唐代詩(shī)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長(zhǎng)恨歌》《琵琶行》、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平行比較,從其間韻味的異同,尋找曹雪芹直接、間接接受的文學(xué)前輩的熏陶影響;按語(yǔ)的第三部分,則是以“做學(xué)問(wèn)”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考訂校勘不同版本中11個(gè)字的差異,重點(diǎn)挑出詞中6個(gè)“儂”字,引經(jīng)據(jù)典,牽古連今,審方音之異,明“你”“我”之辨,將《葬花詞》解讀點(diǎn)點(diǎn)落到實(shí)處,不啻是一篇扎實(shí)的語(yǔ)言學(xué)論文。
有些燈謎、酒令的意涵,即便是帶入具體語(yǔ)境中,也覺(jué)得除字面意思外,無(wú)法找到另有所指,作者的處理方法則是索性“不解”,其實(shí)不解之解,也未嘗不是一種解法。文章之妙,有時(shí)常妙在生出閑筆。然而面對(duì)體量龐大的長(zhǎng)篇,若強(qiáng)作解讀,硬性發(fā)掘出一些微言大義來(lái),難免牽強(qiáng)附會(huì),膠柱鼓瑟,作者顯然不屑于列入猜謎索引一派。但作者解詩(shī)中,竟也偶爾捎帶一兩句閑筆,譬如作者以第三十八回《嘗蟹賞桂》三篇,解寶玉、黛玉、寶釵三首螃蟹詩(shī)畢,筆鋒忽轉(zhuǎn),有感于《紅樓夢(mèng)》中對(duì)螃蟹的種種講究吃法,感嘆“今人吃螃蟹,只饕餮而已,已毫無(wú)情趣可言,哀哉!”這便溢出了解詩(shī)的傳統(tǒng)文體規(guī)范,屬于閑來(lái)之筆了。這樣的閑筆,可以使行文少些拘謹(jǐn),多點(diǎn)活潑。當(dāng)然應(yīng)把握分寸,宜少不宜多,故作者只在這一處無(wú)意間帶出這幾句。
通讀全書(shū),覺(jué)得“科學(xué)性”是作者一以貫之的原則,但運(yùn)用之妙,存乎一心,倒是有些楹聯(lián)、成語(yǔ),往往溢出所在章回的拘囿,具有更豐富的含義,此刻原則性便應(yīng)該要輔之以靈活性了。比如太虛幻境石牌坊聯(lián)語(yǔ),“假作真時(shí)真亦假,無(wú)為有時(shí)有還無(wú)”,曾數(shù)度出現(xiàn)于書(shū)中,雖寥寥一聯(lián),卻字字浸透人生世相,哲理玄思,禪佛意味,其義甚廣,以至于作為名聯(lián),常被援引,這也正是體現(xiàn)紅樓一書(shū)厚重之點(diǎn),在能提供巨大闡釋空間的地方,作者理應(yīng)揚(yáng)己之長(zhǎng),跳出書(shū)外,至少略加鋪展,而不必拘泥于自劃邊界不前,就事說(shuō)事,如此則這部《全鈔》,或許更能增添亮色。